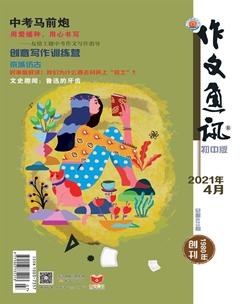艾蒿香
葉傾城
六月回鄉,一進樓門,就看到了艾蒿,長長的一束斜插在人家的鐵門上,暗綠的葉子微卷,露出銀白的葉背。一層一層上樓,各家的鐵門貴賤各異,可是大半都插了艾蒿。滿樓都是微辛的艾蒿香,還帶著一股淡淡的煙味,像是誰忘記把灶火熄滅了。
我家門上也插了,媽媽說:樓下小菜市場就有賣的,五毛錢一把。因為快到端午了。
艾蒿不是什么罕物,能放很久,葉稈越放越硬,越放越脆,撲簌簌響。夏天蚊蟲多,我又招蚊子,打之不盡,趕之還有,沒坐一會兒就被咬了一身包,我亂抓一氣。媽媽一看連忙制止:“會抓破的。”說著去了廚房,我知道她去煮艾蒿水了,屋里漸漸彌漫著一股中藥香。
上網、看書、打電話……總要媽媽千呼萬喚才來到衛生間,浴缸里,艾蒿水瑩瑩的綠,我大白鯨一般浸進去,簡直有“春寒賜浴華清池”的志得意滿。艾蒿水真能止癢祛濕嗎?難說。或許不過如小黃瓜敷臉或者何首烏洗發,象征意義高過實用。
有一年我去周莊,吃人家的青團,很愛那初春的綠及淡香,不冒失不過分,問是什么。有人答是野菜,有人說是野草,最后一位老婆婆給出標準答案:艾蒿。
艾蒿就是草。艾特托瑪夫曾形容他的祖國是一片長滿牛蒡草、艾蒿和車前子的荒原;安房直子的故事里孩子們上山采艾蒿變成了兔子;張愛玲筆下的薄命小女傭叫小艾,日子的確是野生野長。不過小艾是蔞蒿,倒不是艾蒿。
前幾年我膝蓋受傷,當時沒太在意,現在它卻像癡心不改的初戀情人,時時跳出來騷擾,拍片子又說一切正常。武漢正是梅雨天氣,膝蓋又疼起來,媽媽就給我幾根艾條。我一驚,呀,艾蒿香是我永遠不會陌生的。夏夜里,一天家務后,媽媽常常斜偎在躺椅上,膝彎手腕處,淡淡點燃一根艾條,灸她六十年勞頓的關節。現在輪到我了。———原來時序的滄桑不是詩不是文,只是一把燃著的艾條。
選自《懸崖上的草莓》,有刪改

賞析
艾蒿是一種極普通的植物,無論貧富貴賤,家家都買得起、用得著;它的葉子有香氣,可以入藥,可以食用,又可以用來治病;艾蒿還和端午節的家鄉民俗聯系在一起,被人們賦予象征意義。作者以艾蒿喻人生,平凡的人生自有意義,平平淡淡、快快樂樂的生活才是人生常態。此外,其中也隱含著對故鄉多年不變的風俗的眷戀和對艾蒿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