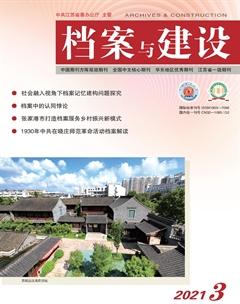蘇北抗戰(zhàn)文藝運動中的淮海戲
汪倩秋

淮海戲流傳至今已有兩百多年,“誕生于清朝末年,成長在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歲月之中,發(fā)源于偉大的淮海戰(zhàn)役的淮海平原”[1],歷史上流行于江蘇省北部的連云港、淮安、宿遷及徐州、鹽城等市部分縣區(qū),其唱腔音樂豐富多彩,樂句結尾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具有拉人魂魄的藝術魅力,故有“拉魂腔”之稱。淮海戲許多表演橋段脫胎于蘇北農村生活,早期的表演者多為走村串戶,上門賣唱、乞討的民間藝人,故而帶有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
在如火如荼的蘇北抗戰(zhàn)文藝運動中,淮海戲得以快速發(fā)展,并被譽為“革命小戲”。淮海戲藝人成為抗日宣傳員、文藝工作者,先后組建了“淮海戲實驗小組”“藝人救國會”等組織,堅持演出優(yōu)秀傳統(tǒng)戲的同時,編演了《三星落》《柴米河畔》等一批有效宣傳抗戰(zhàn)的現(xiàn)代戲,為蘇北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蘇北抗日民主根據(jù)地抗戰(zhàn)文藝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fā)生,中華民族全面抗戰(zhàn)開始,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在領導武裝斗爭的同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還領導并構筑了一條強大的文藝戰(zhàn)線,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抗戰(zhàn)文藝運動,自五四時期開始高漲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發(fā)生了適應時代需要的新變化,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陜甘寧邊區(qū)文化協(xié)會等文藝團體和組織紛紛成立,五四和左翼時期“亭子間”里獨立創(chuàng)作的文藝工作者開始被納入抗日的體系中,形成了抗戰(zhàn)時期的先進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2]因此,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抗戰(zhàn)文藝運動既是一場抗戰(zhàn)救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新啟蒙運動。
1940年10月,新四軍和八路軍在蘇北會師后,在敵后開辟了蘇北抗日民主根據(jù)地。蘇北抗日民主根據(jù)地“為中共中央中原局(后改為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所在地”[3],地域上為江蘇的北半部,總面積4.2萬平方千米,政府管轄人口450萬,包括淮海、鹽阜兩個地區(qū),是華中敵后抗日戰(zhàn)場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劉少奇、陳毅及黃克誠等都曾在這里直接領導過抗日斗爭。1940年,隨著全國抗戰(zhàn)文藝運動的高漲,劉少奇、陳毅等在蘇北抗日民主根據(jù)地發(fā)起蘇北新文化運動,號召“為開展蘇北抗日民主根據(jù)地的文化運動而斗爭”。[4]1941年4月16日,蘇北文化協(xié)會成立,劉少奇、陳毅等人到會講話,號召民間藝人參加抗日宣傳。1941年1月和6月,劉少奇、陳毅曾先后兩次主持華中局會議,討論華中根據(jù)地的文化事業(yè),主張在“抗日根據(jù)地軍民開展文化事業(yè)、擴大文藝宣傳、繁榮文學藝術等”活動,以此“喚起民眾,鼓舞軍民,打擊敵人,有力地為抗日武裝斗爭服務”。[5]其中,劉少奇在《蘇北文化協(xié)會的任務》,陳毅在《關于文化運動的意見》《為廣泛開展蘇北新文化事業(yè)而斗爭》,以及華中局宣傳部長彭康在《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的報告中,都以《新民主主義論》主要思想為蘇北新文化運動的指導思想,明確提出以抗日救亡為中心的蘇北根據(jù)地新文化建設思想,堅持與日寇作毫不妥協(xié)的尖銳對立的文化斗爭政策。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fā)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并著重闡釋了文藝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強調“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chuàng)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6]。延安文藝座談會“在知識分子中灌輸了黨性原則,黨性的輸入使文藝創(chuàng)作更加統(tǒng)一化”,“為后來相當長時間的中國文藝定下了傳統(tǒng)和底色”。[7]不久,文藝界掀起了文藝結合政治,面向群眾、服務工農兵、走大眾化道路的文藝運動熱潮,蘇北抗日民主根據(jù)地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榮景象,其“規(guī)模之大、成果之豐、影響之廣,是僅次于延安而列其他根據(jù)地之首的”[8]。
隨著蘇北新文化運動的形成和廣泛深入地發(fā)展,丘東平、許晴、阿英、黃源等一大批黨的文藝工作者來到根據(jù)地。蘇北抗日民主根據(jù)地形成了一支人數(shù)眾多的文化大軍,先后組建了“魯藝華中分院、魯工團、阜寧文化村、湖海藝文社、蘇北文工團、新安旅行團”[9]等文藝組織和團體,創(chuàng)辦了《江淮日報》《江淮文化》《蘇北記者》《先鋒報》等五十多種報紙雜志。一時間,戲劇、音樂、詩歌、木刻、漫畫、小說、秧歌等文藝形式百花齊放,其中以戲劇、歌詠、墻頭詩、秧歌舞最為廣泛和普及。這些抗戰(zhàn)文藝成果宣傳抗日救國主張,謳歌軍民愛國精神,揭露日偽頑敵罪行,為蘇北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二、“淮海小戲”命名的由來
在沿門說唱“打門頭詞”時期,淮海戲稱“三副調”,后稱“拉魂腔”,也叫“肘鼓子”。形成戲曲后,淮海戲又稱“小戲”,號稱有“三十二大本,六十四單出”,僅是一種民間藝人走村串戶,靠摞地攤演出、賣藝為生的小戲曲,被群眾稱為“七忙八不忙,九人帶廚房”[10]。抗日戰(zhàn)爭前,“各地淮海戲班社發(fā)展迅猛,單是在東海、灌云一帶就有100多個,從藝人員多達千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藝術隊伍”[11]。“當時,有幾個較有影響的小戲班子,如陳步樓、花二、吳大有、紀小豁子等,先后從沭陽來到泗陽縣北片農村集鎮(zhèn)演出。”[12]
1940年,中國共產(chǎn)黨在淮海地區(qū)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領導機構中共淮海區(qū)黨委和淮海區(qū)專員公署的機關設在沭陽張圩、陳圩一帶”[13],共轄沭陽、漣水、淮陰、泗陽、東海、灌云、宿遷、沭宿海、漣灌阜等9個縣、33個區(qū)(包含現(xiàn)在江蘇省宿遷市、淮安市、連云港市、徐州市的部分轄區(qū)),并在全區(qū)廣大農村相繼成立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政權。蘇北根據(jù)地主要以農民為主,僅淮海根據(jù)地內農民就占90%以上。淮海戲等民間戲劇雖然不登大雅之堂,但劇目創(chuàng)作非常便捷,題材反映農村和現(xiàn)實生活,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是淮海地區(qū)群眾喜聞樂見的戲劇形式。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初期,以馮國柱、吳健為骨干成員的“上海國民救亡歌詠協(xié)會二隊”途經(jīng)淮海地區(qū),播下了宣傳抗戰(zhàn)的火種。由于抗日救亡宣傳工作的需要,淮海區(qū)各地抗日民主政府十分重視民間戲劇的發(fā)展,紛紛將淮海戲、柳琴戲、淮劇等民間藝人集中培訓,定期給藝人們上政治課、文化課和業(yè)務課,幫助成立“沭陽縣抗日藝人救國會、漣水縣百藝工會、潼陽縣(東海)抗敵宣傳隊、武裝宣傳隊”[14]等“藝人救國會”和宣傳隊,并發(fā)放“抗日藝人證”。同時,中共的文藝工作者積極協(xié)助民間藝人們整理唱腔,編演新戲。為了配合開展對敵瓦解工作,編演《打偽鄉(xiāng)公所》《小寡婦上墳》《大義滅親》《小放牛》等淮海戲;通過《李月英尋夫》將重慶大后方滿目凄涼和抗日根據(jù)地美好風光進行對比,有效地宣傳了蘇北根據(jù)地的建設工作……正如鹽阜行署主任、蘇北行署副主任曹荻秋所說,“唱一個小調,抵一個報告”[15]。從前線到農村,民間藝人們成為黨的文藝工作者,滿懷熱情地用文藝形式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極大地鼓舞了邊區(qū)人民對革命必勝的信念。[16]
早在1939年,八路軍南下挺進支隊在湯溝建第三團,其宣傳隊就曾將淮海戲列為宣傳演出的劇種之一。蘇北根據(jù)地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淮海戲不再是僅供人們茶余飯后消遣,而是成為宣傳抗日的有力武器,步入了健康的進步成長期。“淮海戲的傳承,原來主要是以家族關系辦小戲班,通過血緣關系傳承為主,師徒關系傳承為輔,而從抗日戰(zhàn)爭時期起,有了以公家出資開辦訓練班的方式。”[17]1940年,泗沭縣抗日民主政府將流散在民間的淮海戲藝人組織起來,首先成立“淮海戲實驗小組”。在根據(jù)地抗日民主政府的幫助下,淮海戲藝人們成立了“藝人救國會”,并積極參加培訓和學習,逐步創(chuàng)建了淮海文藝工作團、淮泗中學劇團、漣東縣文工團、漣水縣文工隊和沭陽縣文工隊等演唱淮海戲的組織和團體,舉辦以淮海戲為主的文娛大競賽等各類文藝演出活動。
1943年12月,沭陽縣政府對敵聯(lián)絡處在馬廠成立淮海小戲藝人小組,這是在“小戲”之前首次冠以“淮海”字樣,從此“小戲”有了自己的“大名”。關于“淮海小戲”名字的由來,在目前的資料中,有兩種說法:一是,“淮海小戲之名是在1942年12月淮泗縣舉辦的‘抗日藝人訓練班上由淮泗縣民眾教育館長程翰亭提名確定的”[18]。二是在淮海行署組織文藝調演沭陽的小戲班被調來演出時,沭陽的同志講不出具體名稱,于是,時任區(qū)黨委副書記兼行政公署主任的李一氓同志將其命名為“淮海小戲”。這兩種說法孰對孰錯,已無從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淮海戲的快速發(fā)展與李一氓的倡導是密不可分的。
三、淮海戲的快速發(fā)展
李一氓是黨內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十分重視文化工作實踐,注重挖掘工農兵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任職新四軍秘書長時,李一氓曾在短短兩年時間里,帶領新四軍創(chuàng)作各種劇本200多個,演出戲劇約800場次,為新四軍的早期戲劇運動做出了重要貢獻。“正因為對戲劇在革命斗爭中作用有著充分的認識,在抗戰(zhàn)期間蘇北堅持斗爭的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李一氓仍大力支持戲劇事業(yè)的發(fā)展”[19],并在為《淮海報》撰寫的社論《五四論根據(jù)地的文化》一文中,率先提出發(fā)展“農民文化”,文化的對象應該是農民,將為“農”服務提升到了第一位。
1942年3月,李一氓調任蘇北淮海區(qū)。上任不久后,他就給予了淮海戲大量的資金、人才扶持,引導藝人編演反映抗戰(zhàn)與根據(jù)地建設內容的新劇目。李一氓親自挑選演員的故事至今仍在淮海大地廣為流傳。為了提高戲劇的演出水平,李一氓一直在尋找好演員,并下令:只要發(fā)現(xiàn)會唱戲的人才,就召集起來使用。一天,站崗的士兵向李一氓報告說,牢房里有一個俘虜天天一會兒唱京戲,一會兒唱小戲。李一氓聽后,趕忙讓士兵帶來俘虜。人稱馬大個子的俘虜很快就被帶來了,李一氓仔細一盤問,發(fā)現(xiàn)他果真唱過戲,是被抓來當兵的。于是,李一氓在向他宣講我黨的寬大俘虜政策后,便讓他參加排演新編劇目,戴罪立功。后來,馬大個子不僅在新編劇目中表現(xiàn)優(yōu)異,還在抗戰(zhàn)中立了功。
在李一氓的大力扶持下,淮海戲得以快速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薛云峰、溫林、苗紹年、潘長發(fā)等淮海戲工農作家,編演了百余出現(xiàn)代戲,涌現(xiàn)出大量宣傳抗日劇目,淮海戲藝人成為黨的抗日宣傳員、文藝工作者。《李月英尋夫》《抗日小放牛》《小板凳》《三星落》《十里好風光》《偽軍反正》《悲慘家庭》《晴天》等淮海戲在根據(jù)地久演不衰,有的連演300余場,“與淮海實驗劇團聯(lián)合演出的《三打祝家莊》受到李一氓的表彰,并獎給鑼鼓一套”[20]。1942年11月,新四軍第三師閱兵慶祝“蘇聯(lián)十月革命節(jié)”,并組織演出,淮海戲《小板凳》被評為最好劇目。1942年,東灌沭邊區(qū)中學組織學生成立抗救演劇隊,首演湯增桐所作的淮海戲《三星落》,其內容為一個偽軍大隊長怎樣在妻子趙桂芝及中共地下黨員陳虎的勸說下反正的故事,受到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的贊揚。“1943年,抗日戰(zhàn)爭已進入反攻階段,黨中央號召全國抗日軍民,不僅要加緊訓練,準備向敵人發(fā)動軍事進攻,還要開展政治攻勢,對敵偽軍進行宣傳瓦解工作。”[21]在這樣的形勢下,《三星落》的影響頗大,一些偽軍看了戲劇后,紛紛帶武器反正了。淮海戲在人民群眾中大量傳唱,不僅在民間廣泛傳播,也掀起了根據(jù)地人民的抗日熱潮,許多淮海戲藝人還積極投身革命,不少人為此獻出寶貴的生命。“泗陽縣東部靠淮陰交界建立淮泗縣抗日民主政府,北部與沭陽縣南部建立泗沭縣抗日民主政府”,這兩小塊根據(jù)地是淮海戲宣傳抗日最活躍的地方,“泗沭縣魏圩鄉(xiāng)抗日劇團有團員80多人,居淮北各縣鄉(xiāng)鎮(zhèn)之首,許多團員就是抗日游擊隊員”。[22]

在黨的文藝工作者與淮海戲藝人們的共同合作下,淮海戲還突破舊的表演方式,大膽地改革唱腔和表演程式,唱腔、說白、行當都變得更加齊備。淮海戲以地攤演出為主,轉為以廣場演出為主。“戲班每到一地演出,請當?shù)厝罕妿椭钜簧刃瓮僚_,用木棒或毛竹搭成框架,只裝一道底幕,觀眾從三面看戲。用銅盆裝上豆油,用棉花捻點燃,作舞臺照明。扮演戰(zhàn)士即借軍衣,扮演百姓則向看戲的觀眾借用,扮演地主就搬用地主家的家具,有時還將真樹砍下搬上舞臺。”[23]1943年冬,淮海戲《柴米河畔》首次定譜演唱。在繼承傳統(tǒng)唱腔的基礎上,《柴米河畔》吸收民歌“十勸郎”中優(yōu)美的旋律,創(chuàng)作小戲新腔“好風光”。演出之后很快在淮海地區(qū)根據(jù)地流傳,逐步成為淮海戲女腔的基本調,使淮海戲女腔藝術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并一直被觀眾認為是淮海戲中最美的聲腔。
四、小 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共產(chǎn)黨依靠文、武兩支大軍的配合奮戰(zhàn),最終取得十四年抗戰(zhàn)的偉大勝利。1945年9月14日,淮陰縣和清江市政府在城南公園召開萬人大會,慶祝抗戰(zhàn)勝利和淮陰解放,五百多名淮海戲、柳琴戲、淮劇藝人及文工團員參加演出致賀。1945年11月1日,蘇皖邊區(qū)政府在淮陰成立,蘇北全境解放,蘇北抗戰(zhàn)文藝運動正式結束。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淮海戲成立了有史以來第一個全民所有制淮海戲劇團——大眾淮海劇團。解放戰(zhàn)爭年代,藝人們肩背步槍,手提三弦,跟隨解放軍轉戰(zhàn)南北,編演了為現(xiàn)實服務,宣傳抗日、反內戰(zhàn)的《災難海州》《大后方》《三世仇》《擔架隊》《反內戰(zhàn)》《周發(fā)乾殺妻》《想想看看》《七塊半》《軍民一家》等影響較大的現(xiàn)代戲和一些傳統(tǒng)戲。“農村戲劇運動的發(fā)展同農業(yè)互助合作運動、減租運動、民兵工作、冬學等結合起來”[24],為配合完成當時中心任務發(fā)揮了很大作用,使農村劇團得以蓬勃發(fā)展。
1949年4月,淮海區(qū)常備民工團文工隊共18人,分淮海戲、京劇兩個組南下參加渡江戰(zhàn)役,抵上海后每人獲一張“渡江光榮證”和一枚銅質“渡江勝利紀念章”。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繁榮文化政策深入人心,淮海戲也迎來了新的春天,其在繼承和發(fā)揚傳統(tǒng)表演風格基礎上,在劇目、音樂、表演、風格等各方面都進行了大力的改革和發(fā)展。1954年,為了參加華東戲曲會演,江蘇省文化局將“淮海小戲”正式命名為“淮海戲”。從此,蘊含了歷代藝人無數(shù)心血和汗水的淮海戲登上了戲劇舞臺,成為江蘇省六大地方劇種之一,并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名錄。
注釋與參考文獻
[1]蘇懷世.淮海荷花——淮海戲簡介[J].上海戲劇,1985(1):30.
[2][4][5][6][9]曹建林.蘇北根據(jù)地抗戰(zhàn)文藝研究(1940-1945)[D].蘇州大學,2012:15,14,15,20,7.
[3]韋澤洋.蘇北抗日根據(jù)地黨的建設[J].檔案與建設, 2013(2):49.
[7]陸茹.中國革命文藝的歷史考察[J].黨史文苑,2018(4):50.
[8]王闌西.序言,劉則先、劉小清編著:《蘇北抗日根據(jù)地文化散記》[M].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2.
[10][15][18][21][23]沈瑞,朱國芳.江蘇戲曲志·淮海戲志[M].江蘇文藝出版社,1999:215,9,305,265,203.
[11][17]章匯,馬紅玲.關于淮海戲的老話題[N].淮海晚報,2017-05-31.
[12][20][22]朱成棟.淮海戲溯源[J].尋根,2020(4):140.
[13]胡楊,周明.沭陽:淮海抗日民主根據(jù)地的領導中心[J].中國老區(qū)建設,2009(12):60.
[14]紀浩波.關于沭陽淮海戲[DB/OL].[2017-01-09]http://www.sshhw.com/show.asp id=793&pageno=1.
[16][24]王衛(wèi)清,王蘇淮.李一氓與蘇皖邊區(qū)政府文化建設[J].黨史博采(理論),2013(6):14.
[19]張冠中.李一氓:新四軍中博學多才的文化人[J].大江南北,2018(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