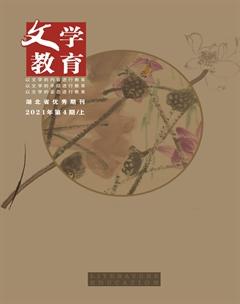浮世日常的文化向往

葛亮,原籍南京,現(xiàn)居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畢業(yè),現(xiàn)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文學作品出版于兩岸三地,著有小說《北鳶》《朱雀》《七聲》《戲年》《謎鴉》《浣熊》《問米》,文化隨筆《繪色》《小山河》,學術論著《此心安處亦吾鄉(xiāng)》《清風有信月無邊》等。作品譯為英、法、意、俄、日、韓等國文字。曾獲首屆香港書獎、香港藝術發(fā)展獎、臺灣聯(lián)合文學小說獎首獎等獎項。長篇小說《朱雀》《北鳶》兩度獲選“亞洲周刊華文十大小說”。《北鳶》亦獲2016年度“中國好書”、“華文好書”評委會特別大獎,年度中版十大中文好書等。作者獲頒《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國人物”、“《GQ中國》年度作家”、“2017海峽兩岸年度作家”。
對文化的承繼以及中西精神的碰撞向來是葛亮小說中的主題,他擅長在傳統(tǒng)文化的本性中堅守藝術的奧義,也往往能在外來文化中尋找融合的可能。歷史與個體的質地融為一體,而人性的傳統(tǒng)基因也在歷史的悠長中歷久彌新。本文將從葛亮的小說《書匠》中,提取歷史之中的文脈傳承,在詩意中尋找信念,在塵世中書寫向往。
我國的工藝向來是被世界所驚嘆的,從陶瓷到玉器,從耗費多人心血所精心打造的皇家器皿到尋常百姓的匠心獨運,在這類關乎藝術的結晶上,我國一直以來都具備著獨一無二的詩意及美感。事實上,歷史的車輪碾過時代洪流的同時,也在不斷碾壓著個體命運的離析。當新舊交替成為時代的主題,龐大的歲月席卷渺小的生命,能夠在文化傳承中保持純粹的痕跡的往往是那些在微小中凝結綿長力量的個體。
葛亮的小說《書匠》正是借用了“修復古籍”這樣一個在歷史長河中逐漸消弭的職業(yè),以古今、中西兩種文脈淵源進行跨度化的對照。他將視點聚焦在兩個完全不同又極其相似的人身上,試圖利用這樣一種手藝上的代代相傳來探討深刻的歷史主題。當時代的洪鐘在每個人頭頂敲響,總有一些手藝面臨離棄,然而,匠人的技術固然會為科技所取代,匠人精神卻仍然在無盡的風云變幻中傳承。
除此之外,小說更借助對匠人的寫作來復刻歲月的遷延,中西兩個完全不同承傳的修復師所代表的正是兩重歷史,當人物的命運與歷史交織,跨越山海后的綿延亦能成就情懷,在不同的歷史舞臺下所演就的匠人故事,正是喧囂塵世下的浮世繪。
一.歲月遷延間的浮世對照
對于匠人精神及歷史演變的書寫一直以來都在不斷地被書寫和想象,而《書匠》的開拓之處在于將對人物的觀照落在了中西兩種文化承繼之下的淵源之中。老董和鹿簡分別代表著舊時代與新時代、中國傳統(tǒng)與西方文化的碰撞。
老董的手藝是師傳,類似于古代傳統(tǒng)的拜師學藝,歷經(jīng)歲月的流轉才能碾磨成一門藝術。而有趣的是,在老董的心中,這并不能算是一種多么高深的技巧,只覺得是“江湖上混飯吃的手藝”。然而,在鹿簡的心中,對書的修復則是一種近乎信仰的存在。鹿簡從中學時起就在不斷地收集書,可以說,是對書的熱愛使得她走上了修復的道路。而在這種熱愛之中,她遇見貴人指導,才開始了真正系統(tǒng)化的學習修復。
而二者對于書的態(tài)度也是有不同的,老董在一眾舊書的粘合乃至滲透之后,才浸潤在書中,體味到書的美妙,恒心和耐心讓他在館中修書看書,成為了一個遠近聞名的“修書匠”,之后也多是為政府服務,將古舊典籍修復。而在修書之外,他也始終堅持著自己出攤兒修鞋的“事業(yè)”。
小說用了極大的筆墨來描寫老董修書的細致和繁瑣,從動作到工具都進行了盡其所能的寫照:“他埋著頭,手用一把竹起子,在書上動作著。……他仔細地用竹起子揭開粘連在一起的書頁,用小毛刷細細刷去頁面上的浮塵。……手邊的起子,約有七八把,大小厚薄各不同,如一排手術刀各有其用。他手里的這把竹起子,很輕薄,顏色較其他幾把更深,末端還掛了紅色吊墜。……這起子由扇柄改制的,剛入行就開始用,據(jù)說是當年他師傅傳下來的。如今不知經(jīng)了多少年,已用得發(fā)亮,像包了層漿。”
不僅工具細致到一點一滴都不能錯過,連帶著動作也極其仔細小心,在今天看來簡直是像在給自己找罪受:“修一本書,從溜口、悶水、倒頁、釘紙捻、齊欄、修剪、錘平、下捻、上皮、打眼穿線得二十多道工序。當年我?guī)煾担涛业谝徊剑褪菍W這補蟲眼兒。那是沒日沒夜地補,看著小半人高的書,一本又一本。吃過晚飯,給我兩升綠豆,到門廊外頭,就著月光,用根筷子,一粒一粒地揀進一個窄口葫蘆……這是一行練就一行的金剛鉆。我?guī)煾狄覍W的,不只是眼力,還有冬三九、夏三伏坐定了板凳不挪窩的耐力。”
在這種清淡的繁瑣之中,我們似乎是領略了所謂的真正匠人精神,這也和如今被大多數(shù)人所稱贊驚嘆的慢工細活兒不謀而合。然而有趣的是,葛亮卻為這種匠人精神作出了另一重注解,那就是鹿簡。
和孤兒老董在機緣巧合之下誤打誤撞入行不同,鹿簡是在正經(jīng)工作被辭之后,選擇了修書作為自己的職業(yè)。她愛書也敬書,在港大老師那兒所學到的“不遇良工,寧存故物”是她的人生信條,這里就與之前的老董拼力修復清雍正國子監(jiān)刊本《論語》形成了一定的對照。
小說中也并未對她修復之艱巨細致做出多么深刻的描繪,而是轉而將視角投向她的日常生活,借此來觀照這一職業(yè)在當下的現(xiàn)狀。不僅如此,小說更將原本的古籍修復拉下神壇。在小說中,鹿簡幾乎什么都修過,從普通的字典到平裝書《圣經(jīng)》,頗有幾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意味。當然,同樣的情節(jié)在老董身上也有所顯現(xiàn),只不過那時候給“我”的小人書的修復更像是友人間的互相幫助,遠未達到對書的崇敬與情懷。
而二者不謀而合的是,無論是老董還是鹿簡,都提到了“醫(yī)”一字。
“他沒有抬眼睛,只是答說,伯伯在給書醫(yī)病。”
“你看現(xiàn)在,她一個將孩子扯大,又找到了工作。她對我說,她每次洗書,人就輕松一點,覺得將奶奶一生的辛酸,連同自己往日的不快,都洗去了。
后來,我也慢慢好起來。做這行,何止是醫(yī)書,也醫(yī)人、自醫(yī)吧。”
對于老董來說,給書醫(yī)病,是某種職業(yè)化的需求,他有意識地將這種技藝看作是普通職業(yè)。而對于鹿簡而言,修復書籍,就是醫(yī)人也醫(yī)己。鹿簡與老董,兩人的社會經(jīng)歷乃至思想都完全不同,小說也并未按照通常所發(fā)展的那樣,為老董和鹿簡刻意勾連起某種關系。然而,正是在這樣完全隔閡甚至是相悖的人物書寫中,小說反而寫就了某種意義上的殊途同歸,更在傳統(tǒng)高雅文化的基礎上蒙上一層頗具煙火氣的人間外衣。
二.個體書寫下的歷史想象
葛亮在自我文學世界中往往十分強調傳承的歷史與情懷,他也常常將個人生活的脈絡與歷史的流轉聯(lián)結在一起,如同在大背景的浪潮之下,敘述一段關于平民的史詩。他生于六朝古都南京,先是前往香港求學,繼而留在香港工作。在他的文學版圖中,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乃至歷史碰撞往往是暗含著的主題隱喻。《書匠》一文中,是以匠人的傳承作為寫作意圖,因而也更增添了歷史的想象乃至特殊時代的構建。尤其在人物的塑造上,葛亮有意地塑造了老董這樣一個在世俗之見中有著一定污點,在工藝上卻保持著絕對的理想人格的個體,借以書寫歷史背景與個人召喚之間的雙重選擇。
小說中不斷地對老董所身處的環(huán)境提出暗示,從最開始時“我”對于年幼生活下的定義“在我看來,小學好像一架運轉精密的機器。這架機器的內核,或者是以競爭、紀律與榮譽感作為骨架”,再到后來的近乎一筆帶過的老董與“我”的爺爺之間的瓜葛,無一不提示著讀者那是怎樣的特殊年代。
老董所犯下的錯誤在之后并未被人追究,即便是“我”的家人們也仍然對老董保持著善意和尊重,但這種痛苦卻綿延影響著老董。當老爺子下葬時,老董遠遠地跟著,佝僂著身體。那一刻,似乎眼淚也沒有,只是不可名狀的痛苦蔓延在每個人的身上。
而他之后的收“我”為徒,為我精心修復獎狀、小人書等等,似乎都可以看作是對當年懦弱的贖罪。然而,在我看來,老董簡直不能算是懦弱了,他所犯的錯實際上是大時代背景下退無可退的選擇,但他仍然自顧自地為錯誤懺悔。
而在女兒元子被親媽帶走之后,“老董沒有再出攤兒修鞋。圖書館里的工作,也辭去了。
后來,他搬家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跟我父親也沒說。
來年春節(jié)前,我們家收到了一只包裹,北京寄來的。
打開來,里頭是我的一本小人書,《森林大帝》。開裂的書脊補得妥妥當當,書頁的折角也平整了。”
老董離開的決絕而坦蕩,似乎要令人懷疑,一開始就是因為女兒才會一直留在原地,他去了哪里,人們無從得知,他最后過著怎樣的生活,人們也難以知曉。事實上,小說在書寫老董時,似乎是僅僅以修書匠作為他的職業(yè)象征,來書寫這個人。但換句話說,正是修書匠的職業(yè),才使得老董成為這樣一個沉默寡言又暗藏山海的人物。匠人精神成就了老董,同時也令老董進入了一個近乎于老僧入定的靜滯狀態(tài)中。個體在時代的陰霾之下不斷被迫妥協(xié),小說將這種歷史想象拔高到了最為豐滿的力度。
相對于老董的特殊年代,對于鹿簡的描寫就更多是關于情感的折磨,一直到小說的最后,在樂靜宜的口中,“我”才得知了一個漫長而慘烈的故事。
“沒錯,這是這么多年來,我和父親唯一的一張合影。背景是查令十字街84號,那間著名的書店。這一天,我的父親告訴我,他要結婚了,和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女人。
這兩年來,她用我,復刻了一個她自己。把我父親的女兒,變成她所希望的樣子。而我,卻不知情,整兩年了。
現(xiàn)在?靜宜搖了搖頭,我對她再恨不起來了。雖然,也不可能愛。事實如此。你說,我的父親,是個什么樣的人呢?在最后的時候,打定主意,讓我的生命與她糾纏了在一起。”
靜宜的父親在去世之前以怎樣的心情,將她托付給了自己的畢生摯愛——鹿簡,而靜宜則是在發(fā)現(xiàn)了一切的情況下仍然假裝不知道,近乎于自欺欺人地將自己復制成鹿簡。
小說在這樣的歷史敘述上始終保持著吉光片羽般的窺探,沒有全貌,也沒有跡象,一切都可以說是突如其來的,也可以說是細水流深,但從始至終,小說都在一種朦朧的光影之下,完成了對個體生活與歷史想象的融合。歷史在個人的生活角落中印下深刻的痕跡,而渺小的個人雖然無法在歷史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卻仍然能夠在傳承之中書寫文脈情懷。
三.盛景頹唐后的文脈情懷
匠人精神在當下的運用、傳統(tǒng)工藝在頹唐之后應當何去何從,甚至于這種“慢工出細活”的手工形態(tài)在近乎全自動工業(yè)化的今天還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在如今都是被不斷探討的主題。以古老的修碗而言,在生產(chǎn)力低下、生活物資匱乏的時期,修碗匠走街串巷,與之類似的還有磨剪子磨菜刀等等,在今天看來都可以算得上是民間技藝。然而,修復古籍典冊的修書匠尚有一席之地,這類傳統(tǒng)民間技藝就完全沒有了用武之地。更何況,在網(wǎng)絡信息發(fā)達的今天,讀書已經(jīng)是少數(shù)人的選擇,有更多的方式可以替代。即便是書上有了污漬很難清理,想到更多的還是重新買一本。
而在這種時代環(huán)境之下,修書匠的意義究竟在于何處,葛亮提出了他的想法。
首先便是以老董為代表的典籍修復,將古書作為一門手藝,這些前文都有提到,這里不再贅述。有意思的是在鹿簡的手中被修復的書:“旁邊的思翔道,我那本書法辭典,給小孩胡鬧打翻了墨汁。不貴重,可已經(jīng)絕了版。用了二十年,心里很不舍得。交給簡,竟然也回了春。人說新不如舊,這感情在里頭,可是錢兩能計算清的?”
“奶奶后來得了老年癡呆癥,后母不容。她大學后,便把奶奶接出來照顧。祖孫相依為命。一年前,奶奶也去世了,她一直撐著。這本《圣經(jīng)》,是祖母的遺物之一,上面有老人的許多筆跡。她從此不離手,寶貝得很。也是用得太久了,書終于散了。她感情就崩潰了。我想一想,就對社工說,別的不敢說,這本書,我可以幫上忙。”
一本書,或許價值不了幾何,然而代表的卻是幾世的情懷與感情:有的見證著自己的生活變遷,陪伴著自己走過漫漫人生路,有的承載著過世親人的遺念,幾乎是活著的人的全部念想。
在這樣沉甸甸的情感之下,修書匠所擔負的絕不僅僅是老董那般的家國情懷,更是關乎人間煙火氣的人文關懷。除此之外,小說更為修書匠鋪陳上了文化傳承乃至交流傳播的效用。從“我”同鹿簡的見面,小說有意識地加了一處閑筆,電梯里走進來的壯漢,看樣子十分兇狠,然而“他轉過身,我看見他背后紋著一條龍,龍爪的位置,寫著“兼愛非攻”。我們在五樓出去。我抱著箱子有些吃力。大漢咧嘴一樂,露出一口被煙熏得焦黃的牙齒,問‘使唔使幫手。”
背后紋龍,本是看起來就不好惹的狠角色,但龍爪上寫的“兼愛非攻”,又在這一層霸氣之上平添了幾分喜劇色彩。小說正是在這樣一種交融中,接著去寫鹿簡對書的愛護及與書的關系。在鹿簡的生活里,書已然成為了一種象征,在她的每個人生拐點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從年幼的愛書,到因書而工作,再到同靜宜的父親有關系,其間種種,可以說,都是書在起著轉圜的功勞。
歷史的車輪下,所謂的盛景頹唐之后,修繕書這一行業(yè)的存在仍然能夠讓他們在平凡生活中顯露出晶瑩的光影,這何嘗不是一幕屬于平凡人的傳承與召喚。
正如葛亮在創(chuàng)作談中所言的:“‘整舊如舊是他們工作的原則。這是一群活在舊時光里的人,也便讓他們經(jīng)手的書作,回到該去的斷代中去。這些書的尊嚴,亦是他們的尊嚴。”
工匠精神在今天被不斷提起,想來不僅僅是社會意義上對精細化運作的生產(chǎn)追求,更是歷史背景下對于專注、創(chuàng)新、敬業(yè)等品質精神的呼喚與向往。一方天地之中,匠人將畢生心血投身于修復之中,暮鼓晨鐘之間,即是“整舊如舊,歲月如新”。
四.城市想象中的東方風韻
無論何時,作家的生活狀態(tài)都會對其寫作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在香港生活的經(jīng)歷以及其江南文人家族的淵源將葛亮熔鑄成為了都市與歷史長期并存的復雜矛盾體,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們也常常能夠窺見這類生存困境的打磨。
香港意味著大都市、是現(xiàn)代生存時代的場域營構,同時也承襲著生命個體的精神糾葛。都市人群的精神面貌在城市的外核之下得到了極為超越性的書寫和拷問,被投射在生命背景之中時,城市也就影響了人物的生存困境,顯現(xiàn)為宿命的表達。
事實上,香港在城市的歷史中來說,是一個極為復雜和變異的存在。一方面,它具備著國際化大都市的名頭,有著燈紅酒綠的外在形式,而另一方面,香港又由于其長期的殖民地身份,絕緣于東方的文化,失落了對于本土文化的歸屬。
因此,在江南文人家族中成長的葛亮在這一空間中感受到了極為強烈的反差,也就在此呈現(xiàn)出了割裂且全新的書寫與沉淀。在這種地緣性潛移默化的影響之下,葛亮的小說往往具備了流轉的東方氣韻,在這些砥礪與融合之中,小說形成了多重文化的碰撞,也在決然不同的身份認知中重新思考城市的底蘊。
很顯然。城市乃至城市所代表的底蘊文化,均可以成為自我根基在寫作中無限沉降找到新我的途徑。與西方所盛行的文化不同的是,在東方的思想之中,我們所書寫的往往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關聯(lián)事件。藝術是某種具體的抽象,因而,通過日常生活細節(jié)的書寫和人物心理細微之處的把握實際上揭露的就是一種對于城市的迂回想象。
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下,實際上,葛亮采取了一種歷史的永恒變動觀念來對他所懷戀的民族文化進行重新書寫,他對于城市的情感特質是復雜的,多元文化的碰撞以及不同城市之間文化內涵的反差,文化的認同感在他的小說中被書寫的極為匯聚,這種復雜迷惘的“尋根”姿態(tài)跨越了文化身份的處理,同時也在城市的精神之中挖掘到了個人經(jīng)歷的異化和歲月立場的堆疊。
作為南京長大、香港生活的作家,葛亮的小說中帶有復雜的城市氣質。物質自身的粗陋、情懷中令人膜拜的美、城市意象的破碎等等,都包含著某種對于城市空間的集體欲望。在嶺南篇的《飛發(fā)》中,雖然講述的是理發(fā)店的變遷,但卻有諸多對于生活空間意識形態(tài)的描摹。很顯然,小說所懷戀的不僅僅是理發(fā)店的斗爭,更是城市光暈的消散。理發(fā)店的“殘骸”所披露的就是市場經(jīng)濟之下舊有生活形態(tài)的破碎。
同小說《書匠》類似,《飛發(fā)》中也有強烈的“我”的意識形態(tài)介入,會令人難以分清是否有作者自我的思考和憂郁,小說中諸多真實的屬于葛亮個人的情感,使得小說天然地帶有了對于城市空間的痕跡懷念,也作為歷史空間形式表征著意識中的現(xiàn)實原本狀態(tài)。很顯然,舊時的理發(fā)店作為了一種歷史的空間形態(tài),在城市之中具有獨特的美學敘事,這種連續(xù)同一性的整體書寫,所喻示的是外部空間的破碎。新式理發(fā)店的入侵,舊時理發(fā)店中少年的出走,都帶有對城市記憶和歷史空間的消磨和逃遁,也在敘事和視覺上直觀地展露了情感的凄惶。
“電車經(jīng)過的春秧街保留了下來。這里大約沒什么交通的概念。行人在車路上走,身后聽到叮叮當當?shù)穆曧懀顺北阕匀环珠_,任由電車開過去,然后再重新匯集起來。店鋪前多半是僭建的攤位,一路可以擺到車道上。其亦隨電車進退,有條不紊,并不見一絲慌亂。由馬寶道走來,路過振南制面廠, 對過是同福南貨店,賣的點心仍然以紙包裹。作為江南人,是感到親切的。直到看見有觀光客,舉著相機左右逡巡。才意識到,這條街實已成為時間的標本。”
很顯然,城市的發(fā)展過后,小說所論述的是城市創(chuàng)作之下的鮮明特點,這種獨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回溯,帶有豐富多彩的風貌講述。在《飛發(fā)》中,葛亮天然地為城市賦予了想象性的現(xiàn)實,也就是自己獨特經(jīng)歷所引導的多重姿態(tài)樣貌,在這樣的精神資源補充之下,小說形成了跨文化視域之中的精神原鄉(xiāng)建構。在葛亮豐富的文化身份之中,他能夠闡釋全新的文化視野,并且令他筆下的城市在東方底蘊的基礎上,沾染雜糅出東西方共有的多元文化,構建出凝聚的文化內核和城市空間。
事實上,當我們開始關注城市的文學性時,也代表著我們對于歷史的日常想象,小說所承載的對于城市中人物的精神困境的思考,也是城市進步的基礎上,城市本身發(fā)展的紛繁的困惑。在這種窺探之下,小說所形成的是不自覺的個體投射,也就是說,葛亮通過他對于中國經(jīng)驗的熟稔以及他多年西方生存的經(jīng)驗,在他的小說中為古老的城市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構建了歷史狀態(tài)下的都市氣息。
在葛亮的小說中,家園、故鄉(xiāng)、中國古老的東方氣韻始終都是被不斷描繪和執(zhí)著追尋的母題,尋覓的故鄉(xiāng)之中,被異化的痛苦和城市的變遷更加讓人絕望。在這樣現(xiàn)實的都市之中,葛亮無法再尋找到他曾經(jīng)所思戀的新鮮血脈,正相反,他所看到的是一個粗陋的、不堪的世俗洶涌。因此,葛亮所做的實際上是利用他的筆觸,重新刻畫日常生活之中的典雅氣韻,試圖以自己的筆觸,將個體敘事融入到大時代下的生命想象之中,寄托更為傳統(tǒng)和深遠的精神寄托。
馮祉艾,生于1995年。湖南長沙人,畢業(yè)于湖南師范大學。作品散見于《文藝評論》《百家評論》《名作欣賞》《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東吳學術》《中國文藝評論》《青年作家》《湖南文學》《文藝報》等報刊。現(xiàn)供職于湖南省文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