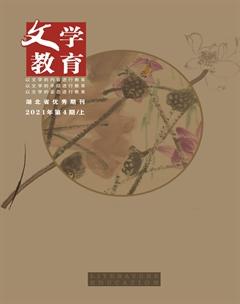《中庸》之“誠”思想含義與其現實關照
陶然
內容摘要:朱子認為四書是儒學的精華,他繼承二程的理學思想,為《中庸》學開了新的方向,即《中庸》詮釋中的心性之學和以"道心惟微"為核心的道統論。本文內容以朱熹對于儒家經典《中庸》思想進行的詮釋為主體,探析《中庸》一書“誠”的思想含義與其在當代社會所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中庸》 理論框架 誠 天人合一
一.引言
《中庸》是儒家思孟學派論人性修養的一部道德哲學專著。原是《小戴禮記》的一篇儒學論文,相傳為子思所作,是儒家學說經典論著。經北宋程顥、程頤極力尊崇,朱熹又從《禮記》書中抽出,并對其進行整理和注解,與《論語》、《孟子》、《大學》并列,合稱《四書》,成為宋代以后封建正統教育的基本教科書,對中國古代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明晰“誠”的含義,指導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踐行“誠”尤為重要。而這一過程將提高個人修養,利于和諧社會的建成。
二.淺析《中庸》“誠”思想含義
《中庸》一書的內在脈絡體系,以其獨有的特點呈現在大眾視野面前。法國學者于連曾提出:“《中庸》用很少的篇幅就讓讀者進入中國思想的核心。因為這篇古代的短論被當作文人傳統的基礎經典。同時,《中庸》讓我們達到一種思想的核心,這種思想隨著人們對它的理解和吸收,顯示為能夠成為最普遍的、最易于贊同的:因為《中庸》并不思考一個特殊的對象,而是思想的“中”,即通過世界和我們自己的不斷適應得到的平衡,即“調節”。以南宋大儒朱熹之說為:“(此書)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 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圣之書,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全書僅數千言,以內容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孔子對中庸的解讀,二是子思對于孔子中庸思想的繼承發展,其重點就是“誠”論。《中庸》一書包含著以下幾個重要的觀點:天人之道、誠論、君子論。
1.天人之道:《中庸》“誠”的中介作用
《中庸》的第一章寫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
此為全書的綱領,這是歷代學者都認同的。人性來源于天之所賦予,把人性的本質歸結于天命,是天生萬物給予了人性,通過從天到人的步驟,把天人合二為一。天作為中國古老的文字之一,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過。天字在殷商之際起源于“帝”或者“上帝”的宗教觀念之中,延續至周代賦予了天道德的涵義,主要是指具有人格化的“神”,以“敬德保民”為旨。孔子眼中的天具有神秘色彩和主觀性,一方面認為天是客觀存在的自然之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天的絕對。牟宗三先生對于“天”解釋說:“不是人格神的天,而是‘于穆不已的實體義之天。而其所命給吾人而定然如此之性,是以理言的性體之性, 即超越層面的性,面不是氣質之性,則此性體之實義(內容的意義)必即是道德創生之實體……《中庸》引‘惟天之命,于穆不己之詩句以證天之為天,則天非人格神之天可知。是哉誠體即性體,亦即天道實體,而性體與實體之實義則不能有二亦明矣。就其統天地萬物為真體言,曰實體,就其具于個體之中而為其中言,則曰性體。言之分際有異,而其為體之實義不能有異。”
2.“真實無妄”的誠論:《中庸》“誠”的真正含義
“誠”是作為《中庸》一書最重要的范疇之一。《說文解字》解釋“誠”為信,從言,成聲。即言之有信、虔誠之意。在殷商時代的甲骨文中,誠意為祭告祖先時所表達內心的虔誠。
在《中庸》第二十章提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誠來源于天道(誠者,天之道也。)作為天道之誠,又要體現在人道(誠之者,人道也。)之上。對天而言,誠是自來的:對人而言,要做到誠實不欺的德行和修養。周濂溪說:“誠者,圣人之本,圣人,誠而已矣。誠,五常之體,百行之源也。”程顥說:“《中庸》言誠,便是神。”朱熹說:“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中庸章句集注》“誠者,天之道。”一節)《中庸》言誠者和誠之者,把天人關系統一起來,既是對于天道實然的肯定,又是對于人道的應然判斷。陳榮捷先生對于此評論說:“使天與人合一的那種性質為'cheng'(誠),'sincerity'(真誠),truth'(真理),或'reality'(實在)。在這部經典著作中對這個觀念的廣泛討論使它同時成為心理學的、形上學的和宗教的概念。誠不只是一種精神狀態,而且還是一種能動的力量。它始終在轉化事物和完成事物,使天(自然)和人在流行過程中一致起來。”誠可以解釋為真誠、真理或者實在,但是無論哪一種解釋,都是針對于人的存在而言的。正如孟子所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誠字主要集中在《中庸》的第二十章至三十二章,基本涵蓋了此書的后半部分內容。誠和誠之者,作為溝通天與人之間的手段,一方面是對于天道之誠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加強對于人自身的修養,提升人的內在道德水準和要求。天道與人道是同一的,天自身而言其本性就是“誠”,而人通過后天的努力學習和修為才能達到誠。天道之誠賦予到人道時,才可以彰顯出人性至善之理,使人與天地萬物一體,與天地參:“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第二十二章)誠作為《中庸》一書中的重要范疇之一,是溝通天人之際的基礎, 即“天地之道”。杜維明先生對于此解釋說:“的確,誠,用《中庸》的話來說,就是無所不包而又充實飽滿的實在。它或許可視為存有在存在的多維結構中的一種自我彰顯。然而,誠不僅是存有,而且也是活動;它同時既是自我潛存又是不斷自我實現的生生不息的創造過程。‘至誠無息特別地指向這種‘生生不息的活動。誠就是處于原初本真狀態的實在,是人的真實本性的直接的內在的自我顯示的活生生的經驗,也是天人合一得以可能的終極基礎。”
3.君子之道:《中庸》“誠”的現實關照
《中庸》多處言君子,比如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第二章)“……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第十三章)
《中庸》所談到的君子,是為了形而上的天道給予形而下的人道一種修養的方法和途徑,從而體現出人自身的價值和道德理想。“君子”有時候和“小人”作為參照對比,告訴大家正反兩個方面的效果截然不同;有時候《中庸》所論及的君子之道好像是“費而隱”,用處雖然很廣,但是卻隱微難見。即便是愚夫愚婦有時也可以知道的道理, 但有時極精微的道理連圣賢之人也會不曉得,君子的道,是從點滴之間而積累起來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會有一個大的飛躍,洞察天地間的萬事萬物。但是,君子之道之像孔子說的那樣“未能一焉”,就是因為人們很少能夠把倫常日用與自我認識的追求相聯系。通過日常的父子之道、君臣之道、兄弟之道、朋友之道的人際關系中體會出真正的價值取向和意義,這樣的人還是沒有的。
杜維明先生說:“理解君子的一種方法,就是按照一個趨向不斷深化的主體性的過程來規定他。《中庸》所憧憬的似乎是一種自我實現的創造性過程,它是由一種自我生成的力量源泉所孕育和推動的。”誠者,不欺,不欺天地,不欺人,亦不欺本心。心懷誠篤,行事光明磊落,是天性。為了彰顯自己的誠實而倡導別人效仿,是教化。篤守誠實的天性,自然能夠洞悉幽微。深明天地化育的至理,必然信守誠篤。
三.“誠”在現實中的正確導向作用
其一,立理想目標。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誠”則是人的思想意識修養所達到的一種境界,具有培養目標的意義。以“誠”所提倡的尊師重教,愛人愛己,人們可以反省自身去發現“誠”,從而更好完善自己,實現人生的價值。
其二,筑精神根基。“誠”是認識論與價值論的統一,過程與目標的統一。每個人所處的時間空間不同,但都肩負著自己的使命,也都應對歷史承擔責任。無論個人境遇如何,都不可忘卻為中華崛起而奮不顧身的歷史使命。君子立行,唯誠而已。堅定理想信念,內化“誠”,不失為一種君子之道。于個人,誠可立身,嚴于律己;于社會,誠可致和,以禮服眾;于國家,誠可存久,生生不息。不被利益所蒙蔽,不為名利所折腰,堅守精神家園。
其三,成和諧社會。《中庸》說:“誠者,自成也,”引導人跟隨自然天性,率性而為,體現的是真誠無偽,真實而無妄。每個人都要堅守目標,成就一番事業。又言“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提倡幫助成就他人,進而成就萬物。能夠成就別人才是真正地心懷誠篤。如果沒有愛天地愛萬物之仁,沒有海納百川的胸襟,成人之美也無從談起。誠即是成,成人成物成其所成。真正的“誠者”擁有成就他人的誠心,社會和諧之美也就呼之欲出。誠所體現的就是人類美好的天性。不同緯度,修身致誠更是一個堅守的過程,面對紛繁復雜的環境,正心誠意跟隨初心,成就自己的同時服務于和諧社會,是謂“誠”的最高境界。
參考文獻
[1]黎靖德.1986.《朱子語類》王星賢點校本,中華書局。
[2]朱熹.2002.《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
[3]胡廣等.2009.《四書大全校注》,武漢大學出版社。
[4]杜小真.2004.《遠去與歸來:希臘與中國的對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5]朱熹.2011.《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
[6]牟宗三.1999.《心體與性體》,上海古籍出版社。
[7]朱熹.1992.《二程遺書》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8]杜維明.2008.《<中庸>洞見》,人民出版社。
[9]杜維明.1999.《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武漢大學出版社。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