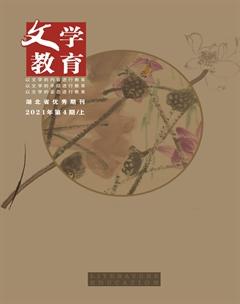“文氣說”的現代意義與價值
鄧惠文
內容摘要:“文氣說”是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的重要范疇之一,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其最初是作為一個哲學觀念而存在,曹丕首次把“氣”引入到文學創作領域中來,而后在劉勰、韓愈、蘇轍等人的補充下不斷得到完善。從現代學術的視點出發,對“文氣說”進行現代意義的解讀是十分必要的,闡釋其在指導文學創作和品評文學作品等方面的實踐價值,從而為當代文論建設作出古典文學的貢獻。
關鍵詞:文氣說 現代意義 價值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文以氣為主”的觀點,認為作家的才氣品性是文學風格的重要因素。此后關于“文氣”論方面的內容不斷豐富,并衍生出許多新的文學理論術語,如“氣韻”“神韻”等。韓林德先生曾說:“不了解氣論,就很難深刻把握華夏美學的精粹要義之所在。”[1]可見,“文氣說”蘊含著中國古代獨特的文學觀,對探尋中國古代文論的價值意義重大。然而,中國古代文論在世界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有的已經處于弱勢地位,尤其是在和西方文論的比較中出現了“失語”的癥狀,“文氣說”也不例外。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失語”的中國人必須重拾文化自信,在堅實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納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融匯中西,自鑄偉詞,才能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話語體系。
一.“文氣說”的歷史展開
“文氣說”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核心范疇,它是對作家的創作而言的,在文學創作實踐和文學批評領域具有豐富的內涵,并對后世作家的理論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探討“文氣說”應先從“氣”說起,它指的是充塞于宇宙自然生物之間的一種物質性元氣,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哲學大綱》中說:“中國哲學中所謂氣,是未成行質之有,而為行質所由以成者,可以說是形質之‘本始材料。”[2]
“文氣論”的哲學基礎是氣的觀念,它發生于自然之風,在傳統文化的背景下,人們從自然之風中感受到這種神秘的力量,并把它與自身聯系起來,進而融入到生活中,逐漸在思想層次上形成一種心靈的文氣。在這個氣化和諧的同時,體現的是中國古典詩學進程中不斷發展的個體精神、生命意識和倫理道德。古人認為“氣”是人的生命之氣,人是來源于自然并有了生命的靈動,“生氣”是二者之間的媒介。在傳統的生命觀里,假使人的生命沒有了,但他的身上的“氣”將代替實在的軀體而存在,這一過程表明“氣”能夠在超出生命的不同層次上向著更高的形式進行轉換,體現出“氣”的哲學特征。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這是最早孟子提到的關于“文”與“氣”之間的聯系。曹丕首開“以氣論文”先河,他主張“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認為文章中的氣是由作家不同的個性所形成,體現出作家創作的特殊性,也符合漢魏之交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想發展的實際,呈現出一種和經學時代不同的文學批評標準。但曹丕提到的“氣”和孟子所說的“氣”是不同性質的,后者是仁義道德修養達到一種境界后與之相配的浩然之氣,是可以學而后至的;前者是先天賦予的,屬于心理和生理方面,重視的是作家鮮明的創作個性。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氣”進行了充分討論,賦予了“氣”更多的文化內涵,包括作者的氣質稟性、創作動機的沖動等。“才有庸俊,氣有剛柔”(《文心雕龍·體性》)是指作家的內在氣質,這里將曹丕的“氣之清濁”化為更形象具體可感的“剛柔”一說。《養氣》篇是專門論“氣”的,認為養氣是要保養精力,反對勞神苦思、嘔心瀝血來寫作,主張自然醞釀。
韓愈用養氣來寫作,“氣,水也;言,浮物也。”(《答李翊書》)通過水與浮物的關系看出氣是可以駕馭的,也就是說作者要有充沛飽滿的感情,不難找到恰當的言辭。“氣盛言宜”說把思想行動跟理直氣壯跟語言文辭結合起來,形成了文思、文辭和寫作活動的緊密結合,這是韓愈勝過劉勰之處。
蘇轍等人在前人的基礎上擴大了“文氣說”的思想內涵,但基本都是對韓愈理論的沿用。直到清代桐城派的出現,韓愈提出“氣”與“言”的關系形成了“因聲求氣”說,在一定程度上對“氣”的認識進一步具體化和生動化,這也是“文氣說”理論發展較為成熟的時期。
“文氣說”在中國傳統文論中有著漫長的發展歷程,從先秦兩漢到唐宋明清,由最初的神秘變得易于把握,在這個過程中也體現了儒家傳統智慧“天人合一”的觀點。因此在討論“氣”時只有把它放在“天人合一”的體系背景模式下,才能更準確地把握整體的“氣”論。這種思想體系是古人對于中和之美的追求,也體現出“文氣論”以“生命”為核心的美學內涵。
二.“文氣說”的現代實踐價值
1.指導文學創作
曹丕提出“文以氣為主”,韓愈提倡“氣盛言宜”,那么“氣”無疑就成為了寫作的根基,而“養氣”作為“文氣說”的內核就顯得尤為重要。宋濂提出“為文必在養氣”(《文原》),認為“養氣”對于寫作有決定性作用,如果氣勢充沛,就能文思順暢,情深文明。
在文學創作時,要求創作主體通過“養氣”來提升個人的道德修養,從而使文學產生真正的審美價值。古人認為,“養氣”是文學創作的前提,作家通過“養氣”獲得飽滿的熱情,就會產生一種難以抑制的激情,進而形成文學創作沖動。這種沖動是主體生命力量的迸發投射在客體中,是主體的生理與精神,心血與氣性的統一,體現在文學上就是達到情理通融,呼之欲出的狀態。創作沖動之后還需經過藝術構思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養氣”不僅通“文思”,而且致“虛靜”。靜心養氣使得文思暢達,同時保持虛靜的狀態,擁有積極專注的精神,最終輕松自如地進行藝術構思創作,就像莊子的人生智慧,通過“坐忘”而“物化”,進而達到“養氣”的終極目標。
“氣”的概念比較玄妙,從“氣”到“文氣”的發展演變,古代文論家的解說中不免存在難以捉摸等問題,而在文學寫作的實際過程中,桐城派“因聲求氣”的觀點使“文氣”對于文學創作來說變得較為親切可感。“聲”是指文章抑揚頓挫的聲韻,“氣”是指文章于聲調、節奏和字句之間體現的神韻和氣勢,以聲得氣,氣因聲成,這就是所謂的“因聲求氣”。劉大櫆在《論文偶記》中說:“神者氣之主,氣者神之用。”強調神氣作為論文的極致。但以神論氣畢竟太抽象了,于是他指出“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從聲音中可見作者感情高低起伏的節奏美。聲音的符號是文字,漢語中同音異義的字又很多,所以劉大櫆又指出“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論文偶記》)。從神氣到音節再到字句,是由抽象到具體的過程,這樣關系逐漸明朗起來,以神氣來談文學創作就不會陷入玄虛。同時,劉大櫆又把神氣和誦讀相聯系,認為通過多讀多寫就會懂得文章怎么寫,為人們積累文氣學習寫作提供了重要方法,這也是桐城派在文學創作上的突出貢獻。此后,張裕釗在《答吳至父書》中提到了誦讀對于體會文章用意、文辭、風格方面的作用,并強調技巧法度的重要性,拓寬了“因聲求氣”的視野。這些對我們今天文學創作中音節、字句的選擇使用,以及強調誦讀的作用仍有借鑒意義和價值。
2.品評文學作品
作家之“氣”散發融注于作品,就形成作品中的氣,對于“氣”的描寫歷代作家都非常重視,他們把“氣”作為作家才力的依據,把“氣”作為評價文學作品的重要標準。
氣是詩人主體的精神特征,是表明生命個體精神意義的價值形式。因此可以從詩人主體精神氣質出發來品評詩作,《詩品》中評曹植為“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骨力和氣韻特別高,辭藻富麗;論孔融“體氣高妙”,氣質和風格都很高妙;評劉楨“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其詩倚仗氣勢,愛好奇異,但氣勢超過文采,修飾潤澤恨少,而曹丕評劉楨“公干有逸氣,但未遒耳”(《與吳質書》),說劉楨的文章有逸氣,遒勁不夠。盡管我們今天對這些觀點持有不同意見,但在當時卻仍顯示出詩人以“氣”論詩的文學風格特色。
“氣”是詩人的根本,也是詩作的根本,用“氣”來品評文學對于過去和現在都具有很大意義,而我們從歷代“文氣說”的文學批評中,可以得到一些具有借鑒價值的啟示。首先是關于作者的道德修養,孟子提出的“養氣”論就是與創作主體的精神道德修養密切相關。孟子認為必須使作者培養一種正義感,具有內在精神品格之美,養成“浩然之氣”,然后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辭,才可以寫出好的作品。這與中國古代文論認為道德與文章之間的因果關系是一致的,創作主體有了美好的德行,高潔的品質,所傾注于作品的情感也就越豐富,創造出來的作品也就越優秀。因為作者與作品是唇齒相依的關系,作者是作品審美價值產生的前提,而作品是作者整體風貌的展示。再者是要求我們對待文學批評有嚴謹的態度,不偏不倚,盡管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呈現不同面貌,但我們今天再來審視時,要有正確的認知觀和價值觀。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三,稱:“風云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鐘嶸的《詩品》論張華詩:“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云氣少。”按鐘嶸是根據他所看到的晉詩對張華詩作出評論的,元好問用唐代溫李詩作比較,這是兩個標準,標準不同,評論自異。
三.總結
“文氣說”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重要范疇,它建立在哲學“氣”論的基礎上,可以說整個古代文論史就是以“氣”貫穿的文學審美史。從魏晉南北朝“文氣”理論的基本形成,到唐至明代的理論補充創新,再到清代文論家文學實踐后的完善,它的內涵也被不斷地更新、充實。對古代文論的研究,不能僅停留在膚淺的表面,而要在其理論基礎和發展脈絡的大框架下,深入進去,尋求精華,使其對當代文論建設具有鮮活的借鑒意義和價值。同時,作品之“氣”來自于作家生命之“氣”,這說明“文氣說”的論述是賦有生命活動意義的,這種風格美指向讓我們感受到古代文學家對生命的敬畏、熱愛和尊重。而這些,正是當下文學所缺的。
參考文獻
[1]韓林德:《境生象外》,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53頁.
[2]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頁.
(作者單位:河南理工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