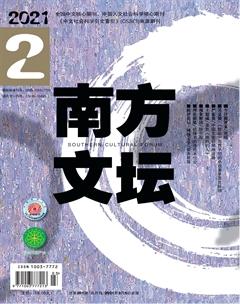《野葫蘆引》的人物及孟樾的“天地境界”
一、人物重要還是情節重要
在小說的諸多爭論中,其中就有一項:是情節重要還是人物重要。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將“情節”界定為悲劇的靈魂(亞里士多德認為詩學的最高級表現形式是悲劇),①他對古希臘悲劇的推崇使他自然得出“人物從屬于情節”的結論。似乎俄狄浦斯是誰不重要,“殺父娶母”的情節是重要的;亨利·詹姆斯則認為事件和人物密不可分。他說:人物不是事件的決定因素是什么呢,事件不是人物的解釋又是什么呢。從而翻轉了情節重于人物的觀點,認為人物重于情節。其后,M.福斯特等都主張:人物從根本上比情節更重要。西方現代派以后的小說,則似乎人物、情節都不重要,作家的觀念、理念或小說的形式翻新更重要。但只要還是視現實主義小說的成規為小說規約,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要承認,某種意義上,人物,才是小說的原動力。“不朽的文學作品的條件之一,就是要創造出令人難忘的新的人物形象,創造出新的堂吉訶德,新的哈姆雷特,新的巴扎羅夫,新的K甚至新的巴比特。”②
基于《野葫蘆引》的敘事特點的考察,可以說,人物顯然比情節重要。這部長篇基本是自敘傳色彩的回憶錄,當然是較為客觀的、在特定領域接近于“歷史”的回憶錄。由于作者的身份,所寫群體為中國知識分子中最高層,在校園及家眷們的日常生活這一領域,作者的敘事是較為客觀的。雖然整部小說的結構方式,既不是以情節為結構單元推動因果鏈的敘事,也不是以人物性格為沖突單元的命運敘事,毋寧說,是以時間為經線的類編年體的自然敘事。
即便如此,小說還是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其中不乏非常有個性、具有高度美學色彩的人物。孟樾、蕭澂、莊卣辰、江昉、秦巽衡等,這些需要一般讀者查字典才能讀對音、搞清意思的名字,在作者進行人物類別及個性塑造方面發揮了可以想象的作用。劉心武曾撰文說:“宗璞給書里人物取這類名字,一是想表達出這些人都是書香門第的后裔,二是想傳達出一種古色古香的傳統文化的氣息。”“這些莘莘學子不僅個人符碼古雅脫俗,他們還都掌握著中國古典與外國古典的符碼系統,這樣的人士在全中國人口里不消說只是一個邊緣部族。這個族群頑固地堅持一種雅致生活。他們不僅有著獨特的語言文字習慣,而且還有套社交禮儀規則,有只有他們那個圈子才理解的含蓄與幽默,甚至有不同凡俗的肢體語言。”③某種意義上,這些表意策略意味著這部長篇小說對小說的娛樂功能的拒絕。
宗璞的人物譜系,主要還是一種“范型人”,比如孟樾、蕭澂、莊卣辰、江昉、秦巽衡、李漣、梁明時、劉仰澤、錢明經、晏不來等,都是知識分子的類型形象;如衛葑、李宇明等更是一個現代文學史以來的形象類型:青年知識分子革命者譜系;他們與老革命家呂非清構成一種革命的接續與比照關系;除了“范型人”,還有處在“何事”中的人,嚴格說來,書中所有的人物都處在抗日戰爭這件大事中。直接參戰的人物有國民黨軍長嚴亮祖;作為大學生走向滇西戰場的詹臺瑋、冷若安、孟嵋、李子薇等,更有民間抗日英雄、傳奇人物彭田立和苦留、福留等;與之相對的漢奸繆東惠、凌京堯(這個人物作者傾注了同情);還有幾位師母、太太,作為傳統“女主內”型的形象,最典型的如碧初,賢惠、識大體,國難當頭之際貢獻自己柔韌的力量,維持家庭的存續。另一些人物在愛情中,如嵋、莊無因、雪妍、玹子、殷大士等,峨則很快因單戀受傷變成一個執著于事業的女強人;這些在愛情中的人物和他們的愛情故事,都體現出宗璞創作史中的互文性。衛葑與雪妍、嵋與無因的愛情,似乎都是《紅豆》的續寫與重寫。
由于作者對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知識分子保全知識火種,為國培育人才的精神的正面謳歌態度,知識分子的整體形象得以正大正氣地呈現;一方面是作者試圖達到這樣的效果:即塑造出明侖大學知識分子的整體崇高感,另一方面,卻又將他們還原為在日常生活中有著衣服住行需要的凡人。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部中國最高層知識精英的怯魅之書。矛盾與張力也即在此。作者于整部小說的創作中,除了遵循歷史時間的線性連續性,還主要遵循了人物塑造的模仿原則(現實主義的)。而小說時時籠罩的紀實風格,作者照實寫來的筆意,也與一般小說塑造人物的方法不同。如孟弗之這個人物,由于作者對這個人物的愛敬,致使這個人物某種程度上變成了先知、完人(孟夫子)。這個人物的塑造采用了所謂的典型形象的手法,把最高的智慧、德行都用在了他身上。其他人物則難見到“典型”,倒都是一些各具個性的人。作者擁有著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來塑造這些她所熟悉和親切的人物。對一般讀者來說,這些人物本來是高深神秘、不可臆測的。借助宗璞近乎實錄的人物造像,人們了解并讀懂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與日常。
宗璞的本意恐怕并不是要為這許多人物都造像立傳,她更多的只是想借嵋的一雙眼睛,回憶追索從1937年到1949年的歷史。這段歷史既有大時代的背景輪廓,即抗戰及解放戰爭時期;這段歷史更有其還原價值和意義的,在于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各色人等的心理現實與圖景;在于作者文化學、哲學、倫理學意義上的歷史反思與考量。比如,作者在這幾個主要人物身上寄托的主題:孟樾的“天地境界”;瑋瑋是“忠”的化身;嵋在親情與愛情之間(因要照顧有肺炎的父親,放棄了出國與無因團聚)選擇了親情,成全了“孝”;呂非清寧死不事日寇,謂之“節”;嚴亮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是謂“義”。可以說,整部小說中,從頭到尾貫注了作者本人的思想規范、道德倫理。這些道德倫理的主題往往成為塑造人物的主旨,影響了人物的命運。
通過作者近乎紀實的按圖索驥的寫作方式,通過作者事無巨細的記錄,我們可以一窺知識分子在險惡政治環境中的自處,以及作者是如何用他們的政治意識來塑造人物形象的;小說中人物對于時代義務、社會責任的自覺與利己主義、個人本位主義的沖突或對照;在這個總體的時空世界里,每個人物又有著自己的個性世界;她在自己的道德意識與審美意識的交錯中,又有哪些人物形象方面的得失;作者與她所寫對象之間的距離如何影響了人物。
作者精深的古典文學修養以及對西方經典文學的熟稔,都使人物形象體現出這兩方面的影響。如小說中隨處可見的古詩句、古代文學典故,這些或成為某種思維方式,直接影響到作者的行文,不自覺地貫注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或成為一種隱喻手段來刻畫人物;至于哈代的敘述視角給予作者的影響、伍爾夫等的意識流與內心獨白等,都成為作者敘事風格、人物塑造的豐富底蘊。還有一些傳統小說常用的手法,比如形象迭用。最為人所熟知的如晴為黛影,襲為釵副的描寫法,在小說的人物塑造中也可見其驚鴻之影;我們在這部小說中還發現,作者的主要人物大多形成平行或相反的結構,并且反復或重新形成這類平行或相反的人物來產生效果。這種模式的用意顯然是為了突出人物的個性以及創造一種結構上對稱的形式美,使小說的多層次質感得以展現。這種模式在中西方小說中都可找到經典案例。如莎士比亞在《亨利四世》中,就設置了亨利·珀西與哈爾王子這一對相反的人物。而在實際歷史中,這兩個人物之間并不存在這種相反的對照。莎士比亞為了后面一系列的比照形成系統,以完成人物功能設置的形式感,不惜篡改了歷史。在《野葫蘆引》中,作者塑造了孟樾一家人以及他們周圍各個不同的人物群像,還原他們每一個都是在心理上獨立的“真實的人”,將魅力趣味賦予了這些人物形象。
二、孟樾的“天地境界”
作者塑造孟樾這個人物用了多種方法,如人物的名字、住所到書房的擺設與對聯等。最重要的當然是他的思想,在小說中表現為這個人物的言論和選擇。“倘若我們取一個較為特殊的角度,把中國現代文學的‘大部分,如實地看作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體系”,趙園的立論根據是,高爾基在俄國文學史中談到,……俄國文學大部分是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體系。④那么,我們仍然可以沿用這個“思想體系”的概括。事實上,“四記”就是現當代知識分子思想體系的形象表現。作為“五四”那一代“先覺的知識者”,孟樾對于歷史、對于中國問題的思考,以及他個人道路的選擇等,都是這個思想體系的一部分。
在整部小說中,孟樾的言論是最多的,最能體現人物的思想與性格。作者甚至還敘述人物著作的歷史觀點,用以表明人物的政治態度。當然,孟樾也有一些“行動”。比如幫李漣擋住傷兵的一擊;既保護過國民黨逃跑人員,也保護過共產黨學生;因為寫文章、發表言論被國民黨當局抓捕。總體說來,作者塑造這個人物主要運用了“思想化樣式”與“理想化樣式”⑤。這兩種樣式都與生活化樣式或行動樣式形成區別,從而使人物基本呈靜態化的形象。但孟樾這個人物無疑寄寓了作者關于知識分子最高的道德理想。
他姓孟,字弗之,暗喻孟夫子。這個命名有深意。孟子最著名的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甚至主張“君無道便推翻”。孟子主張施仁政,“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把道德規范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強調舍生取義。君子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主張性善論。這位儒教“亞圣”的思想、主張,在作者的設計里,對應著孟樾的思想規范。“樾”,意思是樹蔭,如樾蔭(蔭庇,比喻尊長照顧著晚輩或祖宗保佑著子孫)。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作者與馮友蘭的親情關系,書中的孟嵋(作者的自我形象)也一直在這棵大樹的蔭庇之下。
孟樾住的寓所叫“方壺”。且看這個空間的寓意:方壺,相傳是東海三仙山之一。歷代帝王為了接近神仙,在園林里挖池筑島,模擬海上仙山的形象。一直沿襲到清代。乾隆將傳說中東海的龍宮移植到圓明園,取名方壺勝境,是圓明園十景之一,被譽為圓明園最美的景觀。方壺勝境景群于1860年10月被英法聯軍劫掠后焚毀。方壺,也是紫砂壺的一種器型。在《野葫蘆引》中,校長秦巽衡住的是“圓甑”。甑,是中國古代的蒸食用具,民間有俗語,鍋圓甑不圓,比喻事情不圓滿。方壺與圓甑,平行出現。足見在敘述者筆下,孟弗之在明侖大學的地位和影響。方壺,在這里的寓意,大概更多的還是取歷代文人隱居時愛用的居室名。如宋代詩人汪莘,自號方壺居士。以上種種透露出來的微妙象征及聯想,都意味著這個人物的重要性。在《北歸記》中,秦巽衡校長最終離開明侖之前,與孟樾還就方壺、圓甑有過幾句對話。巽衡說:“這四個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想過沒有?”弗之道:“大概是說住在里面的不過是——”巽衡抬手插話道:“不過是酒囊飯袋之人。”兩人大笑。這彼此會意的大笑,既有無用書生面對政治歷史風云的無奈,更有對此身份的自矜與自憐。
《南渡記》中,孟弗之是和莊卣辰一起最先出場的。作者接著就寫到方壺,進入弗之的書房。“書房在孟家是禁地,孩子們是不準進的。”書桌更是連碧初也不能動的。書房中有一副對聯,是從泰山石峪拓下來的,這幾個字是“無人我相,見天地心”。臺燈的燈身鐫滿五千字的道德經。“接著他開始寫他的著作《中國史探》。”這副對聯,又是一個大關節。這副對聯,是作者理想化地塑造人物的又一典型手段。“無人我相”,出自《金剛經》,原句為: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對聯的重點在這一句:見天地心。天地心——天地間至精至純至簡至明的道理,或者說,就是天道。這副對聯連在一起,意即看破表象,感受到天地至理的意思。這大概就是馮友蘭所謂人生四重境界中的最后一重,也就是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試問什么人配得上這副對聯。這個寓意既是人物的自我期許,也是作者認為這個人物的境界寫照。從書房的擺設,尤其是對聯的寓意,敘述者的目的無非是使人物顯得更加真實可觸。背景本身可以展現故事,是刻畫人物的重要手段。幾件道具往往可以省去作家幾頁篇幅的人物描寫。可使人物行動更加令人信服,使虛構故事增添真實的色彩。
盡管作者聲明,反對對小說中的人物做索隱鉤沉、對號入座,但小說一旦面世,它就進入了作者與讀者的交流模式。作為敘述的讀者具有參與功能,并且正是由于這一功能,讀者才會將小說中的事件看作歷史,將人物看作真實的人。
按照詹姆斯·費倫等的敘事學理論,人物既具有模仿和綜合成分,還具有主題成分。孟樾這個人物,就承擔了小說有關“知識分子主題”的大部分的主題成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尤其像孟樾這個階層的,關心政治是應有之義。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再被列強打敗,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帝制,中國的現代化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方面都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但中國社會積貧積弱、落后愚昧的現狀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社會主義文明興起。此時,走西方的道路已不是中國現代化的唯一選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和各種社會主義思潮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關于中國富強和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思考和爭論,在中國思想界、知識界濫觴。這個時代政治背景正是人物展開行為的環境。
知識者與政治的關系,表現在文學中,政治并非僅僅外在于文學,它不是外部對于文學的強加,而是滲透在從作者、敘述者到人物以及讀者的整個過程。《南渡記》中,敘述者借蕭澂說出了:你這個Sincere Leftist。第一次表明了孟樾的政治態度。弗之一笑:“正因為我sincere,我是比較客觀的。現政府如同家庭之長子,負擔著實際責任,考慮問題要全面,且有多方掣肘。在我們這多年積貧積弱的情況下,制定決策是不容易的。共產黨如同家庭之幼子,包袱少,常常是目光敏銳的。他們應該這樣做。”⑥這段話說得合情合理,符合人物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所可能達到的認識程度。此時的孟弗之,在與政府有吏屬關系的大學里擔任著重要職務,他并不能真如江昉那樣,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左派”。但這段話表明了一個憂國憂民、凡事站在國家大局立場,并不偏倚某一黨派的中立態度。葆有著一個知識分子“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關于“左”還是“右”,還有一次明確的談話。又是與蕭澂:“子蔚站住了,躊躇道,關于你有一種說法。說你和那邊有聯系,至少是思想左傾吧。這些議論你早知道了。還有親屬問題,說是老太爺已往那邊去了。真是無稽之談!株連攀附是中國人的老習慣了,我們不必計較。弗之笑道,我的思想則在著作中,光天化日之下。說左傾也未嘗不可。無論左右,我是以國家民族為重的。我希望國家獨立富強,社會平等合理。社會主義若能做到,有何不可。只怕我們還少有這方面的專家。當然,學校是傳授知識發揚學術的地方,我從無意在學校搞政治。學校應包容各種主義,又獨立于主義之外,這是我們多年來共同的看法。”⑦
在《東藏記》中,由于孟弗之“左傾”的政治態度,上峰不同意他繼續擔任主任之職。接著我將錄幾段有關孟弗之的文字,以便集中分析。這么做是因為敘述者實在是太聰明了。她一直在跟讀者玩著耐心和理解力的游戲,她甚至不希望你從這部小說中真看出什么來。即使是一些主要人物,“戰”線也拖得太長。她的方法是把情節再切割成更小的單元,細碎地撒在四部曲全篇中。這一點尤其是在人物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一些論者從這部小說看出《紅樓夢》的意思,也許《紅樓夢》的語言以及語法是一種潛在的影響,但其實兩者在長篇的結構方式上大相徑庭。在前者,比如秦可卿、尤三姐等的命運,都是二三回里命運的底牌就揭開了。而《野葫蘆引》的很多關鍵信息隱藏在冗雜緩慢的敘述里,如果是瀏覽式閱讀,很容易漏掉那些也許是最重要的情節。因為這部小說的寫法,情節并不是敘述者要著力經營的,所以情節隱藏在細節之中就是必然的了。
有一段是這樣的:“秦校長道:‘各方面的事很復雜,你那篇講宋朝冗員的文章,重慶那邊注意了。有個要員說孟弗之越來越左傾了,這是抨擊國民政府。弗之道:‘談不上,談不上——我認為研究歷史一方面要弄清歷史真相,另一方面也要以史為鑒。免蹈覆轍,這不是好事嗎?最近我又寫了關于掠取花石綱和賣官的文章,還是要發表的。‘道理很明顯,但是有時簡單的事也會變得復雜。巽衡頓了一頓,又關心地說:‘還有人說你鼓勵學生去延安,以后可能會招來麻煩。弗之只微笑道:‘我也鼓勵人留下來,只要抗日就好。老實說延安那邊的人也對我不滿,說我右傾。兩人相視默然。”這一段,再一次重申了孟弗之的政治態度或立場。甚至影響到他的仕途。
孟弗之與江昉的一段對話更加耐人尋味。一個是被認為的“左傾”,實際上的立場應在當時的正統主流,盡管正直的人都知道那個“正統”已經非常腐朽。另一個是真正的左派。他們分屬兩個陣營,按理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之間會彼此水火不容。我們從魯迅與他的論敵之間的文章即可看出火藥味的濃烈程度。但弗之與江昉之間,不但完全沒有辯論起來,最后在精神境界上居然同一了。兩人先都抨擊了國民黨當局政治的腐敗墮落,“江昉突然轉身道:‘聽說延安那邊政治清明,軍隊里官兵平等,他們是有理想的。弗之道:‘整個歷史像是快到頭了,需要新的制度,——不過那邊也有很大問題,就是不尊重知識,那會是很大禍害。江昉不以為然,說:‘知識固然重要,但對我們來說,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最重要。……
“弗之沉思道:‘若能在心里保存一點自蘸清溪綠的境界,就不容易了。江昉說:‘想法會影響行動,要是真做起來,豈不是自私自利?弗之微笑道:‘我想你也盼著有一天能夠得到純粹的清靜,好遨游九歌仙境之中。江昉磕磕煙斗,說:‘你看透我了。仍把煙斗放在口中。弗之忽然想起,從柜角找出一包煙絲,遞給江昉,‘這是舍親送的,我又不抽煙。江昉接過,笑說:‘他多送些才好!”⑧
這一場對話,描畫出兩個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的風采。既是主義的不同,也是性格的不同。于是,一場文明的、和平的交鋒,到此為止了。江昉說出了“自私自利”的話,弗之卻將鋒矛轉向了邵雍的詩。用知識分子都向往的理學大師的境界化解了江昉的鋒芒。智慧、大氣、溫厚卻不失正義的弗之形象更加鮮明了。
弗之由于校長親囑他代修身課,因學生思想太激進,都反對國民黨,而國民黨又想將這課上成三民主義的思想課,來統一學生的思想。弗之因別的老師不愿帶而接下,事后也因修身課被學生誤解他壓制思想自由。可見,那時要做一個正直的、又政治正確的知識分子是很難的,孟弗之的處境似乎左右為難。作為學校的管理者之一,孟弗之深知人才難得。他愛才,不懷成見地幫助提拔人才,包括白禮文、尤甲仁等。在代管學校期間,既保護過國民黨的人,也放走過共產黨學生。有著一顆仁愛溫厚的心。
被捕又被放回的弗之的心理活動,歷來被研究者關注。這一大段內心活動的描寫,帶領我們深入到這個人物的內心靈魂深處。“這一晚弗之想了很多,他被帶走時,心里是一片空白。當時各種思想很活躍,罵政府的也很多,他是再溫和不過了,怎么會攤上了被捕?莫非是綁票?可是也還沒有當‘票的資格,看這兩個人似乎也不是土匪。……天漸漸黑得沉重,壓得人透不過氣來,不時需要大口喘氣。他努力調整呼吸,想無論如何要應付這局面,不能暈倒。
“當時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簡直像一場夢,沒想到這么快就能回來,時間雖不長,可足夠長記不忘。若只是對他一個人,還簡單些,不過既然有這樣的行動,以后很難說。學界安危實堪憂慮,因為他教修身課,有些學生認為他幫助政府壓制思想自由,因為他以史借鑒,當局又認為他幫助另一方面,要想獨立地走自己的路,是多么艱難。他覺得自己好像走在獨木橋上,下臨波濤,水深難測。他頭暈,伸手去拉了一下碧初。‘勿使蛟龍得,他想起這詩句,深深嘆息。碧初輕輕拍拍他,柔聲道:‘睡吧,睡吧。‘只要自己問心無愧,哪管得了許多。弗之這樣一想,漸漸迷糊睡去。”⑨
這一段非常真實。想來對作者來說,這段記憶也是刻骨銘心的。在修辭上,作者是照實寫來,弗之的恐懼不安、胡思亂想,都很逼真,表現出了高超的現實主義手法的魅力。一句“勿使蛟龍得”,終將解釋這個人物的一生。這便是他與江昉的根本區別,命運的走向因此變得可測了。
與之有聯系的是,馮友蘭先生親歷過被捕事件。這在他的《三松堂自序》等書中都有記載。1934年,馮友蘭先生訪問蘇聯之后,對蘇聯大加贊賞。被莫名其妙地關進保定公安局,幾天后才得以釋放。應該說,這一事件對馮友蘭先生此后政治、哲學的立場是一個分水嶺。他開始認同辯證唯物主義。有名的“正反合說”即是之后的哲學觀點。
因敘述者對這個人物的情感及人物所承擔的知識分子主題成分,有一些描寫顯得用力過猛,過于生硬地拔高人物。比如:弗之一家去素初家拜壽,親人團聚。忽然說到鴉片煙,本來素初抽鴉片也頗尷尬,弗之將話題接過發揮成如下:
“若說鴉片是一種武器也可以,”停了一會,弗之笑道,“只是這槍口是向內的,我們真的秘密武器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只管向前,永不停止:御外侮,克強敵,不斷奮斗,是我們的歷史。《易經》上乾、坤兩卦的象傳,有兩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是對乾、坤兩卦的一種解說詞,也是古人的人格理想。君子要像天一樣永遠向前行走,像地一樣承載一切,包容一切。”⑩
讀來令人深覺知識分子的迂腐。因這一大段并沒有前后文上下語境,顯得非常突兀、生硬,情緒也不在恰當時候。如果作者此時借機幽默一把,輕微地反諷一下人物的不知場合,也許這個人物反而更真實了。然而,敘述者的下文卻是:大家都有感動。這一段就硬生生成了帶有說教意味的、孟教授自己的演講。只可惜演講的場合卻是團聚的家宴。也許對敘述者來說,這些涉及形而上的莊嚴話題是不能拿來取笑的,但有時一味莊嚴崇高,不分場合,也會顯得不真實。“普魯斯特對發散性和部分自我否定的人物形象的描繪,被經常稱贊為逼真地呈現人類自身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性。”11人物形象應該是多維的,不能簡化為單維的、單一的功能。這也是為什么弗之看起來遠不如錢明經、白禮文等更像小說人物。與前者比起來,錢、白都有著顯著的個人性格特征。錢明經好色輕浮,白禮文則澆漓無行。但有缺點的人,幾乎能立刻讓讀者認同他的真實性,一個古怪的人則常常是有趣的。如狄更斯筆下的人物,幾乎都是性格怪僻偏執的人物。當然,歷來有疵點的壞人顯得更有個性更好寫,好人難寫也是千古難題。連《白癡》中的梅什金伯爵也向來被認為不如他的邪惡的對手刻畫得好。
敘述者關于孟弗之的真實“心曲”,在《南渡記》第一章末尾插入的《野葫蘆的心》中有集中傾訴。文章以孟的口吻講了一個野葫蘆的故事。似乎在揭示整部小說的題旨。雖然小說中是孟弗之向孩子們說,但讀者都會接過這個訴說,認為是在向我們——讀者說。
“許多事情讓人糊涂,但祖國這至高無上的詞,是明白貼在人心上的。很難形容它究竟包含什么。它不是政府,不是制度,那都是可以更換的。它包括親人、故鄉,包括你們所的。它包括親人、故鄉,包括你們所依戀的方壺,我傾注了半生心血的學校,包括民族拼衍的歷史,美麗豐饒的土地,古老輝煌的文化和沸騰著的現在。它不可更換,不可替代。它令人哽咽,令人覺得流在自己心中的血是滾燙的。”12這一段文字,歷來被研究者引用,認為是整部小說抗日愛國情懷的集中體現。接著又有一段,從祖國傾訴到個人——自己,孟弗之的自我靈魂剖析:“我其實是個懦弱的人,從不敢任性,總希望自己有益于家國、社會,有益于他人,雖然我不一定能做到。我永遠不能灑脫。所以十分欽佩那堅貞執著的秉性,如那些野葫蘆。”最終指回題旨——野葫蘆。
那么“野葫蘆”到底喻指了什么。劉心武在《野葫蘆的夢》中說:“葫蘆在野,本非中心人物,又怎能要求它們過高?葫蘆其實常與糊涂通解,從野處望中心,‘許多事讓人糊涂(難得糊涂!),但在維護一種自源頭而來的文化這樣的關鍵問題、大是大非上,野葫蘆又的確是極堅韌堅貞堅強堅毅的。”野葫蘆象征著那些不在權力中心的知識分子,他們寧愿在邊緣生機勃勃地守護著自己的文化價值。這就是孟樾的心曲,也是整部小說知識分子主題所要達到的題旨。當然,孟弗之也表達過,同樣是向蕭澂:我的抱負是學問與事功并進。這就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矛盾,簡而言之就是入世與出世的矛盾。
在《北歸記》接近尾聲時,敘述者還是忍不住讓孟弗之親上講臺講了烏臺詩案。結合小說內外來看,這個細節都似乎在辯解什么。“大才如蘇軾,也不得不這樣說,而且是這樣想的,這是最最讓人痛心的。千百年來,皇帝掌握億萬人的命運。國家興亡全憑一個人的喜怒。一個人的神經能擔負起整個國家的重任嗎?神經壓斷了倒無妨,那是個人的事,整個國家的大船就會駛歪沉沒。”13馮友蘭先生在64歲時寫了《四十年的回顧》一書,時在1959年,對自己早期學術生涯進行了自我否定式的檢討。以及另一些關涉“文革”的公案,是近年來,馮友蘭先生招致批評的原因。結合這些文本外的事件,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何以作者要這么寫,要在這里寫這一情節。
把人物線索揀出來,會發現一些形象是圍繞著孟樾而設置的。錢明經的浮浪襯托出孟樾的端方;蕭澂、李漣的右傾跟孟樾的“左傾”形成對比;在更加激進的江昉那里,孟樾又代表學校的官方正統立場;《北歸記》出現了社會學家劉仰澤,他是繼江昉之后新的政治激進派。敘述他在云南考察時跪在了原始部落頭人恫嚇的刀前,在屠刀面前,人們的自然表現誰也好不了多少。是孟樾被抓的襯寫。白禮文澆漓無行卻一再受到孟樾的提攜賞識,寫出這個人物的愛才與寬厚;同樣愛才于尤甲仁。顯然敘述者對于這一對夫妻過于直白的挖苦揭露,一反作者一貫含蓄溫和的文風,實在像是對這一對人物有極深的心結。塞米利安曾說,一個作家最喜歡的和最恨的人往往寫得最好。從這個角度來說,拋開作者的心結,這一對人物的刻薄細節,有的地方倒也顯得較為生動;跟莊卣辰、李漣等在1949年的“走”對比,孟樾是“留”的一方。這大關節的選擇最后昭示出他的愛國情懷,從而完成從《南渡記·野葫蘆的心》開始的人物形象塑造。
截至《北歸記》為止,孟弗之的形象就是這樣完整地呈現了。因大部分時候記史實錄的寫法,致使虛構成分少;缺點也因太重“史”錄,形象缺乏集中性、人造性以及戲劇性。作為“四記”的小說人物,大喜大悲跌宕起伏之類的美學風格不是它的特點,但讀者卻因此收獲了當代知識分子文化史的深刻內涵。
【注釋】
①參見[希臘]亞里士多德著:《詩學》,陳中梅譯注,商務印書館,2005,第65頁。
②[美]利昂·塞米利安著:《現代小說美學》,宋協立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141頁。
③劉心武:《野葫蘆的夢》,《粵海風》2002年第5期,第43頁。
④⑤趙園:《艱難的選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第142、121頁。
⑥12宗璞:《南渡記》,載《宗璞文集》(第三卷),華藝出版社,1996,第47、39頁。
⑦⑧⑨⑩宗璞:《東藏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第238、209、282、25頁。
11[法]熱拉爾·熱奈特著:《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王文融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182頁。
13宗璞:《北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第221頁。
(何英,新疆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