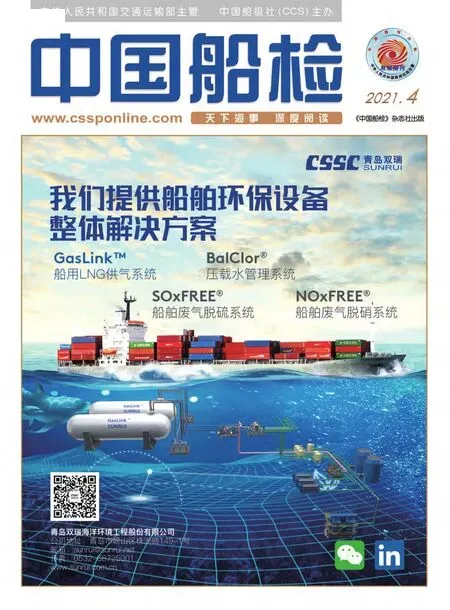協(xié)同治理視角下海員作息時(shí)間履約機(jī)制優(yōu)化研究
崇明海事局 丁寶喜
多管齊下,是否能“破局”海員作息時(shí)間履約困境?

世界海事大學(xué)的研究報(bào)告指出了海員作息時(shí)間履約的系統(tǒng)性失效性問題,引發(fā)了航運(yùn)界的強(qiáng)烈反應(yīng)。如何破解這一“痼疾”,保障海員的生命健康權(quán)益,減少海上疲勞問題的產(chǎn)生,是目前航運(yùn)界急需解決的問題。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背景下,海員作息時(shí)間的履約問題已然成為一個(gè)全球性的治理議題,需要國際海事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各締約國政府、行業(yè)組織、航運(yùn)企業(yè)和海員群體的協(xié)同配合。
在《現(xiàn)行海員作息時(shí)間履約機(jī)制的系統(tǒng)性失效分析》(《中國船檢》2021年第2期)一文中,筆者從執(zhí)行者、推動(dòng)者和監(jiān)督者三個(gè)角度對海員作息時(shí)間履約機(jī)制系統(tǒng)性失效背后的原因進(jìn)行了分析,多重因素綜合導(dǎo)致履約第一環(huán)執(zhí)行者嚴(yán)重違規(guī)、逐利性使得推動(dòng)者長期漠視海員作息時(shí)間問題、利己選擇使得監(jiān)督者沒有起到應(yīng)有的監(jiān)督作用。在協(xié)同治理視角下,如何從上述三個(gè)維度進(jìn)行“破局”,如何“激活”現(xiàn)行海員作息時(shí)間履約機(jī)制,可以從以下幾個(gè)方面展開:
鼓勵(lì)海員使用人為因素不安全事件保密報(bào)告系統(tǒng)報(bào)告違規(guī)行為
制定海員作息時(shí)間相關(guān)規(guī)定的初衷,是為了保護(hù)在船工作的海員的勞動(dòng)權(quán)益。如今,出于在不對等就業(yè)環(huán)境中的自我保護(hù)、加班費(fèi)、對現(xiàn)行檢查機(jī)制的不信任等因素促使作為執(zhí)行者的海員在海員作息時(shí)間的記錄方面進(jìn)行造假。因此,如何調(diào)動(dòng)海員準(zhǔn)確的記錄海上的作息時(shí)間的積極性,打消海員舉報(bào)任何違反海員作息時(shí)間事件的顧慮,是海員參與海員作息時(shí)間履約機(jī)制治理的解決之道。
《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規(guī)則5.1.5部分和5.2.2部分就船上的投訴程序和海員投訴的岸上處理程序分別作出了規(guī)定。但是,無論是船上的投訴程序,還是岸上的處理程序,都在尋求盡可能的達(dá)到“努力促成在船舶層面上解決投訴”的效果。這就使得,投訴程序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只能成為停留在紙面的“僵尸”條款,除非海員決意放棄工作。對此,鼓勵(lì)海員使用保密程度較高的人為因素不安全事件保密報(bào)告系統(tǒng)(CHIRP ,Confidential Human Factors Incident Reporting Programme)。海事CHIRP人為因素不安全事件保密報(bào)告系統(tǒng)于2003年7月開始運(yùn)行,最初是由英國政府資助,目前已轉(zhuǎn)由領(lǐng)港公會(huì)、勞氏船級社和布列塔尼亞保賠協(xié)會(huì)提供資助。當(dāng)前組織的董事會(huì)由9名成員組成,其中有獨(dú)立的資深船長、還有來自英國航運(yùn)協(xié)會(huì)、國際海事局和英國海事與海岸警衛(wèi)署的首席要員。所接收的報(bào)告的個(gè)人信息不會(huì)被留存,在核實(shí)報(bào)告所涵蓋的所有相關(guān)信息后,所有的個(gè)人信息將會(huì)反饋至報(bào)告者以作接收確認(rèn)信。每份報(bào)告都會(huì)有唯一的標(biāo)識(shí)碼。在退還個(gè)人信息后,系統(tǒng)會(huì)粉碎原有的聯(lián)系信息,即無法再聯(lián)系報(bào)告人,除非報(bào)告人自愿通過報(bào)告的唯一標(biāo)識(shí)碼向系統(tǒng)提供額外信息。
航運(yùn)公司應(yīng)培樹安全文化、開展海上疲勞項(xiàng)目管理
作為海員作息時(shí)間履約的推動(dòng)者,航運(yùn)公司應(yīng)從安全文化塑造和海上疲勞項(xiàng)目管理開展方面進(jìn)行努力。
安全文化方面,公司應(yīng)及時(shí)獲取和解決來自船上的有關(guān)海員作息時(shí)間方面的反饋或者增加額外配員方面的正當(dāng)請求。結(jié)合海員的反饋,公司要定期評估船舶的配員是否滿足實(shí)際的用工需求。在諸如過運(yùn)河和重大維護(hù)保養(yǎng)等非常規(guī)事件時(shí),應(yīng)提前主動(dòng)增加配員。此外,公司應(yīng)充分授權(quán)他們的岸上指定人員(DPA),就建立有效、可靠的反饋機(jī)制發(fā)起實(shí)質(zhì)性變革,就船舶操作官僚化及其對船舶安全、船上工作條件的影響開展研究。應(yīng)調(diào)整內(nèi)部審核指南,使之成為一個(gè)名副其實(shí)的評估安全性的有效工具,而不僅僅是紙上談兵。海上疲勞管理項(xiàng)目開展方面,公司應(yīng)該培訓(xùn)他們的岸基管理人員和決策人員,使他們意識(shí)到人為因素的重要性和海上疲勞對船舶安全、海員職業(yè)健康的危害性,并能夠提供相關(guān)的證據(jù)來佐證相關(guān)培訓(xùn)的開展情況。
主管機(jī)關(guān)應(yīng)采取多種措施履行監(jiān)督者責(zé)任
作為監(jiān)督者的船旗國主管機(jī)關(guān)和港口國主管機(jī)關(guān),通過人防、技防和物防多維度履行監(jiān)督者的責(zé)任。
人防方面,主管機(jī)關(guān)應(yīng)對所屬的檢查官開展專門培訓(xùn),提升其在甄別海員作息時(shí)間違規(guī)行為方面的能力和技能。并通過培訓(xùn),使得檢查官對人為因素的重要性、不充分的休息對海上安全的危害性的認(rèn)識(shí)提升一個(gè)臺(tái)階;技防方面,應(yīng)給船旗國檢查官和港口國檢查官配備專門的軟件工具,用以甄別海員作息時(shí)間記錄違規(guī)行為。這種軟件應(yīng)以培訓(xùn)做支撐,具體可以參照MARPOL公約附則I的燃油消耗計(jì)算軟件為模板;物防方面,主管機(jī)關(guān)應(yīng)更新供檢查官使用的檢查指南,將如何系統(tǒng)性確認(rèn)海員作息時(shí)間記錄的準(zhǔn)確性納入指導(dǎo)手冊,并將兩班倒工作機(jī)制視為可觸發(fā)詳細(xì)檢查的“明顯理由”,將作息時(shí)間記錄方面的缺陷作為確定ISM規(guī)則不符合項(xiàng)的重要來源。
此外,港口國檢查組織和區(qū)域港口國檢查組織應(yīng)該開展針對海員作息時(shí)間記錄的檢查會(huì)戰(zhàn)(CIC),對世界海事大學(xué)報(bào)告中揭露的海員作息時(shí)間履約失效性問題重拳出擊。在CIC集中檢查之外,應(yīng)允許常規(guī)的PSC檢查開展重點(diǎn)檢查。重點(diǎn)檢查中,交叉檢查應(yīng)允許通過風(fēng)險(xiǎn)評估或者任意的方式開展。例如,現(xiàn)行的港口國監(jiān)督檢查機(jī)制應(yīng)通過修改他們的選船辦法,以提高針對使用兩班倒工作制(0-6和6-12的在船工作機(jī)制)的船舶的海員作息時(shí)間記錄的檢查率。
國際組織應(yīng)對相應(yīng)的文書進(jìn)行修訂
(1) 對港口國監(jiān)督程序作出修改
國際海事組織第1138(31)號大會(huì)決議通過了《2019年港口國監(jiān)督程序》,成為各國政府在行使港口國監(jiān)督時(shí)新的準(zhǔn)繩。其2.4部分,對可以觸發(fā)更詳細(xì)檢查的“明確依據(jù)”進(jìn)行了列舉,具體見表1。

表1 2019年港口監(jiān)督程序中的明確依據(jù)
M.Lützh?ft等人、P.Maurier等人、P.Tucker等人和英國的海事調(diào)查局的研究報(bào)告對兩班倒的工作機(jī)制的危害性進(jìn)行了研究,建議將“兩班倒”工作機(jī)制納入《2019年港口國監(jiān)督程序》2.4部分的“明確依據(jù)”中。換句話說,對待采用“兩班倒”工作機(jī)制的船舶,直接開啟“更詳細(xì)檢查”模式。
(2)對《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中的“補(bǔ)償性休息”進(jìn)行解釋說明
規(guī)則2.3部分提及,“在一海員處于隨時(shí)待命情況下,例如機(jī)艙處于無人看管時(shí),如海員因被招去工作而打擾了正常休息時(shí)間,則應(yīng)給予充分的補(bǔ)休”。但是,并未對補(bǔ)休進(jìn)行解釋說明,相應(yīng)的導(dǎo)則部分中也未就如何補(bǔ)休給出建議或指導(dǎo)。對此,應(yīng)作出修訂,對“補(bǔ)償性休息”的方式、方法以及相應(yīng)的記錄保存給出統(tǒng)一的解釋和說明,以指導(dǎo)成員國采取統(tǒng)一的行動(dòng)。
(3)對STCW公約中的“其他重要操作”進(jìn)行限制說明
《經(jīng)修訂的1978年船員培訓(xùn),發(fā)證和值班公約》(STCW公約)A-VIII/1.4部分規(guī)定:“在緊急情況或者其他重要操作時(shí),有關(guān)作息時(shí)間方面的規(guī)定可不必遵守。按照國內(nèi)法規(guī)和國際公約進(jìn)行的應(yīng)變部署、消防和救生演習(xí)應(yīng)以對海員的休息產(chǎn)生最小的干擾的方式進(jìn)行,并不能導(dǎo)致疲勞的產(chǎn)生。”常規(guī)的講,船上對緊急情況的理解不會(huì)出現(xiàn)太大的偏差。但是,“其他重要操作”卻給海上作息時(shí)間條款的遵守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間。對此,建議對公約中“其他重要操作”進(jìn)行限制性的說明,防止這一條款被濫用。
(4)不同公約中關(guān)于海員作息時(shí)間規(guī)定的應(yīng)予以統(tǒng)一
在《海員作息時(shí)間記錄造假與海上疲勞問題研究》(《航運(yùn)交易公報(bào)》2020年12月第3期)一文中,筆者對現(xiàn)行的國際公約體系中關(guān)于海員的工作和休息時(shí)間的有關(guān)規(guī)定進(jìn)行了梳理。但是,對《經(jīng)修訂的1978年船員培訓(xùn),發(fā)證和值班公約》(STCW公約)和《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中的條款進(jìn)行比較發(fā)現(xiàn),二者在關(guān)于海員作息時(shí)間方面的規(guī)定并不一致。從任何7天內(nèi)允許的最長工作時(shí)間維度,《STCW公約》中規(guī)定為最長工作時(shí)間可達(dá)91小時(shí),但在《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卻表現(xiàn)為72小時(shí);從任何7天內(nèi)允許的最短工作時(shí)間的維度看,《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自身規(guī)定的時(shí)間為96小時(shí)或77小時(shí)。具體情況詳見表2。

表2 《STCW公約》和《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作息時(shí)間對比

對此,建議國際海事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應(yīng)在作息時(shí)間方面的規(guī)定方面加強(qiáng)溝通,并通過修訂保持一致。
對ISM規(guī)則進(jìn)行修訂
在《飽受詬病的船舶記錄調(diào)整文化》(《中國船檢》2021年第1期)一文中,筆者將ISM規(guī)則的實(shí)施導(dǎo)致書面工作量激增視為海員調(diào)整船舶記錄方面的根本原因。大量的文書工作,占據(jù)了海員的大量時(shí)間和精力,使海員為了應(yīng)付層出不窮的文書工作而陷入極度疲勞的境地。因此,回歸安全這一“初心”,對ISM規(guī)則進(jìn)行結(jié)構(gòu)性重構(gòu),從根源上減少船上的文書工作,是優(yōu)化海員作息時(shí)間履約機(jī)制的必經(jīng)之路。
此外,開展ISM外部審核時(shí),船旗國主管機(jī)關(guān)的審核員不應(yīng)只專注于書面文件的檢查,應(yīng)豐富數(shù)據(jù)收集的手段,例如鼓勵(lì)采用與海員私密會(huì)談的方式。在ISM符合證明換新時(shí),審核員還應(yīng)就ISM記錄開展交叉檢查,并就反饋機(jī)制的有效性開展驗(yàn)證。
正如扎德克(Zadek S.)指出的那樣,“協(xié)同治理是有效應(yīng)對環(huán)境和社會(huì)挑戰(zhàn)的共同趨勢,是全球性的趨勢,沒有替代方案”。作為一個(gè)全球性的治理議題,海員作息時(shí)間系統(tǒng)性失效問題的有效解決必須走協(xié)同治理的道路。只有各個(gè)參與主體作出相應(yīng)的改變,執(zhí)行者認(rèn)真執(zhí)行,推動(dòng)者樂于推動(dòng),監(jiān)管者盡職監(jiān)督,制度機(jī)制適時(shí)調(diào)整,海員作息時(shí)間履約問題才能真正回歸“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