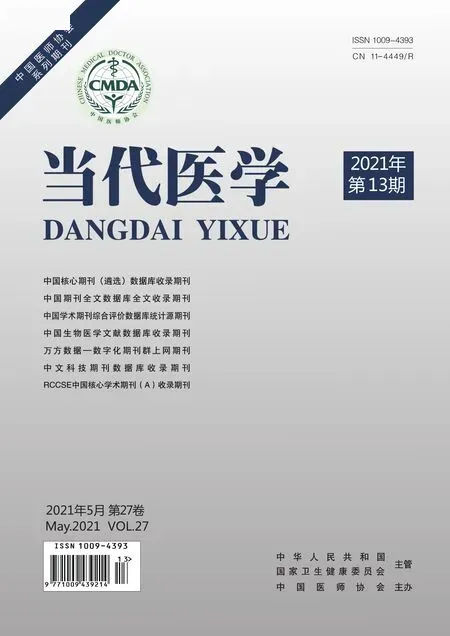3D打印技術(shù)在前交通動脈瘤治療中的應(yīng)用
王金鵬
(九江市第一人民醫(yī)院,江西 九江332000)
前交通動脈瘤是顱內(nèi)所有動脈瘤中最常見的一種類型,其病因與動脈硬化、腦動脈閉塞與顱內(nèi)血管發(fā)育不良等相關(guān)[1],因致殘率和致死率較高,患者需盡快行手術(shù)治療,避免動脈瘤破裂出血威脅患者生命安全。雖然,國內(nèi)外已首選開顱動脈瘤夾閉術(shù)治療前交通動脈瘤患者,但前交通動脈解剖結(jié)構(gòu)復(fù)雜,治療難度較大,無法保證療效。3D打印技術(shù)是一種迅速成型技術(shù),操作原理是在數(shù)字模型文件基礎(chǔ)上,通過計算機軟件構(gòu)建出3D模型,以便醫(yī)護人員對患者的顱內(nèi)組織結(jié)構(gòu)與病變情況進行觀察,從而開展下一步的手術(shù)治療[2]。本研究旨在探究3D打印技術(shù)在前交通動脈瘤治療中的應(yīng)用效果,現(xiàn)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選取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本院收治的前交通動脈瘤患者30例作為對照組,并選取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本院收治的前交通動脈瘤患者30例作為觀察組。對照組男16例,女14例;年齡50~76歲,平均年齡(65.21±1.58)歲;動脈瘤大小:微小型(≤3 mm)15例,小型(3~9 mm)13例,大型(10~25 mm)2例;Hunt-Hess分級:Ⅰ級11例,Ⅱ級12例,Ⅲ級4例,Ⅳ級3例。觀察組男18例,女12例;年齡51~75歲,平均年齡(66.05±1.50)歲;動脈瘤大小:微小型(≤3 mm)14例;小型(3~9 mm)12例;大型(10~25 mm)4例;Hunt-Hess分級:Ⅰ級13例,Ⅱ級10例,Ⅲ級5例,Ⅳ級2例。兩組患者臨床資料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通過醫(y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
納入標準:經(jīng)影像學(xué)檢查確定為前交通動脈瘤;行雙側(cè)頸動脈造影檢查過程中,前交通動脈顯影不完整;患者家屬均對本研究知情同意,并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合并重度頸動脈狹窄患者;合并血液系統(tǒng)疾病者;合并肝腎功能障礙者。
1.2 方法兩組均接受開顱動脈瘤夾閉術(shù)治療,治療過程中,對照組不使用3D打印技術(shù)。觀察組應(yīng)用3D打印技術(shù)構(gòu)建出模型后再開展治療:使用膠帶與頭托固定患者頭部,并通過CT做峰值法容積掃描處理,參數(shù)設(shè)置:間距與層厚各為0.625 mm,矩陣512×512,電壓120 kV,視野220 mm,電流200 mAs。由患者顱底依次掃描至顱頂,采集數(shù)據(jù)后測定峰值;同時,應(yīng)用CT專用高壓注射器,經(jīng)外周左肘正中靜脈使用20G套管針注入10 mL 0.9%氯化鈉溶液與15 mL碘海醇非離子造影劑,注射速度控制在4.5 m/s,在獲取達峰時間后將2 s經(jīng)驗值設(shè)置為正式增強掃描時間,并以相同的速度將20 mL 0.9%氯化鈉溶液、65 mL對比劑注入患者右肘正中靜脈,在增強掃描后上傳原始數(shù)據(jù)至電子計算工作站。在Mimics軟件中導(dǎo)入圖像數(shù)據(jù),通過閥值法提取患者動脈瘤血管閾值,以結(jié)合3D計算工具構(gòu)建出動脈瘤模型;同時,借助Mimics Cut with Polyplane工具干預(yù)處理動脈瘤模型,在立體光刻格式導(dǎo)出后取出動脈細小分支,對圖像做3D計算處理,以生成動脈瘤面網(wǎng)優(yōu)化模型,最后使用3D打印機構(gòu)建出動脈瘤血管固定模型。
1.3 觀察指標比較兩組術(shù)前準備時間與術(shù)中操作時間;比較兩組術(shù)前、術(shù)后GCS評分,該量表包括睜眼、言語與運動3個項目,以患者評分劃分昏迷程度,輕度:13~14分,中度:9~12分,重度:3~8分[3]。
1.4 統(tǒng)計學(xué)方法采用SPSS 20.0統(tǒng)計軟件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計量資料以“±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
2 結(jié)果
2.1 兩組術(shù)前準備時間與術(shù)中操作時間比較觀察組術(shù)前準備時間與術(shù)中操作時間均短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兩組術(shù)前準備時間與術(shù)中操作時間比較(±s)

表1 兩組術(shù)前準備時間與術(shù)中操作時間比較(±s)
?
2.2 兩組術(shù)前與術(shù)后GCS評分比較術(shù)前,兩組GC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術(shù)后,兩組GCS評分均高于治療前,且觀察組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術(shù)前與術(shù)后GCS評分比較(±s,分)

表2 兩組術(shù)前與術(shù)后GCS評分比較(±s,分)
?
3 討論
由于患者顱內(nèi)動脈瘤形狀、大小等存在差異,且前交通動脈復(fù)合體解剖結(jié)構(gòu)復(fù)雜,在單側(cè)頸內(nèi)動脈造影過程中,諸多因素均可限制開顱動脈瘤夾閉術(shù)的順利開展,如部分患者的交通動脈無法顯影或顯影效果不佳等[4]。因此,需要采取相應(yīng)的技術(shù)以減少其中存在的誤差,改善患者預(yù)后。
3D打印技術(shù)因具有迅速成型、直觀立體等特點在醫(yī)學(xué)模擬領(lǐng)域(生物組織材料與人工血管等)中已得到廣泛應(yīng)用,其優(yōu)勢為術(shù)前應(yīng)用構(gòu)建出3D模型,以便臨床醫(yī)護人員了解患者組織器官的解剖特點、變異情況,并分析動脈瘤整體與血管間的解剖關(guān)系,在此基礎(chǔ)上模擬手術(shù)操作,對手術(shù)治療方案進行設(shè)計與調(diào)整,從而縮短術(shù)前準備時間,提升手術(shù)操作精準性與療效[5]。本研究結(jié)果顯示,觀察組術(shù)前準備時間與術(shù)中操作時間均短于對照組(P<0.05)。提示,3D打印技術(shù)有利于醫(yī)護人員進行術(shù)前準備,并縮短手術(shù)操作時間。分析原因為術(shù)前應(yīng)用3D打印技術(shù)可構(gòu)建患者的動脈瘤3D模型,可全面分析與評估動脈瘤組織關(guān)系,并以此為依據(jù)模擬選擇動脈瘤夾與分離瘤頸等手術(shù)操作,在此過程中,醫(yī)師間可針對手術(shù)操作展開深入的分析與討論,以明確手術(shù)治療方向,并縮短術(shù)前準備時間。此外,術(shù)前談話會使患者與家屬情緒過度緊張,再加上抽象的醫(yī)學(xué)名詞,患者與家屬難以認識到手術(shù)治療的迫切性。而3D模型能直接反映出患者的實際病情與病變程度,一方面有利于醫(yī)患間進行高效溝通,以便醫(yī)師為患者家屬詳細講解病情與手術(shù)治療方法,獲得患者的支持與配合;另一方面可幫助患者完善術(shù)前準備,讓患者以最佳狀態(tài)進行手術(shù)治療,為良好預(yù)后提供保障;同時,手術(shù)治療過程中,3D模型經(jīng)消毒處理后能放置于手術(shù)臺,可使手術(shù)醫(yī)師多角度、全方位旋轉(zhuǎn),對術(shù)中觀察動脈瘤瘤體的朝向與評估顱骨的解剖關(guān)系均可提供指導(dǎo)[6],有利于手術(shù)醫(yī)師展開各項操作,從而縮短手術(shù)時間,并減少術(shù)中組織解剖的暴露。本研究結(jié)果顯示,術(shù)前,兩組GC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術(shù)后,兩組GCS評分均高于治療前,且觀察組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提示,雖然應(yīng)用開顱動脈瘤夾閉術(shù)治療后,前交通動脈瘤患者的意識障礙已得到改善,但觀察組改善效果更佳。分析原因為3D模型具有直觀、逼真的視覺效果,對手術(shù)方案的設(shè)計具有積極作用,可保證手術(shù)方案符合患者的病情,減少方案設(shè)計上存在的誤差,為患者術(shù)后恢復(fù)提供幫助[7]。此外,在治療過程中,3D模型可發(fā)揮輔助參考作用,即手術(shù)醫(yī)師可參照3D模型對患者動脈瘤進行準確定位,并以此為依據(jù)選擇最佳的路徑開展治療操作,從而保護患者的重要血管,避免手術(shù)操作損傷血管,確保患者治療后意識狀態(tài)恢復(fù),提升預(yù)后質(zhì)量[8-9]。此外,3D打印技術(shù)有利于臨床醫(yī)師進行手術(shù)回顧,并結(jié)合手術(shù)錄像與3D模型總結(jié)經(jīng)驗,針對其中的不足做出相應(yīng)的改進,確保3D打印技術(shù)今后可更好的應(yīng)用于臨床手術(shù)治療中。
綜上所述,在前交通動脈瘤患者治療中應(yīng)用3D打印技術(shù),有利于臨床醫(yī)師通過構(gòu)建的3D模型全面觀察患者動脈瘤組織結(jié)構(gòu),進而完善術(shù)前準備,在模型的指導(dǎo)下順利開展治療,保障患者預(y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