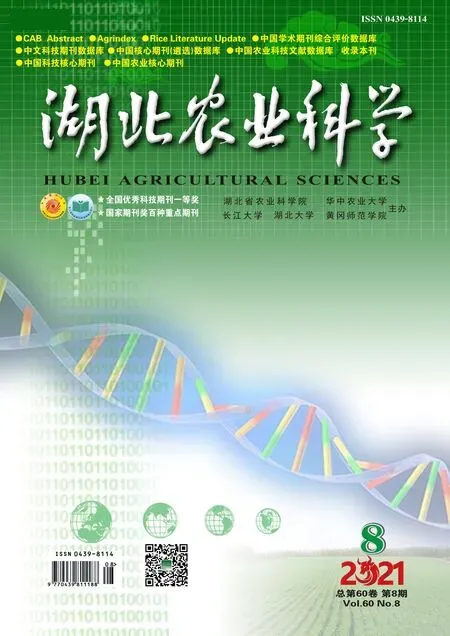金沙江流域生態脆弱性評價
尚嘉寧,邵懷勇,李 峰,歐陽欣
(成都理工大學地球科學學院,成都 610059)
金沙江流域地跨青藏高原、川西北高原、川西南山地等幾大地貌單元,既是長江流域的生態屏障,也在長江經濟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不合理的發展模式存在一定弊端,再加上流域內自然條件復雜,土地退化、地質災害頻發等生態問題[1-3]的嚴峻考驗隨之而來,流域的生態保護作用不僅得不到充分發揮,造成的壓力反而對流域生態系統恢復、發展起到阻礙作用。因此,重視該流域的生態環境十分必要。但目前有關金沙江流域的研究[4-7]大多基于微觀角度,鮮見綜合性研究,因而基于金沙江流域復雜的人類-環境生態系統開展生態脆弱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人口、能源和環境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引起了人們對生態環境的重視,推動了生態脆弱性研究的發展。區域生態脆弱性評價有助于人們客觀、全面地了解當地環境的脆弱程度及其變化趨勢,從而可以有針對性地實施益于區域環境脆弱性改善的環境規劃。國內外學者們已運用多種方法[8-18]對區域生態脆弱性開展了量化分析及動態監測,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空間主成分分析能夠得到個數較少卻包含信息較多的幾個綜合特征指標,不僅可以保留絕大部分指標信息,而且減少了主觀性對評價結果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優勢。
為此,本研究通過GIS 和RS 技術,基于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理念,耦合地形、氣候、覆被和人類活動等因素,運用空間主成分分析法對金沙江流域2005—2015 年生態脆弱性進行動態監測、評價及分級,進一步分析該流域生態脆弱性時空變化格局,從而為構建金沙江流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和利用框架奠定理論基礎。
1 研究區概況
金沙江流域(24°—36°N,90°—105°E)地處長江流域上游,自西北—東南方向跨青、藏、滇、川、黔5省區,總面積約47.32 萬km2。流域內高原、峽谷、盆地和丘陵縱橫交貫[19],地勢北高南低,上游與下游海拔之差在5 000 m 以上。在多種季風的影響下,流域內氣候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地帶性。受流域地貌、氣候等綜合影響,植被類型的地帶性和多樣性也較為顯著。流域內水能資源、礦產資源和生物資源等方面在中國地位極為重要。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研究采用的數據主要包括3 種。①遙感數據。從美國航天航空局下載MOD13Q1 數據集(分辨率為250 m),采用最大值合成法得到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從地理空間數據云下載季相相近的Landsat 影像(分辨率為30 m),運用支持向量機進行監督分類,得到土地利用數據。②基礎地理數據。DEM 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分辨率為90 m;坡度數據提取自DEM 數據;1∶100 萬土壤類型數據來源于地球系統科學數據共享網;研究區年平均氣溫和年降水量來源于中國氣象科學數據共享服務網,進行空間插值實現數據空間化。③統計數據。包括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均來源于5 省區統計年鑒,需進行數據空間化處理。
本研究數據均采用WGS 1984 地理坐標系和Albers Equal Area 投影坐標系,柵格大小需統一為250 m×250 m。
2.2 生態脆弱性評價方法
2.2.1 評價指標 生態脆弱性評價指標的選取對于評價結果科學性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既借鑒了前人研究成果[20-23],又充分考慮了研究區實際情況,最終從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2 個方面,選取了9 個指標評價金沙江流域生態脆弱性(表1)。

表1 評價指標體系及選取依據
2.2.2 指標標準化 由于各評價指標的單位和意義存在差異,無法直接進行比較,所以需要對以上9 個指標通過標準化來消除量綱,使其數值介于0~10,從而有助于對各指標進行比較。根據指標不同的性質,本研究采用2 種標準化方法。
定量指標需采用極差法來標準化[24,25]。其中,按照指標與脆弱性的關系,又有正向指標與負向指標的區別。前者數值與脆弱性呈正比,包括高程、坡度、平均氣溫、年降水量和人口密度;后者與脆弱性的關系與前者相反,包括NDVI和人均GDP。計算公式[24,25]分別為:

式中,Xi、Xmin和Xmax分別為第i個指標的 實際值、指標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定性指標包括土地利用類型和土壤類型。根據專家知識[24-27]與研究區實際情況,對土地利用類型和土壤類型2 個指標采用分等級賦值的方法實現標準化(表2)。

表2 土地利用類型指標分等級賦值標準
2.2.3 評價模型 空間主成分分析(SPCA)是一種降維的統計方法,使原有多個變量轉換成為少數幾個相互無關的綜合變量,其最突出的優點是在確定指標權重時具有較強的客觀性,能夠較大程度上使得各指標依照數據本身特點和性質而集成,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可減少人為賦予指標權重的主觀性。本研究在對上述9 個評價指標標準化的前提下,再將它們作空間主成分分析處理,結果確定累計貢獻率超過87%的前4 個主成分(PC1、PC2、PC3、PC4)(表3)。在此基礎上,采用生態脆弱性指數(EVI)來定量表達區域生態環境脆弱程度,計算公式[26]為:

式中,wi表示第i個主成分的貢獻率;ri表示第i個主成分。EVI越大,表示生態環境脆弱程度越嚴重。

表3 主成分信息統計
由上述結果可得,研究區 2005、2010、2015 年的生態脆弱性指數計算公式分別如下:

式中,A1至A4、B1至B4、C1至C4分別代表對應年份9 個指標實現空間主成分分析后,得到累計貢獻率大于87%的前4 個主成分。
2.3 生態脆弱性分級
為方便對比EVI,需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24,28],使EVI介于0~10。由于通過上述SPCA 模型計算得到的研究區EVI是連續值,所以可根據數值大小將其劃分為不同的生態脆弱性等級,以便更加直觀、清晰地了解到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分布狀況。目前在生態脆弱性分級中已被學者們廣泛應用的方法之一是自然斷點法,它是一種以聚類思維為基礎的客觀分類方法。因此,本研究基于研究區實際情況并參照前人采用的分級標準[29-31],采用自然斷點法將EVI劃分為5 個等級:潛在脆弱(Ⅰ級,0<EVI≤3.50)、輕度脆弱(Ⅱ級,3.50<EVI≤5.75)、中度脆弱(Ⅲ級,5.75<EVI≤ 6.75)、重度脆弱(Ⅳ級,6.75<EVI≤7.75)和極度脆弱(Ⅴ級,7.75<EVI≤10.00)。
2.4 生態脆弱性綜合指數
在對研究區生態脆弱性指數分級之后,本研究采用生態脆弱性綜合指數(EVSI)來呈現生態環境的整體變化趨勢,以此使得研究區生態脆弱性變化情況可通過定量的形式表達出來,更加明了。計算方法如下[32,33]:

式中,i為評價等級;n為評價等級總數;S為總面積;Pi和Ei分別表示i級脆弱性等級值及等級面積。EVSI與生態環境整體狀況呈反比。
3 結果與分析
3.1 生態脆弱性空間分布與時空變化分析
根據上述生態脆弱性評價方法,得到金沙江流域2005、2010、2015 年的生態脆弱性分級結果(圖1、表4)。
從圖1 可以看出,2005—2015 年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地區差異性較大;極度脆弱區和重度脆弱區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流域下游地區,即云南省昭通市、楚雄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四川省攀枝花市北部及涼山州(涼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寧縣、德昌縣等地;上游地區生態脆弱性普遍較低,生態穩定性相對較好;中下游河谷兩岸坡面比河流流經地區脆弱程度嚴重。2005—2010 年楚雄州北部的極度脆弱區面積有所減少,其中,永仁縣東北部脆弱等級由重度轉為中度,生態環境有了明顯好轉;而昭通市和涼山州交界地區脆弱性由中度發展為重度,昭通市東北部重度脆弱面積有所增加。2010—2015 年重度和極度脆弱區面積減少,潛在脆弱等級面積有所增加,表明這6 年間生態環境質量整體有所提高。
由表4 分析可得,在2005—2015 年不同脆弱性等級的面積占比變化情況分別為:潛在脆弱性面積占比先減少后增加,2010 年比2005 年比重減少了1.26 個百分點,2015 年比 2010 年比重增加了 6.98 個百分點,增加幅度大于減少幅度;輕度脆弱性面積占比先減少后增加,變化幅度較小;中度脆弱性面積占比先增加后減少,2005—2010 年占比增加了1.10 個百分點,2010—2015 年占比減少了6.64 個百分點,減少幅度大于增加幅度;重度脆弱性面積占比呈先增加后減少的趨勢,增加與減少幅度相差不大;極度脆弱性面積占比持續減少,2005—2015 年減少1.18個百分點。研究區潛在脆弱、輕度脆弱和中度脆弱3 個等級占比之和超過了70%,由此可以判斷金沙江流域內生態環境總體處于中等水平。

表4 金沙江流域生態脆弱性不同等級面積統計
由式(7)計算可得,金沙江流域2005、2010、2015年的生態脆弱性綜合指數依次為2.53、2.55 和2.38。自2005 年后的10 年間,EVSI呈先略增長后減小趨勢,表明整體上生態環境較穩定,朝良好趨勢發展,這與研究區長期以來堅持開展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政策有密切聯系。2005—2010 年EVSI增長了0.02,增幅較小,生態環境整體變化不大;2010—2015 年EVSI下降了 0.17,與 2005—2010 年的變化相比,這5 年來的生態環境變化相對較大,局部地區生態環境出現好轉。

圖1 2005—2015 年金沙江流域生態脆弱性分級
3.2 生態脆弱性驅動因子分析
本研究根據空間主成分分析結果確定累計貢獻率達87%以上的前4 個主成分,計算生態脆弱性指數,分析發現,前3 個主成分具有一定規律性:第一主成分中,NDVI的貢獻率遠超過其他指標;第二主成分中,平均氣溫、年降水量的貢獻較大;第三主成分中,坡度和土地利用類型的貢獻率較高。這表明金沙江流域生態脆弱性動態變化過程與其特殊的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息息相關,其中主要驅動因子為NDVI、氣候、坡度和人類活動等。
金沙江流域呈南北狹長形,跨越中國地勢一二級階梯,地形地勢復雜,再加上多種不同季風的作用,流域上、中、下游的氣候、植被覆蓋情況、資源分布等自然條件差異顯著,而自然環境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必然會影響人口分布和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正因為生態脆弱性與這些因素密不可分,所以研究區脆弱性分布地區差異性也較大。流域下游地區地勢相對平緩、雨熱同期、水能豐富,利于發展工、農業和人類居住,但特殊的自然條件和不合理的開發利用方式也會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如金沙江干熱河谷光熱豐富、干熱少雨,植被覆蓋率低,河谷坡面甚為脆弱,伴隨的焚風效應會加劇干旱,使河谷兩岸更加脆弱;人口密集、土地開墾嚴重導致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建設水電站、不盡合理發展工礦業造成嚴重污染等,使得下游地區難以抵御外界干擾、自我恢復,脆弱程度嚴重。而流域河谷內河流流經區域縱深層次生態系統的發展程度較深[1],自我修復和自我更新能力強,因而比河谷兩岸脆弱性低。流域上游為水源涵養生態功能保護區,實行生態工程建設,對生態系統恢復產生了積極作用,因此相對于流域內其他地區,上游生態脆弱性低。
4 小結
本研究通過GIS和RS技術,采用空間主成分分析對金沙江流域生態脆弱性進行了評價,得出以下結論。
1)金沙江流域的生態脆弱性地區差異明顯,上游生態環境良好,中游部分地區較脆弱,下游部分地區脆弱程度較高,河谷兩岸比河流流經地區脆弱性高。流域內生態環境整體處于中等水平,在各脆弱性等級中,輕度脆弱區面積最大,中度脆弱區次之,潛在脆弱區面積占比中等,重度脆弱區又次之,極度脆弱區比重最小。2005—2010年,流域內生態環境脆弱性指數先增加后減小,減小幅度比增加幅度大得多,且自2010 年后的5 年以來,中度、重度和極度脆弱性面積占比均呈下降趨勢,說明生態建設已有成效。
2)2005—2015 年,金沙江流域生態環境總體上有所改善,主要是因為研究時段內堅持綠色發展理念,有效落實生態恢復和環境保護措施。但由于該流域自然條件獨特,并且生態作用和戰略地位不可替代,應該采取更加科學的環境治理方法,使得其生態更具穩定性。對此,本研究建議把握好恢復治理和協調發展兩個關鍵點,提高大源頭生態保護意識,堅持“長江大保護”戰略規劃;因地制宜實施林地、草地工程建設;創新產業模式,優化產業結構。
3)生態脆弱性評價既需要充分考慮研究區自然環境,又不能忽略人類活動方面的影響,涉及土地、植物、河流和人類生產生活等諸多因素。由于多種數據的收集尚存在困難,本研究在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方面有局限性,會對研究結果產生一定影響。因此,構建更加完善的生態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是下一步研究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