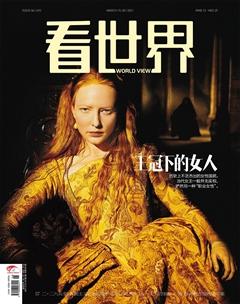美版“三和大神”的真實生活
沙皮狗

本篇圖:《無依之地》劇照
在美國,有這么一些人奔馳在“無依之地”:他們有著自己群體的信仰與規矩,人們像稱呼成吉思汗所率領的民族那樣稱呼他們—游民/游牧者。
“現代游民”游牧般的生活方式,便是《無依之地》這部先后獲得金獅獎和金球獎的電影的看點之一。電影對現代游民的關注,也因切中時代癥候而被各大電影獎青睞。
在電影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輛貨車,滿載家當,周期性出現在全國各地。片中的女主角菲恩說:“我們不是沒家(homeless),我們只是沒房(houseless)。”
傳統游牧VS現代游民
現代游民,好似模仿著傳統游牧民族那樣生活。
他們首先要選一匹自己的馬。在《無依之地》中,每個游民都有一輛自己的貨車。不僅如此,他們還要很認真地給自己的貨車起個名字,就像游牧民族稱呼自己的馬駒一樣。起名,是現代牧民的儀式,是一種生命的認可,使貨車不再是貨車,而是成為“伴侶”一樣的存在。
在電影中,女主角菲恩的貨車出了故障。當修理人告訴她修車的價格不如買一輛新車時,菲恩憤怒地斥責修理人根本不懂這車對她來說不僅是一輛車。
有了“馬”之后,就能效仿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游蕩,當永遠的旅行者。古老的游牧精神呼喚著這批人,讓他們重新反思現代社會的定居生活,反思高額房貸,反思貨幣的價值,反思資本。

“游牧”,或許是逃離現代資本社會僵局的新出口。
現代游民和傳統游牧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現代游民作為游牧者,產生于資本系統內部;而傳統游牧民族,是“長城外”的民族。強大的游牧民族對于帝國來說,就像《權力的游戲》中的夜王,像《進擊的巨人》中墻外的巨人,是一種可怕的威脅。現代游民并不呈現出對抗的姿態,他們誕生于資本系統內部,不在墻外,而在系統內部游蕩。
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對“游牧”這一概念有著高度的關注。他說:新的游牧者并不會(像傳統游牧民族那樣)誕生于“周邊”,因為(全球化的關系)再也沒有“周邊”了。所以,現代游民只能從資本系統內部出現,從系統的主宰中跑出許多小的游民個體,他們的存在是一種對權力的解構。他們不對抗,但也不服從,不合作。
他們生活在荒野,游蕩在人間,但并非完全背離現代社會。從《無依之地》開頭,我們就看到菲恩在資本巨鱷亞馬遜分店打工,現代游民們輾轉于餐廳、中產階級露營地等場所勞動。他們穿上不同的制服,換取貨幣,因為它們的“馬”不吃草,吃汽油,而購買汽油則需要貨幣。盡管他們在一起批判美元,但他們仍被卷入這套美元為首的貨幣系統。這相比我們印象中血氣方剛的傳統游牧民族,似乎有些不著調。
我們從歷史中了解到,游牧民族一大特點便是掠奪。失去了掠奪這一手段的現代游民,實際上已經從“掠奪”變為了“拾穗”,變為了拾荒者。他們甚至還保留著曾經的飲食習慣—喝咖啡,吃罐頭—而非直接從大自然中獲取資源,這些都和真正的游牧民族相去甚遠。
當然,現代游民其實并不全是一場對傳統游牧民族的模仿秀。現代游民不一定總是游蕩的,它甚至是“定居的游民”。德勒茲也曾對現代游民有過描繪:“我想知道我們的社會究竟會制造出什么樣的‘游牧者,如果需要的話,他們甚至是不動和定居的。”
游民們交流個體生存的經驗,交換生存技術,進而幫助個體自哺,即更少地依賴他人。
如果《無依之地》中的游民還保留著“在路上”的習慣—就像導演趙婷在片尾致敬的那樣,那么還存在一種定點的游民,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三和大神”。他們只打日結工,居無定所,每天只要一把掛面滿足生理所需。他們其中有的是迫于無奈,但其實也不乏有人主動去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他們滿足了游牧的另一個特征:沒有包袱,能隨時拍屁股走人。
個人不服從整體
《無依之地》中有這樣一段:所有游民響應游民文化中一位意見領袖的號召,開著自己的房車,像是傳統游牧民族的部落那樣聚到一起。這就是他們的部落。
“游牧”是一種思想,而非身份,也并非游民專屬。
不同于帝國官僚體系,游牧民族的組成方式是一個個小部落,且常常遷徙,組織結構相對松散。如果要找一個與部落相對應的現代治理概念,那就是社區—人們住在一起,互相幫助扶持。但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游民的部落和現代社區治理有著很大的差異。


社區中有不同的職能,有人負責醫療,有人負責教育,有人負責法律顧問,所有的功能分支組成一個有機整體,進而形成社區。這些社區治理規則,背后的邏輯都是為了使這個社區的整體更好發展,整體再反哺個體。
而游牧部落的互助,并非為了整體的發展再惠及個體。部落聚集互助的目標是個體,整體并不重要。在《無依之地》中,戴夫教菲恩簡單開罐的方法,并給了她好用的工具。游民們交流個體生存的經驗,交換生存技術,進而幫助個體自哺,即更少地依賴他人。在這里,個體的獲益并非來自整體,而來自個體更全面的進化。假如有一天部落徹底消失了,也絲毫不會影響游民的個體生存。
自給自足的精神內核
我們會在《無依之地》中聽到許多牧民的生活實用技能。比如,你必須學會自己處理自己的屎尿,因此你要學會用適合你的塑料桶。DIY文化就是游民文化的核心之一。
20世紀上半葉,美國有些雜志會刊登各類有用的手工制作技巧,比如修屋子、修家具、制作新玩具等等。到了20世紀下半葉,DIY不再局限于“自制”或者“技能”一類的實用層面,而上升為一種文化運動。如今像bilibili、YouTube等視頻網站的教程類視頻更是層出不窮,激起了全民自學熱。包括我們常用到的知乎、下廚房等知識分享型App,無不是受DIY文化的影響。
游牧不只是身份

《無依之地》配角工作照
影片中的“游牧”更注重思想境界而非身份,重要的是我們要找到一種“游牧”的狀態。不一定非要變成“游民”,才能完全實現“游牧狀態”。實際上,游牧狀態是一種對權力的解構。它不是一種針鋒相對的力量,而是一種逃逸的力量。世上從來不存在完美無缺的系統,只要存在某種系統,這個系統就會有裂縫,而抽象層次尋找的“游牧狀態”就會發生于此。
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就是一位系統內的游牧者。維特根斯坦曾勸他一個學生不要來劍橋,因為那里沒有他能呼吸的“氧氣”。學生問維特根斯坦,“那為什么你能在劍橋呼吸呢?”維特根斯坦說:“我能自己制造自己的氧氣。”
“游牧狀態”可發生在方方面面,例如當今的性別觀念逐漸從原先固定的男性與女性,走向流動的性別觀。自媒體時代之初,出版的力量被互聯網技術從傳統出版和媒體行業中解放出來,分發到個人手里,也是一種游牧狀態……游牧狀態意味著對“新”的追求,正如《無依之地》中那位因患癌癥而被宣判只有七八個月壽命的老人所說:“我想要新的感覺。”
游牧,就意味著在蠻荒之地冒險。
自我制造“游牧”境界
但要注意,游牧狀態并非是永久的,它甚至十分短暫。權力和資本系統,永遠不會停下內化“游民”的腳步—就像曾經原子化的小自媒體也會成為新的媒體機構,進而形成新的權力系統。
當最初的游民們放棄了原子化,形成新的體系,最初那種游牧狀態也將隨之消失。但總有固執的游民—《無依之地》中菲恩,就算收到妹妹或是戴夫住下來的邀請,依然無法停下她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和在路上的腳步。另一方面,因為系統總有裂縫,所以總會有新的游民誕生。游牧與穩定,大體上來說總處于一種動態平衡中,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游牧者。
因此“游牧”是一種思想,而非身份,也并非游民專屬。“游牧”的狀態,每個人實際上都能找到,或曾有意或無意地體會過。尤其是對于藝術創作者而言,優秀的藝術家在創作中必須始終處于“游牧狀態”。當藝術家不再“游牧”,就是他最需要警惕的時候。
《無依之地》獲得多項大獎,對趙婷來說是一種表彰,卻也是一種“系統”對“游民”最危險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