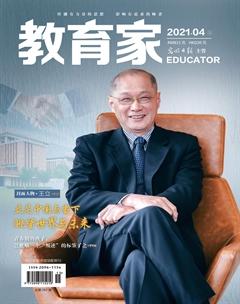從新一代青少年文化理解青春期
朱迪

有人說青春期是美好的花季,也有人說青春期是乖戾的叛逆,叛逆和沖突使得青少年面臨諸多風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青春期泛指11~20歲的青少年時期。就叛逆的表現而言,外顯的有反抗、不聽話,嚴重的發展到反社會行為,而容易忽略的則是拒絕溝通,有的甚至形成心理疾病。在我國精神科就診的患者中,13~17歲發生率最高(15.9%)、18~22歲其次 (13.6%),其他年齡段較少,2000年之后,學齡兒童的心理疾病患病率呈逐漸上升趨勢。
那么,應如何理解這一階段表現出來的“叛逆”,僅僅是青春期發育的生理特征,還是有著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因素?家長和社會又該如何與青春期的孩子相處?
自我意識的萌發
青春期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1~13歲的青春期初期,主要表現為與父母頻繁發生沖突,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成年人的權利和自由;第二階段是14~16歲的青春期中期,主要表現為情緒失控,容易產生抑郁、焦慮等心理問題;第三階段是17~20歲的青春期后期,主要表現為冒險行為增多,由于缺乏自我控制能力而發生諸如暴力、濫用藥物等反社會行為。
這些“叛逆”行為首先與青少年的心理發育有關。青少年從之前依賴父母到逐漸關注自我,既包括對自我身體的關注,也包括自我意識的提升。一方面,對身體的變化感到措手不及,往往不知道向誰求助而陷入恐慌;另一方面,對自己的外表更加在意,容易受到光鮮亮麗的偶像吸引而陷入盲目。同時,自我意識得到飛躍式發展,心理活動集中指向自我,看重他人對自己的觀察和評價,相對敏感脆弱。
在自我意識的作用下,青少年與父母老師、與同伴朋友、與社會的關系都在經歷重構,沖突是典型特征,從而被理解為“叛逆”。
也有研究認為,“叛逆”與青少年額葉發育不完全有關,常常表現出來的是沖動行為增多,愿意冒險,同時青春期個體在杏仁核、海馬、紋狀體等皮質下腦區都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些腦區都與情緒的產生和調節緊密相關,會導致青少年在這一時期變得敏感、沖動。
對既有社會秩序的反抗
如果說心理發展和腦發育是青春期一系列變化的生理基礎,那么社會制度和文化習俗則是青春期行為的社會基礎,同樣應引起重視。從歷史的角度,能更清晰地看到“叛逆”的社會性。幾十年前,違背父母意愿、選擇自由戀愛就被視為“叛逆”,而今天,自由戀愛是再尋常不過的事。可以說,“叛逆”看起來是對家長和家庭的反抗,但實質上是對既有社會秩序的反抗,因此對家長的叛逆或許可以理解為對當前社會秩序反抗的一種映射。
當前青少年的生活方式愈發多元化,但從總體上看,矛盾主要表現在對代際、階層和教育制度的反抗。
中國社會推崇“長幼有序”的傳統文化,并延續至今。通常情況下,青少年應尊重服從家中長輩、學校老師,青少年文化也服從于成年人建構的主流文化,處于從屬地位、亞文化地位。然而伴隨著社會發展與變遷,青少年的社會文化地位逐漸上升,甚至達到與成年主流人群爭奪話語權的程度。
目前來看,這種代際沖突的結果主要有三種:包容、打壓與轉移。
嗶哩嗶哩(bilibili)推出的《后浪》、快手推出的《看見》,可以看作是對“包容”的一種努力,“前浪們”俯身去理解二次元文化、電競文化和土味文化,雖然這種“包容”有著“收編”的嫌疑,落腳點仍是“前浪們”所珍視的價值觀,而這正是青少年亞文化所挑戰的對象。
“打壓”則更為常見,很大原因也是由于青少年文化自身發展的不成熟,與社會規范、主流價值觀相違背,由“叛逆”上升到“越軌”,比如粉絲社群衍生的網絡暴力,但應該思考的是,“打壓”之后我們還應該做什么。
正是由于“收編”和“打壓”的存在,青少年開始“轉移”文化場域。這幾年我們觀察到的趨勢是,微信更多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社交空間,而QQ則成了青少年的社交和文化空間,微博更成了飯圈文化的領地。“轉移”并不是“消失”,而是青少年和青少年文化對抗既有社會秩序的新策略。
當今社會的青少年,除了代際壓力,也面臨著嚴峻的階層差異。古語云“書中自有顏如玉”,現代社會勵志的說法是“知識改變命運”,但到了“95后”“00后”成長的時代,階層之間、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鴻溝很難跨越,昔日作為“天之驕子”的“985”高校大學生,如今自嘲“小鎮做題家”。他們對階層秩序的對抗有時比較隱晦,可能表現為對父母的抱怨,也可能表現為學習興趣的喪失或者孤獨自閉,主要源于對現實的無力感和迷茫。
而對教育制度的反抗在青少年中則更為普遍。現行教育體制下,青少年以主課學習為主,“好學生”“差學生”主要通過學習成績來定義,學習以升學、高考為目的,學習方式大多以被動接受為主,使得師生關系以服從權威為主。青少年表現出的厭學情緒,更多是對應試教育體制的不滿。
在對代際、階層和教育制度的反抗中,也貫穿著對性別秩序的反抗。時至今日,我們仍可以聽到諸如“女孩子要溫柔、要聽話”“男孩子調皮代表聰明”“女孩子小時候學習還行,到初中就不行了”“女孩子學不好數理化”“男孩子當然要學理科”這類言論……遺憾的是,這些刻板印象不僅存在于坊間閑談,甚至還存在于一些教育工作者的理念當中。一旦青少年沒有服從這些性別秩序,比如男孩子不喜動而喜靜、女孩子偏好中性化的裝扮,就很容易被貼上“叛逆”的標簽。
新技術的進步與普及
我們常常聽到大人抱怨“現在的孩子越來越不好管”,是今天的青少年比父母小時候更不乖了嗎?這可能要歸因于新技術的進步與普及,某種程度上放大了青少年的態度和行為,青少年更容易“被看到”,即表達自我,同時更可以“做到”,即實現自我,而成年人的掌控感逐漸減弱。
據相關調查顯示,青少年往往較早地接觸網絡,而且觸網的低齡化趨勢愈加明顯,5歲及以下就已經接觸互聯網的青少年占10.88%,6~10歲開始接觸互聯網的青少年占61.43%。此外,青少年也表現出了較強的網絡綜合使用能力,90.48%的青少年認為自己能夠熟練使用互聯網,88.06%的青少年認為自己能夠對網上搜到的信息是否真實給予確認,75.17%的青少年知道如何制作短視頻。在對18歲以上青年群體的調查中,85.3%的青年非常同意或比較同意社交網絡增強了話語權,92.8%的青年非常同意或比較同意在社交網絡中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利用網絡空間的各種資源、規則與開放屬性的過程中,青少年會發展自己的實踐策略來展開數字生活中的行動,不僅面向自身的學習、娛樂與生活,也會通過技術賦能來“反哺”父母長輩。所謂數字生活中的策略性,正是青少年文化自主性的體現。
當下的青少年并非一味地按照父輩文化和主流精英文化的價值行事,他們對資源的調用、對規則的理解和運用,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和彈性,而互聯網和新技術則極大豐富了可供調用的資源,賦予青少年使用規則乃至創造規則的可能性。
在社會學對當代青年文化的理解中,這種文化自主性具有較強的反身性,這種反身性的文化實踐表現為青少年拒絕自上而下的定義,如同布迪厄描述的“自我觀察的觀察者”,他們會有意識地在數字生活中生產和再生產自己的文化資本,而且很多時候可能是獨特的青年數字文化資本——從網絡流行語到發展青少年的語言共同體,從小鎮青年到土味視頻或新土味視頻,從開直播到做網紅,青少年身份的表達與角色的實踐均表現出很強的反身性。
伴隨著文化自主性的增強,青少年文化及其表現形式更加多元豐富,包括線上的和線下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即使所謂的矛盾、反抗和叛逆,也有著與以往不同的形式和策略,如前文提到的“轉移”。事實上,這些青少年文化的新特征也并非只存在于中國社會。
呼吁“平等、開放與挫折教育”
青少年的“叛逆”可能帶來諸多風險,如網絡沉迷、校園暴力等,僅憑青少年自身力量難以應對,加之當代青少年文化多元性和復雜性的特征,使得這些風險更加難以察覺,給家長、老師和社會帶來了更大的挑戰。下面筆者就如何構建積極友好的親子關系,給出一些建議。
第一,反思自身、促進了解,隨時代發展和孩子成長及時調整教育方式。很多時候家長感受到的“叛逆”,其實是因為沒能及時調整教育方式,用孩子經常抱怨的話說就是“你還把我當小孩子!”。父母應敏銳捕捉到孩子的成長變化,加強對孩子的了解,同時面對社會文化變遷同步調整家庭生活方式,積極改善與孩子的溝通方式,促進親子之間相互理解和有效溝通。
第二,尊重孩子、平等溝通,建立親密關系的邊界。需要說明的是,家長的權威性有必要存在,即使在親子關系看似“自由松散”的西方社會,也普遍認同應維持家長和老師一定程度的權威性,尤其在青少年教育中。但在日常大多數非原則性問題的溝通中,家長應充分尊重孩子,培養孩子的自尊心,盡量做到耐心、平等溝通,給予孩子表達個人看法或保護個人隱私的空間。
第三,終身學習、保持開放,陪伴鼓勵孩子的興趣發展。家長有著學習的熱情、具備好奇心,才能帶動和鼓勵孩子的求知欲。必要時家長也應向孩子虛心請教,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提出“后喻文化”的概念,指年輕一代將知識文化傳遞給長輩,這是當代世界獨特的文化傳遞模式。保持開放、學習的心態,主動了解孩子的興趣愛好,如陪伴孩子探索和體驗最新的游戲、最新的App、最in的時尚活動。
第四,接受短板、擁抱挑戰,以身作則引導孩子積極健康的價值觀。現代教育理念強調家長角色的“祛魅”,回歸人性。可適當放棄完美父母的人設,讓孩子了解你的情緒、痛點,學會與自身的短板相處、與挫折相處,無論在學習還是社交上,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家長的不完美。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青少年與教育社會學研究室副主任)
責任編輯:李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