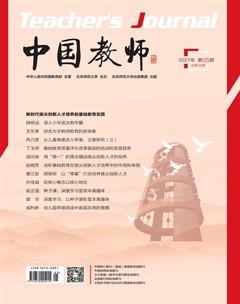所遇見的都是美好: 我與傈僳族童聲合唱團的故事
張莉莉?姜冠群


黃曉娟
女,1985年出生,傈僳族,云南省麗江市玉龍縣人。2003年畢業于麗江高等師范專科學校。2003—2009年,任黎光完小音樂教師;2009—2018年,任黎明完小音樂教師,參與、組織傈僳族童聲合唱團的排練與演出等活動;2018年,任黎明幼兒園園長。從教十八年,黃老師帶領合唱團演出十余次,深受國內外觀眾喜愛。
一、大山深處的鄉村音樂老師
我出生于麗江市玉龍納西族自治縣黎明鄉的一個小村莊。成長環境比較好,爸爸媽媽很疼愛我,特別是我爸,非常支持我。比起同齡人,我覺得我還是很幸福的。2000年9月,我在麗江高等師范專科學校讀書,學習的是幼兒教育,也就是學前教育。我喜歡唱歌跳舞,學習期間,我很認真,非常喜歡自己的專業課。
1. 因為喜歡跳舞,所以選擇了幼兒師范
初中那會兒,我們班主任跟我說,將來讓我去當老師,我還跟班主任生氣,說我這輩子打死也不當老師。我特別喜歡唱唱跳跳,特別崇拜楊麗萍,覺得她的孔雀舞跳得太好了,想著自己要當個舞蹈家。因為我就喜歡唱唱跳跳那種比較活潑開朗的活動,所以畢業時麗江師范招幼兒老師,我就去了。稀里糊涂地去報名,但是報了以后也挺喜歡的。當了老師以后,越來越喜歡這份工作。到今年我已經教了18年,我非常熱愛教師這個職業。
本來我學的是五年制大專,沒想到到了第三年,也就是2003年的時候,麗江撤縣劃市,分為古城區和玉龍縣。劃市以后,學校說我們可以提前畢業,于是我們學了三年就中專畢業了。畢業時教育局分配工作,我運氣比較好,分到了自己的家鄉—玉龍縣黎明鄉。
2. 黎光完小的學生,伴我走過最美的年華
2003年,我剛去黎光完小的時候,整個學校也就一百多名學生。學校四面都是山,只有山背后有幾戶人家,遠離人群和公路,風景很美,但是冬天特別冷。當時我們的縣委書記去黎光完小走訪后,還立了一個碑—麗江最美麗的鄉村小學。
黎明鄉是玉龍縣唯一一個傈僳族鄉,90%的人口都是傈僳族,只有少數的彝族人。我覺得我們的學生天生就有唱歌跳舞的強大基因,舉行婚宴、過年的時候,學生們會圍著篝火打跳。以前還有很多對歌的活動,非常熱鬧,孩子們耳濡目染,也會跟家長一起又唱又跳。黎明鄉的許多父母還是比較貧困的,這幾年脫貧攻堅之后,條件才改善了一些。
我的一些學生來自早婚早孕家庭,他們的媽媽可能十五六歲就開始生孩子了,沒有結婚證,到了法定年齡才去交罰款、領結婚證。有的甚至根本來不及領結婚證,就離婚了:有的是感情不和,有的是出去打工,一去不回。所以我們這邊學生家庭完整的比較少。
我剛到黎光完小的時候,教的是一年級,第一節課去上的就是音樂課。我一進教室,所有學生起立,我既激動又害怕。因為我那會兒剛畢業,才18歲,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孩子,就去教書當老師,心里還是有點忐忑。第一節課教的是歌曲《數鴨子》,就是“門前大橋下,游過一群鴨”那首歌。教他們練聲,把學校學到的那些東西教給他們,學生特別喜歡。除了教藝術,我還教語文、數學。在我們這種小學,老師基本上都是全能型的,什么都會教。
第一年“六一”兒童節的時候,我組織學生們排節目。我們排的節目是民族舞。當時學校條件不好,連演出的服裝都沒有,學生們家里也沒有錢買演出的服裝。我就到處借服裝,東一件西一件的,挨家挨戶去借服裝。最后我們去鄉里比賽,拿了第一名,我覺得特別驕傲。
對我來說,當老師是一筆財富。我剛開始教書時教的那些學生,有的學生已經成年了,有的學生大學畢業了,有的學生的孩子都已經又來上學了。我跟那些學生的關系都特別好,我們像家人、朋友一樣相處。很多學生逢年過節會來家里看我,說:“老師,遇到你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聽到學生這樣說的時刻,是我最自豪、最幸福的時刻。我在黎光完小任教六年。那六年,應該說是我最美好的青春年華,我把它都奉獻給了黎光完小。
二、帶領傈僳族童聲合唱團走出大山
1. 合唱團的前前后后
(1)合唱團的魂:傈僳族民間藝術
2009年,我調到黎明完小,剛好接觸了深圳松禾成長關愛基金會,在基金會的支持下我們建立了傈僳族童聲合唱團。從2010年開始,我和王永鋼老師開始擔任傈僳族童聲合唱團的音樂老師。王老師主要負責民族音樂,我負責樂理、舞蹈。我們兩個一起合作,教學生們唱歌、跳舞。我們在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4點到5點,利用學校課外實踐活動的時間排練。因為周五下午就放學了,所以周五不排練。
第一次帶學生外出演出是2010年。我們接到中央電視臺的邀請,去參加《天生我才》節目。我們帶了四名學生,兩個女孩兩個男孩。我們很認真地編排了一個傈僳族的節目。學生第一次登上那么大的舞臺,比較緊張,不過我們的演出很成功,得到了觀眾們的好評,所有的嘉賓、老師都給我們這個節目很高的評價。
我帶合唱團十多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出,是2019年去海南參加一個國際性的青年演唱活動。在那么多國際友人面前表演,介紹合唱團、基金會。我們表演的節目廣受好評,很多國際友人都找我們拍照。那一次,我覺得特別自豪,因為我們不僅僅是在我們這種小地方表演,而是在國際舞臺上演出,讓那么多國家的人都了解、認識了傈僳族,看到了我們的舞蹈,聽到了我們的音樂,影響力很大。
每次外出表演,觀眾都表示喜歡我們的歌。我想,這可能有歌曲本身的原因,也有學生們的原因。首先,我們的歌節奏歡快;歌詞比較簡潔明了,朗朗上口,不復雜;旋律也比較簡單,一唱就會、一學就會,簡單又好聽。歌曲中最常見的歌詞是“嘎齒哇,納薩哇”①,“嘎齒哇”的意思是開心,“納薩哇”也是開心、愉快的意思。
其次,學生們的眼神和歌聲很有靈氣,特別是歌聲,有一種清泉流過山谷的感覺,很清澈、很純凈。我們的服裝也常常是最漂亮的,讓人一眼就能記住。我們每次出去聽得最多的也是這句話:“你們傈僳族服裝好美,好漂亮。”
(2)合唱團的堅強后盾:公益基金會
松禾成長關愛基金會是一個公益組織,主要是發現、傳承、保護少數民族音樂。基金會希望在中國最邊遠的地區,而且是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快要失傳的地區,建立合唱團。基金會旗下有四十多個少數民族童聲合唱團。基金會不請那些走商業化路線的老師,也不會因為當地老師的文化水平相對較弱就不聘任。基金會還堅持不能影響學生的學習,不能影響老師的正常工作。他們有嚴格的要求,不能隨意地做商業宣傳。如果有電視臺或者企業、單位想邀請合唱團去演出,首先要經過基金會的批準,通過基金會的各方面考核,我們才會外出演出。
基金會有許多專業的老師,他們每年都會組織一些培訓,培訓合唱團的音樂老師,給我們上很多關于音樂的文化課,教我們很多專業知識、樂理知識。最開始,我們不會科學地訓練學生,容易很“原生態”地、使勁地扯著嗓子唱,學生的聲音容易啞。經過專業老師的不斷指導,我們逐漸知道了如何保護學生的嗓子,如何更科學地訓練學生。
基金會還要求我們每個月發一次自己上課的教學視頻到基金會的教師群里,專業老師看了之后會指導我們,就像我們在學校上文化課時聽課評課一樣。基金會把它當作常態化的管理。對我自己而言,這也是一個在專業方面不斷成長、不斷進步的過程。
2. 我的兩個音樂領路人
王永鋼老師是我們市級民族文化傳承人。王老師歌唱得很好,還會演奏、制作很多樂器,如蘆笙、四弦琴,等等。其實,他的樂理知識不是很豐富,比如他不認識“哆來咪發嗦”,但是他聽別人唱一遍,馬上就能彈出來,馬上就會唱。王老師吹蘆笙是跟他外公學的。他外公是村子里有名的蘆笙王,他們家世世代代都吹蘆笙,在我們當地非常有名。像王老師這種完完全全從祖輩那里學來的,才是我們傈僳族文化真正的精髓。
基金會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趙曉愛老師。她是我見過的所有女性中最美、最有氣質的,我特別喜歡她。她原來是一名大學合唱團的教授,退休以后,基金會把她聘回來在基金會擔任藝術總監。她很有活力,笑容滿面,又特別有親和力,是教我們的老師中最和藹的一個。她每個學期都會來我們學校待三天左右,考評合唱團,看學生的聲音怎么樣,老師的專業能力怎么樣。她每次來都會說:“曉娟,你要自信。”她教給我很多東西,特別是自信,對我的影響大。
3. 走遍千山萬水,還是家鄉最美
有時候在學校里組織藝術活動,也是有困難的。例如,很多學校不重視音樂課、體育課、美術課這些藝術課,覺得拿成績比會唱會跳重要,甚至有些老師也覺得會唱會跳沒什么用,有的老師使勁兒給學生們布置作業,學生們作業做不完,就不會來藝術社團唱歌跳舞。再如,剛接手合唱團的時候,我覺得我在專業上欠缺很多,以前只是在自己的學校里唱唱跳跳還可以,但如果要登上更大的舞臺,專業方面的要求肯定還是挺高的。
雖然我在學校教藝術、帶合唱團的時候遇到過一些困難,而且也接觸了“外面的世界”,但是依然覺得“走遍千山萬水,還是黎明最美”,頗有些“月是故鄉明”的感覺。我還是喜歡我們黎明鄉,在這個地方教書讓我覺得很愉快,很享受。雖然黎明鄉各方面硬件條件比不上縣里、城里大的學校,但也有許多寶貴的財富,是縣里、城里的學校,外面的世界沒有的。
合唱團讓我經歷了帶孩子的過程,即使有的時候因為自己能力不足,學到的東西不能完全消化,但我依然收獲頗豐。進入合唱團之后,我最大的收獲是增強了自信。一個人應該自信地活著,不管身處何處,都應該覺得自己是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應該成為最自信的人。
這種自信才應該是最重要的。我們的大部分學生都非常不自信。有一個學生,一年級剛進合唱團的時候,第一天,我在琴邊上彈音,讓她看著我唱我彈的那幾個音。其實她唱對了,但她的眼睛不敢看我,而且聲音非常小。音樂教室有一面大鏡子,我就讓學生看著鏡子中的自己。我說:“你先微笑,看著鏡子中的自己;然后不笑,用你平常那種很害怕的眼神,再看鏡子一遍。你覺得哪個美?”我經常會讓他們這樣看著鏡子中的自己,微笑,找自信。這個小女孩到了五年級的時候,變得自信、開朗、大方了許多,在她們班上唱歌跳舞,舉行朗誦會。她后來學習成績特別好,寫文章也寫得特別好。畢業以后,在我們縣城的一所中學里上學。“學習強國”APP上云南的訂閱號還刊登過她的文章。
三、我的新角色:幼兒園園長
1. 寄宿制幼兒老師的不易
2018年,黎明幼兒園開園,這是我們鄉新創辦的幼兒園。剛開園的時候,我特別害怕寄宿帶來的安全問題。那么多的小孩子,老師的壓力和責任都很大。不過也沒有辦法,有的孩子得走兩三個小時才到學校,不可能讓他走讀。家長有條件接送的,我就招了一個三歲的小班;家長沒法接送的,就招了兩個五歲的大班,五歲來幼兒園,讀一年學前班,然后就去上小學。
最早辦園的時候,有六十幾個孩子住校,現在少了一些,四十多個。每個星期天下午5點,家長送孩子來幼兒園,星期五再來接。整個星期小孩子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全部在幼兒園里。我們共有5名老師,1名保育員。老師們根本就沒有上下班的概念,和孩子們一樣,24小時在幼兒園里,管理所有孩子的起居。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11點多了,有一個孩子發燒,高燒39度多。我們聯系家長,可他家住在一個山上沒信號的地方,聯系不上。我們就到處打電話找他家的鄰居、有信號的同學。好不容易聯系上,他媽媽說他家到幼兒園得走兩小時。小孩子發燒成這樣,怎么辦?我們沒辦法,一邊讓家人趕緊下山來幼兒園,一邊又帶著孩子去買藥,不敢亂給孩子用藥,只好先給他貼退燒貼。
2. 管理工作中的挑戰與欣慰
現在國家特別重視學前教育。在我們這樣的鄉村,其實最應該辦幼兒園。許多家長對學前教育的認識是空白的,他們覺得不需要讀幼兒園,幼兒園啥也不教,孩子就是在里面吃、玩。其實創辦幼兒園的意義就在于,教孩子學會生活的能力,培養行為習慣。有的孩子來到幼兒園,不會用馬桶,不會沖水,沒有刷牙、洗腳、穿襪子的習慣,這些都要老師從頭教。培養孩子們的衛生習慣、行為習慣、生活習慣,太需要在幼兒園學習了。幼兒園開學后的前兩個月,老師們都非常累,聲音都是啞的。有時候我們晚上睡覺都睡不好,半夜要經常起來,看孩子有沒有睡著。
作為園長,有很多事情必須去處理,必須去面對,跟別人打交道、處理問題的能力,都需要有進步。我不僅要考慮自己教什么,我的學生學什么,還得考慮整個幼兒園,如老師的思想動態、老師的專業能力、學生安全問題等各方面。責任越大,身上擔負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在這個過程中我需要不斷學習,不斷努力,有一種找到自己想做、喜歡做的事情的感覺。
訪談后記
張莉莉老師去深圳調研,遇到了帶領傈僳族童聲合唱團演出的黃曉娟老師。十分驚喜的是,兩位老師之前還有一段“緣分”。張老師曾主持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與北師大合作開展的農村女童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培訓,向一線教師傳授女童性健康教育知識與技能;黃老師曾前往北師大參與此次培訓活動,將學到的知識帶給黎明鄉的學生們,開展女童健康教育活動。緣起于北京,聚于深圳。這一次,張老師在深圳看到了學生們在大舞臺上的表演,學生們的眼神清澈,聲音純粹、美好,令人動容。張老師和我以線上的方式采訪了黃老師。從黃老師的訪談中,我重新認識了傈僳族,看到了很有生氣的少數民族地區和熱愛鄉土的老師。我們看到黃老師帶領合唱團走出大山,走向大城市,甚至走向國際音樂交流舞臺,感受到她溫暖而又堅定的力量。在排練節目、表演的過程中,學生們的自信心有所提升,女孩們更是獲得了一種寶貴的力量。同時,合唱團的發展壯大,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傈僳族語言“失語”現象的發生,傈僳族語言、藝術得到了很好的傳承。黃老師作為園長,對責任的擔當、能力的提升有著自己的理解,女性領導力在她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
責任編輯: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