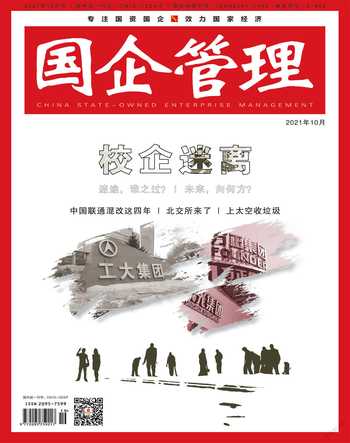數字經濟襲來,如何迎接?
歐陽日輝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教授
“十四五”,數字經濟浪潮奔涌,中國應如何迎接機遇與挑戰?
早在1994年,我國接入第一條國際互聯網,數字經濟就被提出。如果要把發展階段進行劃分,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網絡經濟。網絡經濟始于20世紀90年代,其中最重要的業態就是電子商務。
第二個階段是信息經濟。2015年,我國提出了“互聯網+”的國家戰略,其內涵是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區塊鏈(Block Chain)、云計算(Cloud)、大數據(Big Data)等“ABCD”技術如何與數字經濟相結合。
第三個階段是智能經濟。這是我國正在邁向的一個高級階段,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程度、廣度會越來越深。智能經濟中一個很重要的變量,就是應用的技術。比如,人工智能技術還處于探索階段。在未來,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等新技術應用的廣度、深度逐漸加強,智能經濟將成為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
數字經濟主要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
數字產業化,指一些ICT(信息通信技術)產業,如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量子科技等新技術,其自身就可以形成一個獨立的新興產業。數字產業化,其實就是數字技術產業化的過程。
產業數字化,是指數字技術怎樣運用到三大產業,即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之中,推動其數字化轉型,提質增效。比如,對于東北地區來說,農業作為一項重要產業,插秧是很重要的環節。以前只能通過人力實現,后改為機械插秧,但這一過程中也需要培育秧苗。有了無人機技術后,可以“點播”種子,對農業產量、生產效率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目前,我國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在全球范圍內處于第一梯隊,但與美國相比,還有比較大的差距。長遠來看,要注重數字技術的原創性,在一些“無人區”加大自主創新力度。
我國的主要優勢在于應用方面。基于廣闊的市場,應用的場景比較多,但原創技術還存在不足。我國正在推動打造不同的應用場景,尤其在服務業領域中打造的場景最為豐富。
下一步,應更多關注工業、農業領域,特別是工業領域中的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把5G技術和工業互聯網相結合,推動智能制造的發展,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
未來,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會呈現出八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我國處于爭奪全球經濟發展主導權的機遇期。在過去,全球經濟發展的主導權是以工業經濟為代表,工業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生產制造。在未來,全球經濟發展主導權主要表現在產業鏈、供應鏈的創新方面。我們正面臨這樣一個機遇期,要想把握主導權,就必須要采取創新驅動的方式。
第二,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處在交織發展的時期。未來,隨著技術人員的不斷出現和技術在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領域的應用,各種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會同步發展,同時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機遇期。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上指出,區塊鏈的集成應用在新的技術革新和產業變革中起著重要作用,要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重要突破口,著力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要構建區塊鏈產業生態,加快區塊鏈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前沿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推動集成創新和融合應用。
這說明,這些技術是很重要的發展方向,如果它們形成新的產業,就能在全球起到主導和引領的作用。
第三,我國的數字經濟處在與原有的監管體制、政策、法律法規的對撞期。新出現的業態和原來的監管體制一直在摩擦中前行。未來,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越來越多,會挑戰現有的政策、法律法規、監管手段,并且隨著這些技術的應用頻率、應用廣度和深度越來越高,摩擦和碰撞會越來越多。
舉個例子,在金融領域中,用原來人工的方式去監管數字信貸等新的互聯網業態,就會永遠跟不上數字經濟發展的步伐,需要使用新的、相應的科技手段來監管。
第四,數據要素價值的創造會成為一個新的藍海。最近一年多,數據的所有權、數據的使用、數據要素市場的建設等,成為數據領域很熱門的話題。
既然把數據作為核心生產要素,那數據要素的價值要怎么創造,數據要素創造的價值怎么來評估、定價,誰來建設、管理數據市場,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認真考慮。數據本身是一個大的產業,既然會成為市場的新藍海,也會對我國的監管體系提出巨大的挑戰。
第五,我國的數字平臺將“走平拓廣”,走向更廣闊的領域和更深的維度。早在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工作會議上就講到,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制造業、農業、服務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要堅定不移支持網信企業做大做強,加強規范引導,促進其健康有序發展。
在更深度的發展過程中,需要站在更高的視角來看待數字經濟。數字平臺是數字經濟最核心的一種發展載體,因此,要推動數字平臺的國際化發展。在這一方面,中國和美國存在很大的區別。從互聯網平臺的角度來講,美國的互聯網平臺一產生就是全球性的平臺,而中國真正走向國際的互聯網平臺屈指可數。
第六,我國的智能經濟、智能產業等各種新的業態將會煥發蓬勃生機,主要體現在第二產業。我國要想走制造強國之路,一定要讓智能產業、智能制造、智能經濟領域成為重點發展方向。
第七,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將進入深水區。我國發展的數字經濟是勞動友好型經濟,傳統企業的發展關系到人們的就業問題。比較可行的路徑是,推動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今年初,國務院國資委發布了《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系統明確了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方向、重點和舉措。
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可能會持續5-10年。未來,傳統企業完成數字化轉型后,整個社會的企業會分為數字企業和非數字企業。數字企業就相當于汽車、火車、飛機等交通工具,非數字企業就相當于馬車,會繼續存在,但在整個企業形態里面占的份額會很小。
第八,在線服務、內容消費的創新速度會越來越快。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大大推動了各種服務和產品的在線化。在服務領域,消費不僅包括有形產品,還包括無形的內容、服務的消費,比如內容電商、電子商務,正朝著內容和場景相結合的方向發展。
如何迎接奔襲而來的數字經濟浪潮?
第一,面對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要立足國內數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立足實體經濟的發展,做好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深度融合。
第二,互聯網本身具有全球化的特征,不能只是“室內開花”。要依托“一帶一路”發展數字經濟,特別是東盟地區。對中國來說,東盟的語言、文化、習俗等各方面有一定的先進性。把東盟作為發展數字經濟“走出去”的一個重要區域,有一定的可行性。
在此基礎上,中國的新發展模式、新業態要產生“溢出效應”,幫助其他國家朝著數字化的方向發展,把數字經濟的“走出去”作為建設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我國處于爭奪全球經濟發展主導權的機遇期。在過去,全球經濟發展的主導權是以工業經濟為代表,工業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生產制造。在未來,全球經濟發展主導權主要表現在產業鏈、供應鏈的創新方面。我們正面臨這樣一個機遇期,要想把握主導權,就必須要采取創新驅動的方式。
第二,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處在交織發展的時期。未來,隨著技術人員的不斷出現和技術在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領域的應用,各種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會同步發展,同時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機遇期。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上指出,區塊鏈的集成應用在新的技術革新和產業變革中起著重要作用,要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重要突破口,著力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要構建區塊鏈產業生態,加快區塊鏈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前沿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推動集成創新和融合應用。
這說明,這些技術是很重要的發展方向,如果它們形成新的產業,就能在全球起到主導和引領的作用。
第三,我國的數字經濟處在與原有的監管體制、政策、法律法規的對撞期。新出現的業態和原來的監管體制一直在摩擦中前行。未來,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越來越多,會挑戰現有的政策、法律法規、監管手段,并且隨著這些技術的應用頻率、應用廣度和深度越來越高,摩擦和碰撞會越來越多。
舉個例子,在金融領域中,用原來人工的方式去監管數字信貸等新的互聯網業態,就會永遠跟不上數字經濟發展的步伐,需要使用新的、相應的科技手段來監管。
第四,數據要素價值的創造會成為一個新的藍海。最近一年多,數據的所有權、數據的使用、數據要素市場的建設等,成為數據領域很熱門的話題。
既然把數據作為核心生產要素,那數據要素的價值要怎么創造,數據要素創造的價值怎么來評估、定價,誰來建設、管理數據市場,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認真考慮。數據本身是一個大的產業,既然會成為市場的新藍海,也會對我國的監管體系提出巨大的挑戰。
第五,我國的數字平臺將“走平拓廣”,走向更廣闊的領域和更深的維度。早在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工作會議上就講到,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制造業、農業、服務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要堅定不移支持網信企業做大做強,加強規范引導,促進其健康有序發展。
在更深度的發展過程中,需要站在更高的視角來看待數字經濟。數字平臺是數字經濟最核心的一種發展載體,因此,要推動數字平臺的國際化發展。在這一方面,中國和美國存在很大的區別。從互聯網平臺的角度來講,美國的互聯網平臺一產生就是全球性的平臺,而中國真正走向國際的互聯網平臺屈指可數。
第六,我國的智能經濟、智能產業等各種新的業態將會煥發蓬勃生機,主要體現在第二產業。我國要想走制造強國之路,一定要讓智能產業、智能制造、智能經濟領域成為重點發展方向。
第七,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將進入深水區。我國發展的數字經濟是勞動友好型經濟,傳統企業的發展關系到人們的就業問題。比較可行的路徑是,推動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今年初,國務院國資委發布了《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系統明確了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方向、重點和舉措。
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可能會持續5-10年。未來,傳統企業完成數字化轉型后,整個社會的企業會分為數字企業和非數字企業。數字企業就相當于汽車、火車、飛機等交通工具,非數字企業就相當于馬車,會繼續存在,但在整個企業形態里面占的份額會很小。
第八,在線服務、內容消費的創新速度會越來越快。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大大推動了各種服務和產品的在線化。在服務領域,消費不僅包括有形產品,還包括無形的內容、服務的消費,比如內容電商、電子商務,正朝著內容和場景相結合的方向發展。
如何迎接奔襲而來的數字經濟浪潮?
第一,面對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要立足國內數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立足實體經濟的發展,做好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深度融合。
第二,互聯網本身具有全球化的特征,不能只是“室內開花”。
要依托“一帶一路”發展數字經濟,特別是東盟地區。對中國來說,東盟的語言、文化、習俗等各方面有一定的先進性。把東盟作為發展數字經濟“走出去”的一個重要區域,有一定的可行性。在此基礎上,中國的新發展模式、新業態要產生“溢出效應”,幫助其他國家朝著數字化的方向發展,把數字經濟的“走出去”作為建設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編輯/國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