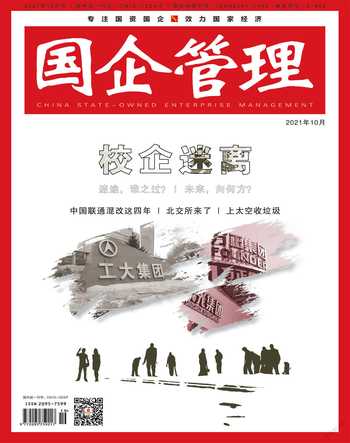迷途,誰之過?



迷途,誰之過?高校,在明明德,在傳道授業解惑;企業,以獲利為贏,不以純粹逐利為中心。“高校+企業”,曾經被當作彌補教育經費不足、促進學研產一體化的高招妙棋,如今何以成了導致大量國資流失、滋生腐敗的雷區?
漩渦中的校辦企業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紫光集團被“債權人”申請的“破產重整”并不等于“破產清算”,破產重整具有一定的維持價值和再生希望。
那么問題來了,紫光集團的巨額負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2009年,北京健坤集團以49%的股權入股紫光集團,趙偉國出任總裁和董事長。自此,紫光開始走上以集成電路為主業的高速發展之路。
不過,與很多芯片企業自主研發的路徑不同,趙偉國選擇了更快的方法,那就是“買買買”。
2013年底,紫光先以18億美元收購展訊通信,后以9.1億美元收購銳迪科。這兩家位列國內前三的芯片設計公司都是清華校友創辦,分別專注通信基帶芯片和射頻芯片,且已在納斯達克上市。紫光收購之后,二者合并成紫光展銳,成為全球前五的芯片設計公司。
接著,紫光又于2015年,以25億美元收購國內最大的網絡設備公司新華三51%股份,進軍網絡設備和服務器領域,布局“從芯到云”戰略。
紫光擴張的野心遠不止于此。2015年7月,紫光意圖以230億美元收購鎂光,但被美國政府禁止。10月,紫光出資38億美元收購西部數據15%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然后由西部數據出面,繞過美國政府的管制,擬以190億美元收購閃迪。此舉最終也因美國政府干預無疾而終。
接下來,紫光試圖出資53億美元收購SK海力士20%的股份,但最終也沒有結果。
海外受挫沒有讓紫光停下腳步。最近幾年,紫光的投資方向主要在國內,包括與西部數據共同成立合資企業紫光西數、組建長江存儲、開建武漢存儲基地、收購存儲芯片公司武漢新芯、控股上海宏茂微電子等。
其中,在武漢的存儲項目總投資240億美元,在成都的存儲項目總投資達240億美元,在南京的集成電路基地項目總投資預期高達300億美元,在廣州芯片制造基地的計劃投資也高達1000億元人民幣。
“紫光的主要問題就是過度投融資帶來的債務困境”,業內人士介紹,從2013年至今的8年間,紫光集團發起并購近60起,投入資金超千億元,成為諸多“造芯”企業中,布局最早且涵蓋產業鏈上的設計、生產、測試等環節的企業。大規模頻繁并購投資,使得集團累計負債規模過大,融資結構失衡。
7月9日,紫光集團發布公告,稱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送達的《通知書》:相關債權人以集團不能清償到期債務,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且明顯缺乏清償能力,具備重整價值和重整可行性為由,向法院申請對集團進行破產重整。
同一天,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網披露:徽商銀行向法院申請對紫光集團破產重整,辦理法院正是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當晚,紫光集團回復媒體稱,被債權人申請重整未對集團下屬公司日常生產經營造成直接影響。目前,公司各項生產經營活動均正常開展。
作為國內大名鼎鼎的校企明星,紫光集團成立于1993年,前身是清華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公司于2004年改制重組,控股股東為清華控股有限公司。經過多年發展,紫光集團形成了以芯片和云網兩大業務為主,能源、金融、教育等業務為輔的多元化業務格局。
紫光集團下設多家核心子公司,包括A股上市公司紫光股份、紫光國微,均為行業巨頭。以從事芯片設計業務的紫光國微為例,截至2020年7月9日,市值高達1034億元,是A股市場貨真價實的“千億選手”。
實際上,紫光集團的資金鏈危機在2020年11月已經顯露。當時,“17紫光集團PPN005”公司債券未能與投資人達成展期協議,成為紫光首只違約的債券。
從這時開始,紫光集團密集發布公告,宣告幾只債券的兌付可能存在問題。隨后,公司發行的8只債券,有6只債券先后違約,包括16紫光01、16紫光02、17紫光03、18紫光04、19紫光01、19紫光02。
截至2021年4月26日,紫光集團負有清償義務的已到期債務累計金額為人民幣70.18億元。12月底,還將有一只13億元規模的債券到期。此外,三家紫光集團全資子公司,包括紫光通信、紫光國際控股、紫光芯盛負有清償義務的已到期債務累計超過26億美元。
根據紫光債券年度報告,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和2020年6月末,公司合并報表資產負債率分別為62.09%、73.42%、73.46%和68.41%,超過了一般企業40-60%的資產負債率。其中,負債合計2029億元,流動負債1192億元。
7月20日,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網更新了紫光集團招募戰略投資者的公告。公告顯示,戰略投資者需整體承接紫光集團或者紫光集團核心產業。
8月28日,紫光股份、學大教育、紫光國微等集團旗下公司公告,北京一中院已裁定對紫光集團等7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并指定紫光集團管理人擔任七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管理人。
與紫光命運相似,但更早暴雷的是北大方正。2020年2月18日,其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宣布申請破產重組。
壓垮方正的,是一筆20億元的短期借款。這筆款項在2019年12月1日到期,但方正未能按期完成本息兌付。作為債主,北京銀行認為方正已經不具備這筆債權的清償能力,將其告上法院。
區區20億元的債務,怎么就把方正壓垮了?要知道,在此之前,方正是一家擁有3600億元資產,年營業額高達1333億元,凈利潤16億元的大型企業。
實際上,20億元只是最后的那根稻草,破產重組之前,方正已經是千瘡百孔。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2月,方正集團本部的負債高達700億元,包括300億元的債券,400多億元的銀行貸款。而整個北大方正的總負債,更是高達3030億元,資產負債率達到83%。
在這些龐大的債務中,有大約1600億元是有息負債。同時,方正的利潤也在不斷下滑。2016年至2018年,凈利潤從32億元下滑至15億元,到2019年前三季度,方正的歸母凈虧損更是達到31.9億元。
相對于債務的龐大,更讓人感到驚訝的是方正的債務增速。數據顯示,在2017年,方正的負債還只有1888億元,但僅僅2年不到,就飆升到了3029億元。
這家背靠北京大學的校企,它的錢從哪里來?最終又去了哪里?這些,都是方正留給外界的謎題。
方正是個含著金湯匙長大的“種子選手”。
20世紀70年代,中國印刷業依然用的是排鉛字的方法,不僅費時費力,還污染環境。當時,先進的激光印刷技術,都被西方世界所壟斷。
打破這種局面的人叫王選,畢業于北大數學力學系。他在實驗室里研制出了世界領先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給中國沿用150年的鉛字印刷畫上了句號。
1986年,商業嗅覺靈敏的王選開始將自己的研發成果推向市場。他與母校合作,正式創立北大方正。
憑借著世界領先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短短3年,北大方正的訂貨金額就突破了1億元。到1989年底,其漢字激光照排系統,已經占據了國內報業99%、書刊出版業90%以及海外華文報業80%的市場。
1995年登陸資本市場后,方正開始做起了電腦,還一度成了與聯想齊名的國產電腦品牌。乘著這股迅猛的勢頭,方正開始四處擴張。到2018年,方正集團的年收入達到1333億元,位居“中國企業500強”第138位、“中國電子信息百強企業”第5位。最巔峰的時候,方正集團旗下有400多家公司,其中6家是上市公司,擁有35000多名員工,總資產高達3600多億元。
與此同時,在光鮮的外殼下,這艘巨輪底部已經暗礁遍布。和其它所有迅速膨脹的企業一樣,方正發展的秘訣就是“加杠桿并購”。
2001年,善于利用資金杠桿撬動各種資源的李友入局北大方正后,組建了一支善于進行資本運作的管理層。2002年,時任方正集團董事長的魏新宣布實施“多元化戰略”,開始瘋狂買買買,先后收購浙江證券、民族證券,參股成都商業銀行、全資收購蘇鋼集團、入主西南合成藥廠等等,在資本和產業市場上橫沖直撞。
這種思路和操作完全改變了北大創立方正的初衷——科研成果轉化。方正從一個高科技公司變成了一個全新的金融控股財團。
2009年,方正電腦年銷量達500萬臺,位居全球TOP10,即便如此,方正集團還是毅然決然地砍掉PC業務,繼續擴張。
除了擴張,方正還有一個死結。1999年,那時候的方正內部分成了兩派:以董事局主席王選為首的技術派,以董事長張玉峰為代表的經營派。
最后,北大要求王選和張玉峰同時退出集團董事會。這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但方正內部的爭斗并沒有因此結束。
王選之后,北大副校長閔維方任集團董事長。僅僅過了2年,同樣來自北大的魏新接任集團董事長。在此后的數年,方正內部的大亂斗輪番上演。
期間,以李友為首的資本集團“凱地系”,還上演了一出“內幕交易,侵吞國有資產”的鬧劇,他們僅以4480萬元,拿下了方正集團30%的股權。這部分股權的真實價值至少12億元。
兩家頂尖學府庇蔭下的明星校企相繼出現問題,讓人們開始懷疑,難道學校真的不適合做企業?
象牙塔的“勤工儉學”
我國的校企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萌芽于20世紀50年代,80年代開始大規模起步。
當時,國家出于公共財政不足和科研成果亟待轉化的考慮,允許高校和院所自籌經費,創辦企業。20年的時間里,各大高校、院所競相辦起了企業。
中小學校辦企業是打著“勤工儉學”的旗號起家的。1958年,為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提出開展“勤工儉學”活動,先后在中小學開展過生產節約運動、勤工儉學和“學工、學農”活動。但這類活動側重于勞動教育,不甚關注經濟收入。
1977年以后,隨著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兩條腿走路”理念的嬗變,于是打著“勤工儉學”旗號的校辦企業迅速發展。
這里有兩個典型的例子:
一是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它起步于杭州市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公司靠著3個人、借來的14萬元起家,一句“喝了哇哈哈,吃飯就是香”的廣告詞將其迅速送上中國制造業企業500強。
另一個是昆山好孩子集團。1988年,昆山陸家中學副校長宋鄭還接手校辦工廠。1989年,憑著從銀行貸款來的5萬元資金,成立了“好孩子”,依靠童車站穩了腳跟,一步步走向全國第一。
1977-2000年,校辦企業收益中用于補充教育經費、改善辦學條件的總金額約為2.2億元。這在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實施教育現代化工程中,是一筆不可或缺的補充。
不過,這類企業早已轉制,脫離了校辦企業的范疇。而絕大多數中小學校辦產業,也都在進入新世紀前,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今天通常意義上的校辦企業,主要指高校所辦的校企。作為“智囊”的集中地,創造力勃發的地方,高校往往可以貢獻出很多新鮮的科技成果,“校辦企業”的形式可以更好地銜接產業化,補齊“產學研”鏈條。改革開放初期,是高校校企集中出現的時期。
1993年1月,“上海復旦復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陸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為中國第一家上市的校企。
到了20世紀末,根據統計數據,全國3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592所普通高校,共創辦了4563個校企。其中科技型企業2355個,占全部上報企業的51.61%;其他類型企業2208個,占上報企業的48.39%。
從經營性質來看,從事工業生產的企業為1893個,占41.49%;從事商貿的企業425個,占9.31%;從事其它經營方式的企業2245個,占49.20%。
從投資性質來看,學校獨資企業高達3044個,占66.71%;國內聯營企業1478個,占32.39%;外資合營企業41個,占0.90%。
從對企業隸屬管理關系上看,由學校管理的企業為4031個,占88.34%;由校內院、系、所管理的企業532個,占11.66%。
1983年2月,根據國務院有關規定,校辦企業免交所得稅。1989年,小學校辦企業除免交所得稅外,還免交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校辦企業所得利潤、返還的減免稅,原則上40%用于教育事業、60%留在企業。當時,許多鄉鎮的校辦企業實際上是掛牌企業,國家免稅部分大都進入了企業籠子,成為承包者的收益。
2003年,高校校辦企業的總收入為826.67億元,利潤總額42.98億元,凈利潤27.95億元,上交稅金38.69億元,對其出資方的回報更是高達18億元;在證券市場上,它們控股或借殼上市公司近40家,占整個股市市值的2%,成為A股中不可小覷的高科技方陣。證券市場上能與“北大”“清華”“浙大”牽上關系的企業一度“呼風喚雨,風光無限”。
以華中科技大學為例,其以全額2.041億元投資了子公司——武漢華中科技大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又投資了華工科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后者是中國資本市場上一家以激光為主業的高科技上市公司,截至2019年9月23日,總市值達到206.83億元。這還僅僅是直接投資的公司,高校企業子公司再投資的公司,并沒有列入此次統計范圍,其實際資產可能更多。
關于42所一流大學校辦企業的數據顯示,投資企業數量最多的學校是天津大學,達到了48家。此外,北京大學、吉林大學、南開大學、北京理工大學投資企業數量也都超過了20家。擁有學校獨資企業最多的是吉林大學,達到了28家。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分別以約47億元、35.7億元和11億元,占據了投資總額前三甲的位置。清華大學投資的企業數量并不多,只有11所,但是其投資總量卻是最大的。
總體上看,高校投資的企業領域涉及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制造業、批發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建筑業、教育、農林牧漁業等,甚至還有房地產、住宿餐飲等行業。
所有高校投資行業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的企業數量最多,所占比重也最大。這個結果與設立校辦企業的初衷一致。
此外,制造業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也是這些高校投資較多的領域。這種現象則是因為在納入統計的21所高校中,很多都擁有強大的制造業或計算機學科背景。
以投資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最多的浙江大學為例,根據《關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的通知》文件,浙大計算機相關的一流學科數量達到了3個。而且在2018年中國最好學科榜上,浙江大學的幾個計算機相關學科排名也非常靠前。
投資制造業企業最多的天津大學,其制造業相關專業也遙遙領先。
同樣,投資建筑業最多的幾所大學,依次為重慶大學、同濟大學、東南大學,它們均為建筑“老八校”。這再次印證了優勢學科對高校投資偏好的影響。
發展初期,校辦企業的作用是學生的實驗、實習場所。發展過程中,校辦企業漸漸成為推動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和產業化、直接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提高國家高新技術產業水平、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陣地。其中,有一批高校科技企業成為海內外知名的企業,在社會享有較高的聲譽。國資流失的重災區2017年6月16日,中紀委網站公布了十八屆中央第十二輪巡視中14所中管高校的巡視反饋意見,校辦企業成為問題“重災區”——14所高校中13家被點名。
從2017年2月開始的這輪巡視,最受輿論關注的當屬中央巡視組進駐29所中管高校。
其實,早在2014年,校企的問題就曾出現在巡視問題清單中。當年,中央巡視組指出復旦大學管理校企中“一手辦學、一手經商”現象突出。
同樣在2014年,教育部發布的《關于深入推進高等學校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的意見》指出,要加強高等學校國有資產管理,理順資產管理關系,嚴防借改革之機侵吞國有資產、牟取私利。這份文件還強調,禁止院(系)、教師違規利用學校資源興辦企業,杜絕“一手辦學、一手經商”現象。
除了校企直接的問題,“清單”中提到的科研經費、基建工程、物資采購等領域也有問題。而這些問題,往往與校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除了此前提到的紫光、方正,哈工大破產也曾一度成為焦點。
公開資料顯示,哈工大集團曾擁有工大高新、航天科技兩家上市公司,并參股哈高科,市值最高時達1100億元,所控資產也曾一度超過北大系校企,成為國內最大的校企集團。2017年的信用評級報告顯示,哈工大系校企中,哈工大集團的總資產為170億元,評級為AA+;工大高新的總資產為71億元,評級為AA級。而被捕的哈工大集團原董事長、前副校長張大成稱,集團在2015年時遭銀行集中抽貸36億元,最終因5億元票據融資及資金困境等原因發生危機,導致200多億元國有資產流失。
內斗的問題也同樣出現在哈工大集團。張大成稱,2015年,時任校領導提出對集團進行私有化,遭其拒絕。此后各銀行紛紛集中抽貸,使集團遭遇流動性危機。后來,哈工大集團和綠地北方公司的3次規模僅5億元的“票據融資”使其落入債務陷阱。其后,集團還陷入了“蘭州刑案危機”。
2015年4月,中國紀檢監察報曾刊載題為《管住權力,別讓“象牙塔”蒙塵染污》的文章。文章稱,相關研究證實,基建項目、物資采購、招生錄取、財務管理、科研經費、校辦企業、學術誠信等七個方面,是高校腐敗問題相對集中的區域。這些區域,都是高校的關鍵崗位和重要領域,附著于此的權力相對較大,權力所帶來的“收益”也相應較大,進一步“刺激”了心懷貪欲的相關負責人。
這類事件并非個例。監管空缺的校企一隅逐漸成為高校腐敗重災區,因此在中央對高校的多次巡視中,校辦企業問題都是反饋意見里的“常客”。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文件明確提出高校要逐步實現與下屬企業的剝離,并且為高校企業改革設置了明確的實施步驟。文件指出,原則上在2022年底前,要基本完成高校與所屬企業的改革任務。
從2018年“紫光系”打響第一槍后,“高校概念股”接二連三易主,一場高校企業改革浪潮正不可避免地席卷全國。
2018年10月起,清華大學旗下三大資本平臺紛紛啟動改革,先將紫光國微、紫光股份和紫光學大三家上市公司控制權轉讓給深圳國資委旗下的深投控;再于2019年3月與雄安新區合作,使清華控股和雄安集團、雄安新區管委會控股的基金并列成為啟迪桑德和啟迪古漢大股東;最后于2019年4月將同方股份控制權轉讓給中核資本。
2019年4月,石大勝華發布公告稱,控股股東青島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擬減持石大勝華不超過4033.13萬股,占總股本的19.9%,而后者為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全資控股企業。石大勝華在公告中也表示,上述減持實施可能導致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及實控人變更。
7月17日,山大華特的實際控制人山東大學與山東國投簽署《股權轉讓協議》,山東大學擬將其全資公司山東山大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及所屬企業的股權轉讓給山東國投。一旦轉讓完成,“山大系”47家企業或將集體易主山東國投。
根據《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規定,校辦企業體制改革開始后,原則上高校不再新辦企業,這意味著大批出現的校辦企業很可能成為歷史。
雙線作戰下的苦楚
大學是知識高地,它們的優勢是知識、科研和人才。比較理想的狀態下,高校應該成為知識溢出、研發溢出、人才溢出的科技產業化源頭。來自高校的創新“種子”,在外部市場中的合適環境和資源的支持下,開始發芽、長大,最終成長為一個個公司。在良性模式下,高校、創業資本、市場化環境、職業經理人等要素的集聚,再加上政策的支持,應該成為一種建立在知識創新基礎上的補全“產學研”鏈條的生態。
然而,在發展過程中,一部分校企摒棄了科技創新的初衷,走上了資本化的道路,很多演化為資本運作的投融資平臺,甚至有些校企利用國資監管的空白,成為少數控制者搞資產交易和政策尋租的平臺。
以紫光集團旗下的北京紫光科技服務集團有限公司(下稱“紫光科服”)為例,在股權上,北京冠華展業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北京亞燃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紫光集團有限公司各持股49%、36%、15%,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均為時任董事長趙偉國昔日商業伙伴李祿媛。
值得注意的是,大股東冠華展業科技的實際控制人同樣是李祿媛,最終受益股份高達99%。進而,李祿媛也成為了紫光科服的實際控制人,持股達49.6%。
從變更記錄來看,紫光科服從最初由紫光集團控制下的北京紫光投資有限公司持股100%,逐漸演變到如今由李祿媛個人持股最多。
此外,紫光科服的股權質押也頗為引人關注。其6次股權出質中,5次質權人是錦州銀行不同支行,不難看出錦州銀行成為其妥妥的“金主”。
除了資產交易,更多的校企投身當時的“金飯碗”房地產。
紫光集團也是地產的擁躉者。其于2016年陸續在北京、南京、武漢、成都、蘇州、廈門等一二線城市,開發紫光科技園區項目。截至2018年,它進駐8個高科技產業集聚城市,管理項目數量達10個,管理資產規模達600億元。嚴格意義上來說,紫光科服更像是一個被冠以“紫光”名稱的地產公司。
而紫光集團最近一次拿地是在2019年12月2日,當時,紫光集團、紫光股份、紫光國微及紫光科服以聯合體身份耗資66.09億元摘得北京市海淀區學院路地塊。如今,伴隨著紫光集團的光環逐漸“消退”,關于紫光科服的故事才越來越少。
而在地產業務布局上,北大方正旗下地產業務平臺——北大資源在地產圈的名氣,顯然高于紫光科服。
北大資源在1992年創立于北京。2013年前,它以數碼產品的分銷和服務為主營業務;2013年,方正數碼正式更名為北大資源,同時推進業務多元化的發展戰略,逐步進入房地產開發和商業地產運營領域。
如今,北大資源資產規模超過1000億,深耕城市20余個,開發面積達2000萬平米。但由于近兩年,大股東北大方正陷入債務重組泥潭,北大資源也“不能獨善其身”。
據其2020年年報顯示,北大資源總營收規模90.85億元,上年為241.32億元,同比下降62.35%;兩年凈利潤均為虧損狀態,分別是-24.22億元和-20.25億元。
或許是因配合重整所致,北大資源年內主動削減物業開發項目面積約2/3,導致收入下調。其資金使用也嚴重受限,從而造成了因延遲償還銀行及其他借款的索償罰款增加。
2020年,北大資源總負債388.99億元,超過總資產,負債率創歷史新高至101.85%。
對于校企的管理者而言,也飽受“雙線作戰”的苦楚。大多出身于教師的校企經營管理人員,不愿意放棄身份,而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又必須要全身心投入,造成他們“腳踩兩只船”在兩種身份、雙線作戰。這也成為校企一路走來,飽受垢病、問題不斷的一大原因。
校企絕對是一種特殊企業——它們具有企業的身份,但又缺乏市場化的體制、機制和約束;它們頂著高校的光環,便利地獲取資本市場高估值,但又缺少國企的黨內監督和國資監管;校企背后的大學,雖然作為大股東掌控著資產,但又缺乏企業管理經驗和金融資產運作能力。
這一系列問題,是導致校企弊案頻發,成為“怪胎”的主要原因。
客觀來看,在強調創新創業的背景下,有關部門并未限制來自高校的創業企業發展壯大,但令人遺憾的是,企業不僅沒辦好,還不斷從高校吸取資源、敗壞其聲譽。
雖然,國家層面自2018年開始推動校企改革,部分校企被劃轉給各地國資監管部門,以促進高校聚焦教學科研主業。但是,從企業發展和高校角色來看,校企改革不能一刀切,建立高校科研成果的轉化機制和科創企業的培育體系才是校企改革的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