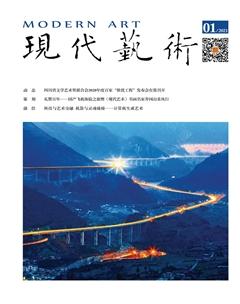馮建吳山水畫語言審美特性研究
馮建吳在一生的藝術探索與創造中,根植于傳統與生活,在此基礎上進行熔鑄、升華,形成了具有書寫性、寫生性、時代性的獨特藝術語言特征與形態,對西南及巴蜀地域的藝術創造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與促進,對當代中國畫藝術創作的探索與創作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價值。
近現代以來,中國畫在藝術形態、語言風格、時代審美等各方面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和轉換,時代的進步推動著中國畫的創新與發展,誕生出了諸多成就卓著的藝術大師。作為20世紀西南及巴蜀地域著名的中國畫大家,馮建吳在詩詞、書畫、篆刻、藝術教育等領域成就斐然,影響卓遠。其中國畫特別是山水畫在繪畫風格、形式語言、藝術意境等方面形成了雄渾勁健、煥爛大氣、凝重樸拙的獨特面貌和體系。他在藝術語言上堅持金石味與書寫性的融匯;在藝術風格上強調“詩書畫印”的繼承與自我創新,在寫生過程中強調“能人、能出、能化”的凝練與方式;在藝術觀念上推崇石魯“生活為我出新意,我為生活傳精神”的時代內涵與藝術自覺。馮建吳在一生的藝術探索與創造中,根植于傳統與生活,在此基礎上進行熔鑄、升華,形成了具有書寫性、寫生性、時代性的獨特藝術語言特征與形態,對西南及巴蜀地域的藝術創造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與促進,對當代中國畫藝術創作的探索與創作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價值,現試論之。
一、書寫性
中國傳統繪畫,自宋元以來文人畫興起,就逐漸形成了詩書畫印一體與兼融的藝術形式與風格,尤其強調“書畫同源”“以書入畫”“畫從書出”的審美特質。書法與國畫都以線性語言為主,具有共同的造型基礎與審美內涵。中國畫的形態結構與造型語言,立足于書法用筆,強調豐富多變的筆形與筆性變化,從而使中國畫更具有視覺與審美上的深度與厚度。南齊謝赫“六法論”中的“骨法用筆”,即是從筆性角度闡釋了中國畫線性造型與書寫性的內涵與關聯。在漫長的繪畫實踐與創造過程中,中國畫注重運用書法的點線造型原則,對書法用筆的枯濕濃淡、轉折、頓挫、藏露、快慢、疾澀等技法進行轉化與吸收,在線性造型的基礎上融匯與表達出書寫性的審美意味。元代趙孟頫 的詩句“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以及山水畫大師黃賓虹所言:“吾嘗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畫”“我畫樹枝,常以小篆之法為之”等都進一步闡明了書畫之間的用筆書寫性的內在關聯與內涵。中國畫最終表現的是繪畫的意境,書寫性則是意境表達最獨特的方式與語言。縱觀歷代大家,無不在探索與表現繪畫語言的書寫性中各領風騷、各顯神通,創造出了獨特的藝術風格與審美內涵。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馮建吳遠赴成都、上海學習,遍訪名師益友,在傳統詩詞、書畫、篆刻等領域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和功底。在成都美專、上海昌明藝術專科學校學習期間,馮建吳受教于王個簃、潘天壽、諸聞韻、任堇叔、馮君木等諸位大家。馮建吳的書法篆刻與繪畫,其用筆書寫性意味濃厚,這與其早期研習傳統金石書法及海派吳昌碩藝術風格緊密相關,“馮建吳后期的書法創作以其樸拙雄渾的金石筆力為世人所稱道,這和他早年投師于金石派大師吳昌碩門下是分不開的。”“另一方面,還主要得益于其一生之中對古今各派的廣取博收,兼容并蓄與融匯貫通。在幾十年研習書法篆刻的過程中,他曾研究過多種流派,掌握了多種書體,既專攻,又博學,一直在不斷探索著自我創造的路徑。他對真、草、篆、隸各體,都下過扎扎實實的功夫。”在多年的探索與創造中,馮建吳形成了他獨特的破體書法,縱橫恣肆,勁健雄厚,極富金石厚度與雄強氣韻,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其繪畫的筆意與內涵。
六十年代期間,馮建吳注重以金石筆意入畫,用筆老辣、樸拙,線條勾勒與皴法的金石味更加厚重凝練,使畫面呈現出雄健蒼勁的書法意趣、濃厚的金石趣味與繪畫風格,創造出傳統底蘊深厚而又不失時代精神的藝術風韻。當代著名畫家唐永明談到,馮建吳強調用筆是傳統繪畫功力的核心元素,“認為文學和書法是中國畫最重要的基礎,并以此嚴格要求學生。”他的“畫面筆墨十分講究,用筆以書寫性,以筆墨的表現性為主干”。其作品中筆墨語言與造型轉折頓挫有力,方硬奇崛,無論勾勒皴擦點染,均以沉雄厚勁的筆法出之,特別是其后期作品諸如《天塹變通途》《綠水青山代代春》《一代青松》《蜀江水碧蜀山青》《月涌大江流》《巫峽清秋》等諸多力作均以瘦硬老辣,雄渾勁健的金石筆法營造出了繪畫作品的宏大氣象與藝術意境,表現出了剛強、磅礴的繪畫藝術風格。通過對傳統藝術的繼承與融匯,馮建吳把中國畫強調書畫一體及其書寫性的特色推進到了一個新的境界與高度,創造出了新的時代的藝術風格和風氣。
二、寫生性
唐·張躁云:“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生活與自然是藝術創作的源泉,是藝術語言生成與探索的母體。歷代藝術創作者諸如荊浩、范寬、黃公望、王履、石濤等無不遵循古訓,以自然為師,并躬身實踐,“搜盡奇峰打草稿”。與古人一樣,“馮建吳畢生重視深入自然和寫生。早在三十年代,他和段虛谷創辦東方美專時即請黃賓虹入川執教,并與黃賓虹在青城等地游覽,寫生。”新中國成立后50至60年代初期,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大環境下,用藝術反映現實、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成為藝術家們的責任與時代要求,藝術家們深入生活、表現生活,通過寫生展現這個時代新的面貌。眾多山水畫家例如李可染、陸儼少、傅抱石、錢松巖、關山月、石魯等人都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到生活與自然當中,用他們的筆墨語言對火熱的現實生活進行了深入的表現和創作。如1954年李可染與張仃、羅銘歷時三個月進行寫生活動;1955年至1956年,趙望云、石魯出訪印度的寫生活動;1960年秋,傅抱石組織的為期三個月的長途旅行寫生活動“江蘇國畫工作團”等對當時的中國畫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和促進作用。在社會主義建設熱潮的促動下,馮建吳逐漸從傳統的審美與意趣中脫離出來,在困厄的生活環境中積極投入生活,以寫生表現生活,逐漸探索出了新的寫生藝術語言風格與形式。在此期間馮建吳經歷了重要的寫生過程,如1959年,同石魯以及方濟眾,何海霞等人于延安楊家嶺等地進行寫生;1962年,歷川、鄂、桂、滇、黔等省,展開了為期兩個多月的長途寫生,創作出了《南通煤礦一角》《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欸乃一聲山水綠》《峽江夕照圖》等三百多幅寫生稿;1972年,響應號召赴襄渝鐵路工地體驗生活,創作《四海為家》《天塹變通途》《一代青松》等畫作;1976年至1977年,帶領學生去奉節、樂山、峨眉等地寫生等。
馮建吳的寫生作品,通過表現生活、反映社會現實,一改過去傳統的語言面貌,逐漸形成了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與風格,這一時期也成為他藝術道路的轉折階段一一如果說其早期寫生之作《蔬菜豐收》《蜀江帆影》《峨眉華嚴頂》《瓜瓞綿綿》《西瓜地》《寶塔晨暉》《南桐山區》等作品生活味濃厚的話,其后期《天塹變通途》《綠水青山代代春》《蜀江水碧蜀山青》《四海為家》等寫生之作則具有了獨特的繪畫意味和全新的面貌,為其晚期創造出的勁健厚拙,雄強大氣的畫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代表作品《黃山猴子觀海》《青城天下幽》《峨眉云海》《夔門天下險》《月涌大江流》等則是在長期寫生,體悟生活與自然基礎之上,創作凝練出的具有極強的藝術風格與語言特性的代表作品。
需要指出的是,在堅持寫生、表現生活的過程中,石魯的思想與觀念對馮建吳產生了重要影響。馮建吳極力推崇石魯重視寫生以及“生活為我出新意,我為生活傳精神”的藝術主張,遵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原則,在生活與自然中飽游飫看,通過大量的寫生,打破樊籠,獨辟蹊徑,依據對現實與自然的深刻觀察和體驗,自出新意,創作出了超越常規審美趣味的新形式。
三、時代性
何謂時代性?時代性是指在社會各個領域中,在某一時代與時期呈現出來的主流思想與價值傾向。反映時代精神,體現時代審美,是文藝創作者的創作目標,也是時代發展的內涵和要求。石濤云:筆墨當隨時代。作為藝術創作者,在繼承與學習傳統的基礎上,對所處時代進行深入的思考、表現與探索,創作出具有時代特色的藝術作品,是一個藝術創作者的責任也是創作的價值所在。“具有時代精神的作者根據他對社會意識、生活形態的理解,將這些藝術形態進行解讀,繼而作出相應的藝術處理,再用自己獨到的表現形式將其重新描繪、組合,最終創作出來的才是最有時代特征而又有獨特審美意味的作品。”
新中國成立后,時代的變更與發展帶來了繪畫領域全新的視覺表現和審美內涵,中國畫無論從藝術形態還是藝術精神的指向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著名國畫家石魯在這個時期提出了“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生活為我出新意,我為生活傳精神”的創作主張,其思想對當時的美術界以及馮建吳本身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大批藝術創造者都以新的時代筆墨、新的表現內容、新的藝術精神來歌頌和反映新中國現實生活的重要成就和發展狀況。
與此同時,經歷了社會主義的思想改造與影響,馮建吳也逐漸從傳統的審美趣味中轉換與脫離出來,逐漸探索屬于自己的繪畫語言與藝術思想。“在這個時期,遠在上海的業師王個移先生也時時寫信來鼓勵他突破過去因承前人遺序而略帶拘謹的創作風格,探求出自己新的創作面貌,他逐漸開始自覺地進行著藝術創新的探索活動。”與此同時,在50年代中后期與60年代初期,與石魯及長安畫派畫家的多次交往與寫生,逐漸使馮建吳形成了獨立的藝術思想,其畫風畫意逐漸走向深入與成熟。
在50年代至70年代左右,馮建吳創作了大量表現人民現實生活場景、反映時代新貌的畫作。創作出了《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欸乃一聲山水綠》《曬魚網》《桂林桃花江》《峽江夕照圖》《天塹變通途》《一代青松》等具有代表性的畫作。馮建吳在寫生與創作實踐過程中,積極對表現現實生活與時代精神的筆墨語言進行探索。他在“繪畫藝術上的變法創新,一方面得益于當時的時代新潮,另一方面得益于江山之助,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他認為:“藝術要反映生活,就得描寫新生活、新景物,以搞具有主題的創作為主,要與時代同步,而不能違背時代。”在自我主張、全面而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淀以及對現實生活的觀察中,馮建吳努力尋求藝術創新的道路,對繪畫反映時代風貌與精神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創造。
文革結束至80年代,是馮建吳創作的黃金時期,經過多年的寫生積淀以及對時代審美的感悟與探索,馮建吳形成了鮮明的圖式風格與雄健大氣、樸厚濃郁的山水畫風。其代表作品諸如《黃山仙桃石》《峨嶺朝暉》《猴子觀海》《橫絕峨眉巔》《峨嶺云海》《峨嶺春云》《高山平湖》等都鮮明地凸顯出了筆墨的厚重與書寫性、色彩語言的濃烈與圖式形態的時代性,繪畫語言與風格更加鮮明凝練,具有突出的視覺沖擊力和強烈的時代美學特征。在筆與墨的凝重與書寫中、在色與墨的對比與輝映中、在形式結構的交錯與布局中,其作品意境更顯渾厚而大氣、樸拙而悠遠,營造出了在同時代中強烈而獨特的畫風與格調。從馮建吳雄渾樸厚,大氣勁健的藝術語言中,深刻體現出了他立足傳統,“外師造化”“與時俱進”的藝術品格,對傳統精髓和時代審美的獨特創造和把握,從而最終創造出了他無愧于時代與藝術的繪畫價值與典范,對巴蜀畫壇的藝術面貌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祝正鋒
ZHU ZHENGFENG
1977年生。四川省宜賓學院美術與藝術設計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畫創作與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