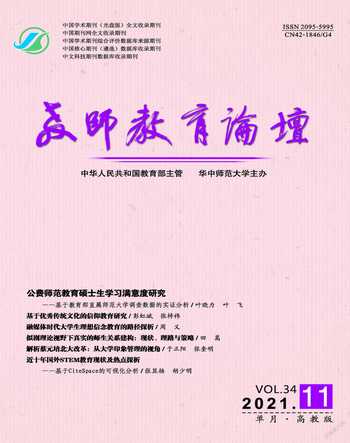擬劇理論視野下真實的師生關系構建:現狀、理路與策略
田嵩
摘要:建立真實的師生關系是實現平等溝通,優化教學效果的關鍵。從教育場域的博弈關系來看,師生關系存在話語權、教育資源、價值裁量權三重博弈。師生關系的戲劇化呈現與不真實性,其成因在于前臺與后臺的巨大差異。擬劇理論背景下師生真實關系構建的策略在于,首先,運用教師形象的多維傳播以促進教師的身份構建與認同;其次,傳播環境里實現教師專業性話語與日常性話語的均衡與滲透;第三,教育環節中多元主體參與下的價值協商與理念共謀以促進共識的達成;第四,傳播路徑上運用新媒體賦能知識生成與傳播,推動師生間關系的平等。
關鍵詞:擬劇理論;教育傳播;媒介賦能
中圖分類號:G45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5995(2021)11-0031-04
前蘇聯教育家贊可夫在20世紀70年代說過:“就教育工作的效果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看教師和學生的關系如何”。但由于學校教育舞臺功能的彌漫,教師常年處于一種對現有世界的“歪曲”與“異化”狀態之中,這種狀態迫使教師個體本真的異化,以方便在教育過程中按照外在預設做出各種虛假的表演。[1]反觀當下師生間關系現狀,其“藏匿性”“尊卑感”“淡漠化”的趨勢嚴重,更有學者指出,學生在課堂中的“話語低迷”現象可視為與教師話語權與面子的協商過程,以互動時的“沉默”保全與構建“面子”,這正是“消極面子”。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戈夫曼的“擬劇理論”對真實性關系的構建也頗有啟迪,戈夫曼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視為一種“表演過程”,并且通過互動的過程塑造“理想自我”,他明確指出幕后的真實現狀與前臺行為呈現存在差異,呈現真實的代價越大,其“表演”的程度越深。基于對師生間關系的真實性考證,同時對不真實關系的成因探討,本文將擬劇理論作為貫穿全文的基礎,通過分析師生間關系的前后臺差異,探索師生真實關系構建應具備的條件。
從語境的角度上看,中國屬于高語境,相比于美國等低語境文化環境,其顯著特點是語言表達含蓄,輔助的身勢語言所藏匿的信息數量與內涵豐富,因此在人際交往中所蘊含的“內隱性”需要動用更多的感官以接近真實。基于師生在課堂中的博弈不難看出,師生間的關系并非理想狀態下的“平等”與“通暢”,而正是出于對師生關系走向“趨利”與“虛假”的隱憂,梳理師生間關系的現狀、成因,探索解決的對策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現狀:教學場域的博弈關系透視
無論是教還是學的過程,教師擁有對教育資源調度、課堂教學節奏、教育政策與知識的解讀等先賦優勢,教師在教學環節的主控性不言而喻,但這不能成為學生在教學環境中“失語”與“被動”的引導與解釋。為確保教與學環節的辯證與統一,教與學應成為動態互為轉化的關系,學生在課堂教學環節中應成為知識創新的重要來源。師生圍繞教育場域中的資本開展博弈,在博弈過程中的前提、環境與評價上,學生均處于弱勢地位。
(一)話語權博弈
圍繞知識傳授過程中的知識傳播力與專業闡釋力。縱觀教學過程,專業話語權構建中的師生博弈主要圍繞知識的闡釋力,課堂教學環節控制,日常生活規制而展開,在此過程中,教與學時常處于流動的狀態,并非靜止。顯而易見的是,教師作為課堂教學環節的“引導者”,呈現出知識闡釋與課堂節奏把控的先賦優勢,而這一優勢也將逐步蔓延至生活日常話語的傳播中來,無論是從話語的類別、數量還是影響力來看,學生在此博弈中處于劣勢地位,而這將進一步消解學生的話語自信,轉而向“被動”乃至“失語”的狀態轉化。
(二)教育資源博弈
圍繞物化教學空間為規訓場域,實現教育資源配置權與使用權。“立法者”角色這一隱喻是對現代型知識分子話語權利的最佳描述,因為“立法者角色由對權威性話語的構建活動構成,這種權威性話語對爭執不下的意見糾紛做出仲裁與抉擇,并最終決定哪些意見是正確的和應該被遵守的”。[2]場域的生成與流動與生存在其中的個體密切相關,場域以資本爭奪為目標,布迪厄將資本分為文化、社會、經濟,象征幾個類別。由此可見,教師在教育資源的使用上具有優先性,即在教學環節過程中,教師通過教學資源的展示與利用,實現課程教學目標,而學生在此過程中通過教師的授權或協同參與教學過程,因此從資源的歸屬上來看,教師具有優先教育資源使用與調度權。
(三)價值裁量權的博弈
教師對學生階段性發展評價與評測結果審定的優勢。值的博弈可推至教學專業領域與日常生活領域,1859年,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斯賓塞(H. Spencer)提出了一個著名命題:“什么知識最有價值?”從而引發對于知識價值的大討論。教師之于課堂中的專業性分工使得教師長期擁有對于自身所從事專業的權威,并通過課堂延展至生活性話語,為教師在話語傳播中賦能。話語的交流與博弈展示著特定價值。教師與學生群體間的話語流動則傳達著家庭教育的價值與學校教育價值、倫理價值間的互動與博弈。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學生通過內心的調試與選擇,最終形成自身的價值取向。然而,通過教育天然賦權的教師成為學生發展現狀的評價主體,通過分數等途徑掌握了學生成長的價值裁量權,使得教師在裁定學生掌握技能的程度上擁有了先天的優勢。二、理路:師生關系的戲劇化呈現與非真實性成因探究教育信息化對教師身份權威產生巨大沖擊,也實現了教育資源與環境的重新整合。從教師專業精神與權威的喪失,傳統教學與教學儀式的固化,價值裁量的絕對控制到課堂中教學過程師生角色的區隔乃至對立等,都將導致教師與學生之間關系真實性“疏離”。
(一)前臺與后臺的差異,呈現師生內在緊張關系
戈夫曼的擬劇理論區別了前臺表演與幕后行為,試探表演者是否愿意為獲得認可而重塑“完美形象”,也展示出前臺的表演與后臺的真實呈現之間的代價,偏離“構建真實”所付出的代價越大,則前臺表演與真實性相距越遠;反之,越容易將后臺與前臺的行為趨于一致,以免除內心的焦灼與對立。學生害怕被孤立而選擇態度調試、脅迫性合群與李普曼筆下的“公眾”擁有一致性。同時,由于在學生面前的角色與心理優勢,在傳統的教育環境中,教師作為表演者非必要去迎合作為觀眾的學生的喜好,在一定時期內,教師前臺表演與后臺趨于一致,有效彌合了前臺與后臺的差異。隨著履行“社會監督”功能的新媒介介入后,教師成為更大舞臺的表演者,觀眾擴大為移動互聯網中的受眾,其積累的身份與心理優勢被逐步消解,更難以契合紛繁復雜的人心當中教師的完美形象,這又迫使教師對于預設的“前臺形象”產生焦慮與調試,而造成教師、學生與家長之間難以均衡的矛盾與聯系。
(二)價值判讀“錯位”與價值定位疏離加劇師生關系沖突
首先,知識價值的多重判讀。教師的教以知識為核心的輻射,其價值圍繞學生對于知識的認知、理解,記憶與運用等目標得以實現。對于“什么樣的知識最有價值”的討論從未休止,而圍繞課堂知識價值的討論也面臨現實需求、社會轉型、時代信仰等多重維度考驗。“靜止”于課堂中的知識體系常被視為落后的、保守的甚至缺乏發展動力的“固態文本”,當學生認知或技能等水平超越或低于課堂教學設定目標時,困于難以打破師生間長期以來積累的教學關系,學生便會選擇適應狀態下的“虛假”協同,讓“因材施教”化為空談。其次,基于不同發展階段對于教育價值認知的差異。學生因發展能力、水平的漸進性與階段性,對于教育價值的認知也處在動態之中,因缺乏教育過程的整體性認知,而對教育評價產生抵觸。對已然擁有知識技能的教師群體來說,“非理性客觀看待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或擁有的技能,稟賦效應”尤為明顯,這將造成教師與學生之間對于教育價值的認知錯位,對知識的超越性認可與貶斥性低估形成鮮明對比,造成教與學角色的沖突。第三,對于教師身份價值的差異。因學生成長階段的不同教育目標,雖然在學生頭腦中構建出教師耐心耕耘的園丁形象,但每一位園丁在漫長的人生歲月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都受到局限,產生因短暫性的陪伴而呈現出功利性培養的價值感偏差,而之于教師群體,其內生性的使命感與自我認同是教師群體得以延續的重要動力。因此,淡漠化與偽善化的師生關系真實存在于校園之中。
(三)教師的絕對“掌控”與學生的被動“約束”間固化角色不平等
關于知識的價值,因個體與社會發展需求間的博弈與調試難以形成統一標準。因價值的二元分化,呈現出知識學習過程中的利他與利己主義的兩大傾向。隨著學校教育專業化與精細化的運作,以及在實現知識創新、人才培養,社會服務職能上的精進,學校在定義知識價值上呈現出獨有優勢。知識本質上的非功利性并不隨著社會變遷與個體價值導向而產生變化。知識表象的變遷與異化。從“功用”的價值本位到滲透本質穩固的“認知”。移動互聯情境下知識創新路徑得到前所未有的優化,傳統的自上而下的知識創新與傳播系統的地位被稀釋甚至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社會微觀層面個體的“井噴”式文化傳承與創新,以及經典知識現代化的遷移。雖然碎片化的信息挖掘被視為淺表的、非系統性的知識體系構建,但仍不可避免的對促生個體新認知的產生埋下伏筆。
社會賦予教師以“育人”的職能,賦予教師成為教育內容的“闡釋者”與“灌輸者”,教師自身便擁有對教育話語控制權,而在教育過程中,學生是知識的“吸收者”,同時因為認知的階段性而呈現出話語輸出困境。在知識的傳播與反饋等環節,教師成為難以撼動的“知識權威”,課堂節奏“掌控者”。被動接受傳統意義中對于課時的理解意味著教師應自身保有對教學全過程的“掌控力”,繼以實現教學目標,任何擾亂教師正常教學秩序的行為將被視為“阻礙”,學生的“規訓”與“配合”的呈現是教育過程的前提條件。三、策略:擬劇理論背景下師生真實關系的構建新媒體技術的持續創新與生活的深度融合,為生活理念與價值的重塑提供了可能性。大量余暇時間被釋放,伴隨著碎片化信息的傳播,為個體認知突圍創設了條件,將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封閉的、等級森嚴的知識體系,使得個體被賦予不同領域、不同認知縱深的知識闡釋力,使得個體能動力得到充分釋放,話語權的多向度分割進一步促進了平等對話的可能性。隨著新媒介技術滲透教學環節,師生間的關系已由原有“教”與“學”的單向度轉化至交互式學習體驗,學生的“學”既是教師的教學內容,更超越了既定的教育目標。這也意味著教師的“教”不僅僅局限于書本中的課程內容,教師的身份由對教材內容的適應轉為批判與創新融合,移動互聯情境下的教育環境的形成,為師生間的真實性與平等性關系的形成創設了條件。
(一)教師形象的多維傳播:刻板印象下的批判與審視到身份的構建與認同
教師的身份認同存在多元性、構建性與適切性等特征,以往固化的“權威”形象在課堂管控、知識傳播過程中具有優勢,因而展示出明顯的“強制”與“服從”,“主控”與“接納”、“灌輸”與“失語”等二元對立的局面。教師形象的主體構建區別于“被構建”的狀態,從而釋放了教師的自主意識與創新活力,其多元形象的展示與輸出,能夠幫助教師從至高無上的“神壇”中走出,充刻畫出“有血有肉”的自然人狀態,打破“圣賢”標準禁錮下的“魔咒”,從而讓學生接受發展中亦同步成長的教師群體。教師形象的主體構建將延伸至與媒介協同、共生的情境,雖然社交媒體的“微小敘事”成為教師展示自我形象的重要樣態,仍舊不能忽視主流媒體“宏大敘事”與“深度報道”帶來人物形象的縱深感。不同類別媒體的協同機制將從全局上構建教師形象的主體脈絡,報道策略的深入整合與新聞價值挖掘為立體的教師形象構建提供創新動力。
(二)符號的解構與重構:專業性話語與日常性話語的均衡與滲透
因知識神秘性和階層性,能夠開展知識教學的教師本身即存在社會地位的優勢,其開展教學過程中也有絕對的話語解釋權,不可也不容置疑。殷商周王室的祝、巫、史、宗等在“絕地天通”之后,壟斷了這些儀式、象征的執行權力和解釋權力。[3]知識傳播過程賦予教師獨特的話語權力,從而演進為課堂的話語控制力,但也應避免專業話語滲透下對于學生日常話語的剝奪而導致的“失語”窘境。理清學科專業話語與日常性生活話語的地位與角色,探求不同類別話語語境下的可轉換性。日常生活性話語將為課程內容建設與創新提供源動力,豐富學科專業性話語的深度與適切性;課程內專業性話語將為日常性生活話語提供科學指征與系統整合力,專業話語會為日常性話語的瑣碎提供系統理論參考,也將碎片化的話語整合成為系統化的思考輸出。專業性話語與日常生活話語的滲透與融合,打破專業性話語與日常性話語的絕對區隔,警惕教師專業性話語權逐步吞噬日常性話語權的分配與均衡。
(三)共識的達成:多元主體參與下的價值協商與理念共謀
學校是傳播教育價值的重要場所,也是教師個體價值彰顯的重要途徑,作為個體社會化的重要場合,教師的價值、態度與行為將對學生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力,同時也解構或重塑著學生的人格。教師價值取向外在顯示為課堂教學行為,教師群體自身價值維度的構建均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從微觀上看,教師的教育行為施加于學生之時,產生的是深層次的價值碰撞,譬如來自于學生家庭價值體系與教師自身價值體系的抵觸或交融,這種抵觸或交融,同時還面臨社會價值導向與教育政治的價值系統等不同價值主體間的作用與張力。學生通過不斷學習、模仿與調試來構建自身價值體系,在學校教育環節中,教師的價值觀占據著主導地位,而隨著學生逐步成長,家庭的或是社會的價值體系將發揮更為實質的作用。聯動的價值主體面臨不同階段的價值取舍與地位調試,應突破原有格局上家庭、社會與學校教育的割裂甚至是對立局面,讓主體間在發展理路中得到均衡與調試,碰撞與交融,在學生的不同成長階段緊密協作,謀求共通價值,實現理念共謀。
(四)傳播路徑優化:新媒體賦能知識生成與傳播,推動師生間關系的平等
移動互聯網背景下,現有知識生成路徑區別于傳統知識生成的系統路徑,跨學科間知識的沖突與融合展示出知識生成過程的靈活性與多樣性,學科的邊界逐步擴寬,而推動學科自身朝縱深式發展,亦與個體發展日益緊密。基于知識生成的多時空迸發、多維度感知趨勢造就了人與社會的密集協作與互動反饋,而進一步推動新知識的生成。學校已不是唯一的知識生成場所,學校已有的陳舊知識體系也不斷遭遇來自于社會實踐創新知識體系的考驗,面臨來自于社會浪潮中的倒逼式“改革”呼聲,象征著固有知識的權威消散。從知識傳播路徑上來看,課堂是傳統知識傳播的重要方式,現因教育信息化的整體推進而值得商榷。特別是隨著移動互聯技術的更迭,特別是人工智能、大數據、移動客戶端等技術運用于教育實踐環節,使得知識傳播突破課堂的時空限制,為優質教育資源的傳播與共享,縮減“信息富裕”與“信息貧困”區域的認知差異提供現實依托。這給傳統單向知識傳輸的課堂教學帶來了機遇與挑戰,即作為以學科知識體系為核心的有效擴充,以及基于信息環境的繁雜趨勢下知識傳播體系的“經典”與“潮流”、“枯燥”與“趣味”、“保守”與“激進”、“傳統”與“創新”的價值對抗。第三,知識創新的根基進一步穩固。知識具有信息的特質,并由特定符號構成。理論與實踐作為知識創新的重要路徑,在媒介信息技術革新與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實現了學科間邊界的逐步消融,基于新現象本質探究的理論回溯與創新。知識創新主體的擴散。使得知識創新與形成不僅是握有話語權威的“精英”,運用自媒體的影響力和普及度,普通受眾也能對“熱點事件”的聚焦和探討,從而實現普通民眾“倒逼”“精英階層”推進上層設計的變革,知識創新技術亟待行業實現多重融合等問題的破解,共同打造學習共同體。“互聯網發展催化了新的知識環境,獲取信息的解決方案日漸多元化,如何完成科學共同體的線上遷移,建立快速、有效的即時連接,打破專業化的知識封鎖,發揮企業、科研機構、社團、個人的協同效應,打通線上線下的溝通交流,尋求科學難題、技術研發的新突破,適應顛覆式創新的剛性需求成為刻不容緩的重要問題。”[4]
參考文獻:
[1]黎平輝.學校教育功能演變與教師角色中的人性開掘[J].教學與管理,2014(15):64-65.
[2][英]齊格蒙·鮑曼,洪濤 譯.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后現代性與知識分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8.
[3]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281.
[4]呂尚彬,黃榮.中國傳播技術創新研究——以技術進化機制為視角探究2017年—2018年創新特點[J].當代傳播,2018(6):24-30.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amaturgical theory: current situation, logic and strategy
Tian Song
(Normal College of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Abstract:Establishing a real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s the key to realize equal communication and optimize teaching eff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ame relationship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has three games of discourse power,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value discretion. The dramatic presentation and unreality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re caused by the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oreground and the background. The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ng the authe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rama theory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multi-dimensional communication of teacher image is us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eacher’s identity. Secondly, 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o achieve the balance and penetr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iscourse and daily discourse. Thirdly, value negotiation and idea collusion under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educational link can promote consensus. Fourthly,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empowered by new media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transmission path to promote the eq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Keywords:dramaturgical theory;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media empowerment;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