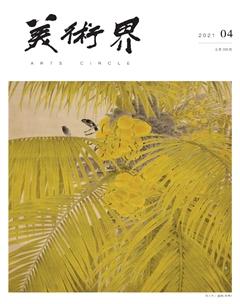發掘生活 超越自我
趙靜

張陽的油畫,多數都是勞動人民的形象,沒有夸張聒噪,反而淺淡安靜,卻自有一種走心的意味。在這個年輕的80后畫家的作品里,沒有兒女的情愁,只有平凡的千秋家國夢;沒有棱角和風情,只有深沉和命運,以及對生活和世界的愛。
一、以愛作筆描繪身邊獨特的美
遼北樸實深厚的土地,給了張陽幸福的童年和青年,也造就了他勤勞、樸實、單純的性格。童年的他充滿著夢想,遼北高遠的藍天,柔和的山川,勤勞辛苦的父母,給予了他繪畫藝術上的啟迪。他愛故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由此而迷戀上了美術。憑著他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勤奮刻苦的努力,終于拿起了畫筆,憑借著優異的成績成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如今,在他心中,沒有什么比油畫藝術更重要了,這是他最大的樂趣和追求。他的畫以獨特的藝術語言,表現了東北勞動人民不同尋常的美,以此為主題創作的一系列油畫作品,使80后新銳畫家張陽獲得了藝術界的關注和好評。
張陽的作品,最令人嘖嘖贊嘆的就是他的礦工系列和東北農村女性系列。在他的畫中,勞作中的農村婦女,臉上布滿皺紋和煤灰的礦工,色彩豐富又穩重,充滿著令觀者動容和感動的力量。
三五個農村婦女,收割和整理豐收的白菜,開拖拉機的農民笑著看她們,悠遠的藍天下,微風吹起她們頭上的紅圍巾,手上抱著翠綠的秋白菜,遠處的鄉村房屋上,已經飄起了炊煙……這是張陽的油畫作品《豐收十月》。他采用了一種微觀的、色彩豐富的畫面,以“贊美”的方式,刻畫出細節逼真、色彩鮮明的農村婦女和秋收景象。平視的角度,近距離的觀察,沒有波瀾壯闊的精神,只有平凡瑣碎而又溢著點點幸福的現實。
張陽說:“選擇這樣的題材,其實是源于對自己父母深深的愛。”在張陽的印象中,母親長年勞作,辛苦照顧自己和兩個姐姐,而作為礦工的父親,更是具備著勞動人民特有的樸素,他們勤于勞作而毫無怨言,為更好的生活、為子女的幸福而奮斗著。每次采風時,張陽看到這樣與自己父親和母親相似的勞動人民的形象,內心都有一種感動和親近的力量,想要用畫筆把他們的生活再現出來。
張陽說:“我的畫主題基本都是東北的農民,尤其以東北的女性為主。在我收集素材的過程中,發現東北的婦女和南方婦女是有區別的,她們普遍身材不高,但很健壯,很有力量感。”他最開始畫的是集市上的婦女形象,并為自己的畫作取名《啟踵可待》系列,主角是賣菜的婦女、賣蔥或賣雞的老太太。在其中一幅畫上,賣雞的東北婦女站在雞籠邊,希望把雞賣掉后回家,表現出她的對富裕生活的期待眼神,充滿著打動人心的力量。

2011年,張陽的《啟踵可待》入選“時代丹青”遼寧優秀作品晉京展,在中國美術館展出。2012年對張陽來說,是一個豐收之年,他的水彩畫作品《一路風塵》入選第二屆上海朱家角國際水彩雙年展,水粉畫作品《礦工老王》在全國水粉畫展中獲獎。隨著創作的深入,張陽屢屢拿下大獎。
張陽說:“我關注著東北這片熱土上的勞動人民的生存狀態,是因為我熱愛我生長的這塊土地,而父母的形象也是我的創作源泉。我畫這些婦女形象時,很多感覺都是與母親很相似的,應該說是我對母親刻骨銘心的愛。”
二、時代敘事每一幅畫都在講述一個故事
張陽的畫面上沒有故作深沉和故弄玄虛的顏色,只有明亮的、歡快的、一氣呵成的、大刀闊斧的,紅色的小雞、翠綠的白菜、燦爛的笑臉、遙遠的天際,一切隨意而自然,自由而舒展。
在張陽看來,靈感的火花是撞出來的,撞,是情與情的撞擊;撞,是雙方的,同軌的,自己的感情軌道越多,相撞的火花就會越多。這種火花來之不易,要十分細心、十分敏感才能抓住。對自己看到的、聽到的,要有心,會積累,會聯想,會串聯,會拆裝,要不斷加深對生活認識的深度和廣度,才有可能抓住身邊那些有價值的素材。人常說:工夫在畫外,畫外工夫就是修養。修,是讀、是看、是聽。養,是思考和領悟,是自身的修正和營造。修養是自己的感情、個性、美學、哲學、文學的綜合體,是理論和實踐的融和體,修養應該是有生命的,是不斷運動的。這樣才能在心靈上鋪架無數條情感和藝術的生命軌道,才能在生活中不斷撞擊出藝術的火花。
張陽有一幅油畫作品,取名《礦工老王》,畫面上是全黑背景,一個礦工的頭像,他的手中拿著一支煙,煙柱飄散。礦工臉上的皺紋布滿煤灰,眼神中有迷茫,也有期盼,表現了一個在井下勞作十幾個小時后期待回家的礦工形象。這幅畫一經投稿便獲得了藝術界的認可和贊嘆。“好的肖像畫也是很成功的作品,我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停留在對表面的刻畫或是形式上的翻新,那樣顯得深度不夠”,張陽說。為了能夠表現得更為深入,他常常用很長的時間去采風和寫生。“短時間的采風,只能是走馬觀花,大體感受一下,像油浮在水面上,不能深層次地滲透和交融。畫家和生活,應該是水和水的關系,滴進去幾滴,很快滲化,渾為一體。融,是非常重要的,融是心靈的溝通,融是真誠和善良的交融、滲化。愛得不深,不能融,不被愛也不能融,有了融,才能深入地了解,才可能產生樸實、真切、深刻的美術作品”,張陽表述。

張陽告訴記者,他的現實主義油畫所刻畫的形象,都是身邊具有典型性格的東北農民,他們有自己的性格和情感。“我在這樣一群善良而又勤勞的人身上,看到了可貴的閃光點,他們臉上的迷茫,他們眼中的希望,他們生活中點滴而又瑣碎的幸福,都是我想關注和刻畫的。”對張陽來說,畫自己愛的,畫自己熟悉的,才有可能深刻。熟悉了,愛了,才有可能在不起眼的地方,形成生活和時代的閃光點。愛是相互的,愛別人和被愛都是一種幸福。跟農村接觸越多,愛得越深;愛得深,才能深刻,才會常常有新的發現、新的創作沖動。把時代的閃光點變成自己的繪畫語言,以它獨特的時代面貌,深刻的思想內涵,繪制出不可重復、獨創的作品,是張陽努力的目標。
三、追求超越用情感與生命投入創作
從2012年以后到現在,張陽畫作的主題是“白菜”系列,表現的是秋季豐收時節,農民喜氣洋洋收割白菜的場景。
張陽說:“一次采風時,我們發現了場景,這使我們都很激動,當天就拍了很多照片,回家后覺得不夠,第二天又去和農民們相處了一整天。”張陽收集了很多素材,拍了幾百張照片,回家后重新構圖,創作了《十月家園》《豐收的季節》《守望家園》等一系列作品,并先后十幾次在各種展賽中獲獎,得到了藝術界的關注。
目前,張陽正在創作的作品主題依然是東北農民,說起即將創作的內容,張陽很激動,他說,在一次采集素材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很令他感動的細節,就是一位賣魚的農民,身后自行車的車筐里放著一張半展開的福字,這一抹喜慶的紅色使這個攤販的生活場景增添了亮色和內涵。“我想創作一系列題為《臘月二十八》的油畫,集中表現賣魚的老兩口,畫他們面前一排排的大鰱魚和身后的一片紅燈籠,以及車筐里放著的福字,表現他們期待著新年的美好心愿。”
張陽的現實主義畫風,深受19世紀法國現實主義畫家古斯塔夫·庫爾貝的影響。他在收集素材時,對于角度、光線的要求一直很嚴謹,而且能和老百姓走得近、談得來,于是也就注定了他的題材多以農村百姓為主。

張陽說:“現實主義創作,就是運用畫面講述一個故事,表現出他們對幸福生活的期待。用一張靜止的畫面給觀者講一個故事,并從中看出很多思想在里面,這是很難的,有時把畫面內容刻畫得更深刻,僅僅局部很小的一個細節,就會盤活整個畫面。我畫畫就是很直接的,沒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技法,用最樸實的筆法,表現最樸實的農民和場景。”

“很多人找了一輩子,也未見找到契合自己的題材,因為總有一些東西注定只能接近是你的,當你離它很近時卻又擦肩而過了,蕓蕓眾生,每天都在上演相同的故事,如此說來,張陽是幸運的,無論是礦工老王也好,收白菜的大姐也好,他們一直在做自己分內的事,很專注、很敬業,只不過與此同時一個畫畫的小伙兒也在做著屬于自己的事,兩條線相交,一張張充滿生活氣息,飄散泥土芳香的作品就應運而生了,誕生得又如此之自然,好像戀人久別偶然地邂逅。”中國工筆畫學會副主席張策在談到張陽的作品時,贊嘆地說。



張陽

1983年出生。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遼寧省美術家協會理事、遼寧省青年美術家協會理事、鐵嶺市美術家協會副秘書長、鐵嶺青年美術家協會副主席、鐵嶺油畫院畫家(副院長)、全國“80水彩”公社成員。
2018年國家藝術基金獲得者(項目并獲得成果運用)。2015年被中國文化旅游部派遣去非洲三國藝術考察交流。作品多次參加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的全國展覽并多次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