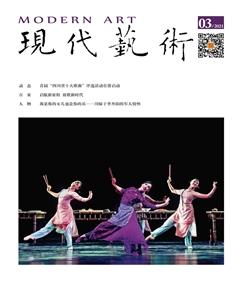從“懸崖天路”到“三尺講臺”
王軍



陳萬
CHEN WAN
四川音樂學院教授、藝術處副處長、碩士生導師,四川省學術與技術帶頭人后備人選,四川省青聯委員,四川省音樂家協會理事,四川省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志愿者協會首批會員。
作品曾獲得中國音樂金鐘獎、文化部文華獎、巴蜀文藝獎、四川省“五個一工程”獎等,演唱曾經獲得文化部第八屆全國聲樂比賽文華聲樂節目表演獎、四川省第二屆聲樂大賽專業組民族唱法第一名、第十三屆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重慶賽區民族唱法第一名、首屆川渝情歌大賽金獎等。
重慶市開州區開縣滿月鄉雙坪村有一條特殊的農村公路——盤旋于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方是巖石,外側是絕壁深淵,云霧繚繞,險象環生,被稱為“懸崖天路”。“天路”建成之前,村民想要出村,需要在山路間手腳并用花上4個小時,人員傷亡等意外時有發生。為了擺脫貧困的命運,當地村民自發集資造路。如今,該村已成為人們心向往之的“世外桃源…‘天然氧吧”。
“通往我家的‘天路上人民日報了,那是我兒時出山的必經之路,是我練就攀巖絕技的好場所哦。”看到了家鄉的道路被媒體報道,四川音樂學院歌劇合唱系教授陳萬在朋友圈發了這樣一條微信。而鑿這條天路的背后,也夾雜著陳萬父親的心血。20多年前,年富力強的陳萬父親和鄉親們一起用勤勞的雙手開辟出了被稱為“懸崖天路”的通鄉公路。
20多年來,這條與外界唯一聯系的通道讓像陳萬這樣的大山兒女一批又一批的走出了高山,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進一步改變著家鄉的面貌。
從事大學音樂教育長達十余年之久,培養了無數優秀的音樂人才,參加了全國各種大大小小的音樂比賽,并獲獎無數,川音最年輕的教授一一陳萬在發出微信不久后,他的朋友紛紛留言感嘆。他也被朋友們稱為“大山里走出來的音樂才子”“沒想到音樂家深藏不露,居然還是攀巖高手。”
這位從大山深處走出來的男高音歌唱家,用歌聲真誠地回饋著大山給予他的愛。雖定居成都,但在陳萬回老家所創作的MV里,曾多次拍攝了那條讓他魂牽夢繞的“懸崖天路”。
作為從這樣的懸崖天路走出來第一位大學生,陳萬有怎樣的成長經歷,童年的他如何在懸崖峭壁上行走的,帶著好奇,我們對陳萬進行了獨家專訪。
背一百多斤肥料穿行懸崖峭壁練就一身攀巖本領
1978年,陳萬出生在重慶市開州區滿月鄉雙坪村4組,父母都是當地土生土長的村民,祖輩世世代代都在大山深處辛苦耕耘。
孩提時代,由于村里沒有通公路,交通極為不便。年幼的陳萬出過最遠的遠門就是跟著父母走三個小時的路到山腳底下,在河邊集市上買一點家里的生活必需品。
從小與牛羊為伴的陳萬,和放牛的小伙伴們漫山遍野奔跑,練就了他強健的體魄。
在陳萬十一歲左右的時候,陳萬就能夠從山下的集市上,背一百斤的肥料,穿梭懸崖峭壁,用長達五小時左右的時間,背到家。“小時候穿梭在懸崖峭壁上,常常是背上背著重物,手就要緊緊抓住山上的樹和植物,一步一步爬上山頂,往往不敢把頭扭過去看身后,因為身后就是上千米的懸崖。”陳萬回憶。
同時,每年玉米豐收后,陳萬就會背一百斤的玉米到山下集市,換二十多斤米。
“吃的是三大坨(玉米、紅薯、土豆),睡的是苞谷殼。”與外界的隔絕,匱乏的物資,封閉的交通環境,讓陳萬一家和其他的村民陷入了深深的貧困境地,自給自足的生活讓村民的生活止步不前。
在村小僅有7名同學的班上,陳萬發奮學習,在小學畢業那年,以全村第一名,全鄉第三名的好成績考入當地的重點中學大進中學讀書。
而當時,沒有出村的公路,陳萬也只能攀爬過懸崖山谷,手腳并用花上4個小時,直下800米高的懸崖峭壁,沿著彎曲的山路外出求學。讀初中的時候,為了節約幾元錢,需要走兩天一夜。就這樣,陳萬靠著自己頑強的毅力,在高中時候憑借自己過人的音樂天賦,考入了西華師范大學音樂學院。
陳萬告訴我們,考入大學后,在1997年回到家鄉,得知鄉親們正在打算鑿山路,而父親作為雙坪村4組的生產隊長,也是隊里的帶頭人。
“古代有愚公移山,再苦再難,我們也要把這條路修起來。”陳萬告訴我們,據父親回憶,當時村中有400多位村民,其中300多位村民每人出資1500元左右,出不起錢的村民要么出讓土地,要么以工抵資,就這么一點一滴地去實現“通路夢”。
“當時父親把所有的精力和時間都花在修路上,即使冒著生命危險,也是咬緊牙關,帶領生產隊的老百姓齊心協力修路。”陳萬告訴我們,由于在外地求學,也很遺憾沒有見證家鄉的懸崖天路是怎樣修成的。據父親回憶,當時每家每戶積極性很高,都是男女老少全家出動,只為了早日實現“通路夢”。
直到大二的時候,從外地放假回來的陳萬驚呆了,閉塞的村子真的通路了。“當時真不敢想象,村民們真的在陡峭的懸崖上活生生地鑿出了這樣一條山路來。”陳萬說。
隨著當地黨委和政府的重視,兩年后,家鄉的山路變成了柏油馬路,不久后,馬路一旁又被安裝了防護欄。陳萬告訴我們,隨著馬路的修通,村民的糧食作物,中藥材,各種家禽都可以很順暢的到當地鄉鎮售賣,陳萬的家庭和村里其他村民也逐漸改變了貧窮落戶的生活,生活也越來越好。
川音學府最年輕教授用歌聲回報家鄉
從“懸崖天路”走出來的陳萬,曾經在心里暗暗發誓,作為村里第一個大學生,一定要為家鄉爭光,要通過歌聲讓更多的人了解在重慶邊遠的開縣有一條如此驚險的天路,有一群如此偉大的村民。
陳萬深知從大山走出來的不易,他在西華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扎實學好聲樂理論知識,并以優異成績保送研究生,后留校任教。2010年,他被調入四川音樂學院任教。
歷經千辛萬苦走出大山,離開家鄉,可家鄉的父母讓他日夜思念,淳樸的鄉親們讓他感到溫暖。近年來,他創作了多首關于老百姓的歌曲,如《老百姓的歌》《我的家鄉我的村》《成都好耍》《四川人的龍門陣》等耳熟能詳的歌曲,也參加了近百場為老百姓義演的文藝活動。
“也許是從大山走出來的原因,我聞著泥土的芬芳長大,我對樸實的農民有著最天然的親近。”陳萬說道,每次去到甘孜、阿壩等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義演,他都會邊唱歌邊走下臺去握著鄉親們的手,那長著厚厚老繭的手,就像是握著他自己父親的手。
為了表達對母親的眷戀和愛,有一年暑假,陳萬驅車回到了家鄉,為媽媽錄制了一首歌曲。
“拉著媽媽的手,又是離家的時候,輕輕擦去媽媽的淚,把媽媽靠在胸口,媽媽抬起頭,為我理一理衣袖,輕輕擦去我眼角的淚,叫我放心的走。”“走過一灣一灣,媽媽還在山頭,一聲呼喚一行淚,淚人小溪隨我流,我向媽媽揮揮手,別樣滋味在心頭,默默地祈禱春和秋,不要白了媽媽的頭。”
“這首歌的歌詞是自己含淚寫出來的,在懸崖天路的村里,是媽媽勤勞的雙手將我送出大山。”陳萬告訴我們,而自己學成歸來,能夠為母親,為家鄉做些什么呢,那就用藝術記錄家鄉的變化,記錄家鄉的親人,唱最深情的歌給大山里的鄉親們聽。
“每次離家出走,媽媽都會在山頭向我不停的揮手。”在陳萬拍攝的《媽媽還在山頭》這首MV里,記者看到了懸崖天路多次出現在視頻畫面中。MV的男主角陳萬在山頂上放聲高歌,大山的美麗景色也一覽眼底。
正如陳萬所言,從山里走出來的讀書人,一定要牢記鄉親們鑿天路的毅力和勇氣,這股干勁和闖勁也將一直鼓勵著他在音樂道路上不怕困難,勇往直前。
為家鄉寫歌希望家鄉早日脫貧致富
2017年春節,陳萬一家回到了故鄉。享受闔家團圓之際,他也看到了揪心的一幕。陳萬老家村里有一位他認為曾經最美的姑娘劉夢翠,家里還有子女在讀書,她身患尿毒癥,與病魔抗爭2年多了,一家人欠債了30多萬元。為了幫助這一家人走出困境,陳萬在朋友圈呼吁身邊的朋友獻愛心,幫助劉夢翠一家。
短短一天時間,得到了無數愛心人士的幫助,陳萬一共籌集22408元善款,并將這筆愛心基金交給了劉夢翠本人。收到善款的劉夢翠看到了闊別多年的陳萬,眼眶濕潤了,沒想到,正如劉夢翠所言。“雖然離開家鄉那么多年,當上了大學老師,可路兒(陳萬小名)沒有變,他還是那么熱心地幫助我們,讓我們感覺到他永遠都是屬于我們雙坪村的”。
如今的陳萬,盡自己的努力,播撒著愛,傳遞著愛,幫助著像劉夢翠這樣的老鄉。正如陳萬所言:“雖然離開了生養我的大山,但是,如果沒有曾經父老鄉親們一元一元的湊錢給我交學費,我也不可能讀上音樂學院,更不可能走上如今的藝術事業,因此,我要用我的歌聲回報愛,回報家鄉。”
看著家鄉那條熟悉的懸崖天路上了人民日報,被各大媒體關注,陳萬心里既驚喜又自豪。“我為我出生在這樣的大山深處而自豪,讓我在音樂事業上,更加的務實,學會了創作貼近老百姓真正生活的作品,我永遠是大山的兒子,我也會用我一生為我的家鄉歌唱。”
“小時候,我赤腳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聽著父親的山歌,與牛羊為伍、驕陽為伴,過著快樂的童年生活。”在陳萬新出的專輯里,他這樣寫道,“后來,我憑著大山賦予我的強健體魄、祖先們饋贈我的山歌走出了大山,走進了藝術的殿堂,走上了歌唱藝術的道路。”
目前,陳萬已經在四川音樂學院教書育人數個年頭,為祖國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藝術人才。
“為了讓更多人知道我的家鄉,我將在近期寫出一首關于滿月鄉的歌曲,為自己的家鄉代言。”正如陳萬所言,回望他走過的路,從懸崖天路走過的歲月,既滿心歡喜,又淚眼朦朧。
“唯有把對家鄉的眷戀和熱愛,對淳樸勤勞鄉親們的歌頌和贊美化成最真摯的音符,變成最真誠的歌聲,以歌聲為媒介,用藝術搭橋梁,讓外界更多的朋友了解在重慶開縣有這樣一個‘世外桃源,”陳萬告訴我們,“讓更多的人慕名而來,通過旅游、農產品等收入,讓家鄉的父老鄉親們早日過上幸福的美美的小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