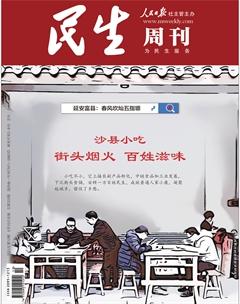小心, 家庭攝像頭正偷窺你
于海軍

如今,攝像頭已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尋常物件。有些用戶在家中裝上了網絡智能攝像頭,老人獨自在家是否安全、有沒有陌生人闖入等,這些實時情況都可以通過手機查看。
然而,“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時,也給不法分子帶來可乘之機。在一些QQ群和網站貼吧,有人公然售賣破解攝像頭軟件,分享他人家庭私密影像,給用戶隱私安全帶來威脅。
無論是在公共場合還是私人空間,人們安裝攝像頭的初衷都是為了安全或者便利,網絡攝像頭不是“法外之眼”,專家指出,應采取技術措施與法律手段,斬斷販賣公民隱私的黑色產業鏈,不能讓其成為個人隱私安全的隱患。
有機可乘
西安的馬先生不久前在客廳安裝了網絡攝像頭,主要是出于安全考慮,以便能查看家中實時情況。但使用后不久,他發現攝像頭在未進行任何操作的情況下,自己動了起來。“裝了有一段時間了,一天我躺在沙發上,發現攝像頭動了一下。”馬先生說,這讓他很意外,有種被偷窺的擔憂。經過排查,朋友告訴他可能是手機上的軟件密碼被不法分子破解。
在朋友的建議下,馬先生更改了初始密碼,上述情況此后再未發生。不過,他對網絡攝像頭的使用謹慎起來,對其拍攝范圍做了調整。
日前,在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審結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巫某某通過一款APP控制了18萬個攝像頭,涉及眾多私人住宅和公共場所。
據了解,“客戶”可在該APP上付費注冊會員,觀看、保存攝像頭拍攝的畫面。該案中,巫某某用網購的黑客軟件竊取某品牌網絡攝像頭的用戶數據庫,并通過社交媒體找技術人員開發違法APP。
無獨有偶,2018年3月,丁某在QQ群里看到有人出售一款軟件,能侵入他人攝像頭,觀看視頻畫面。丁某出于好奇,花錢購買了該軟件。2019年5月31日至7月27日期間,丁某成功侵入367臺網絡攝像頭并截取畫面,供自己觀看。
法院審理認為,丁某違反國家規定,對計算機信息系統實施非法控制,情節特別嚴重,已構成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家庭網絡智能攝像頭的使用情況較為普遍。數據顯示,2020年第四季度,中國家庭安全監控設備銷售額接近6億美元,出貨量為817萬臺,同比增長24.9%。
隨著智能手機、智能家居等設備的普及,網絡攝像頭逐漸成為一些用戶生活的“標配”。
然而,隱私保護已成為網絡攝像頭行業迫切需要回應的關鍵問題。互聯網問題專家高揚坦言,網絡攝像頭的技術特性可能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其利用部分產品的技術漏洞破解大量攝像頭IP地址,高價售賣破解軟件與“偷窺套餐”。有商家未經用戶允許遠程操縱攝像頭“直播”,給公民隱私帶來威脅。
《民生周刊》記者梳理資料發現,民法典對隱私權的定義和保護已作出清晰規定,網絡安全法也對網絡產品、服務提出明確要求。在相關案件中,利用黑客手段破解網絡攝像頭IP并販賣內容的行為,已經觸犯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等條款。
不可大意
高揚分析,攝像頭產品質量瑕疵、云端安全防護脆弱、應用端使用弱口令等都可能導致網絡攝像頭泄露隱私。據介紹,目前不法分子攻擊網絡攝像頭的方式主要通過攝像頭終端、手機端攝像頭應用和云端數據信息竊取。
高揚建議,市場監管部門有必要從生產環節強化監管,要求生產廠家在代碼防護、身份鑒別、弱口令校驗等方面達到國家標準,避免非法破解事件。企業也應當完善設計,不斷更新攝像頭安全防護程序,指導用戶加固安全措施。同時,公民應提高網絡安全意識,購買正規廠商生產的攝像頭設備,設置高級別防護密碼,及時更新攝像頭安全防護程序。
有業內人士強調,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用戶對攝像頭的安全意識不高。用戶在選購攝像頭的時候,只會從外觀上看好不好看,并不去了解網絡安全性,而且很多用戶把攝像頭買回來就直接用弱口令或者默認密碼直接使用,這些都會給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機。
《民生周刊》記者了解到,市場上主流的攝像頭生產廠家,都會把安全性當作重中之重,但是,在安全問題上沒人敢做百分之百的承諾。有科技公司負責人坦言,目前導致隱私泄露的諸多因素中,用戶的防范意識不強也應引起注意。
杭州某科技企業負責人姜先生接受《民生周刊》記者電話采訪時建議,企業應該禁止用戶直接使用默認的用戶名和密碼登錄,個人用戶要盡量使用復雜的密碼并定期修改,回家后最好將攝像頭關閉。
在智能設備越來越普及的今天,保護自己的隱私不僅需要相關部門監管、科技企業賦能,還需要用戶自己主動防護。
姜先生提醒,作為消費者,在選購設備時,最穩妥的方法是在正規渠道選購產品,切勿貪圖便宜,購買“三無”或者山寨產品。非必要的情況下,智能攝像頭盡量不要聯網。不要使用原始預設的、過于簡單的用戶名與密碼,要定期更換密碼。
此外,攝像頭一定不要正對臥室、浴室等隱私區域,也要留意攝像頭角度是否發生過變化,養成定期查殺病毒的好習慣。
不過,高揚也表示,對于網絡安全也不必過于恐慌,相關部門在對抗不法分子過程中也積累出了許多經驗,用戶只要能夠保證對新技術的及時掌握及提高警惕,還是能起到很好的防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