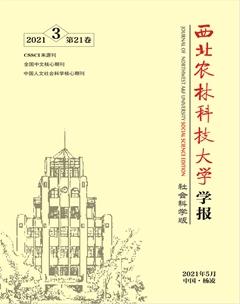勞動過程視角下農業技術應用的社會條件


摘 要:在《制造綠金》一書中,弗里德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勞動過程理論,以美國生菜產業為例探索新技術應用的社會過程與社會條件,突出強調了“勞動者生產組織”命題對一項新技術采用的重要作用。同時有關作物結構的分析為商品系統分析方法的提出以及世界商品鏈、食品體系研究奠定了基礎,這不僅拓展了農業社會學研究的邊界,也為中國農業社會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勞動過程;勞動者生產組織;作物結構;社會條件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1)03-0097-09
收稿日期:2020-12-23"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3.1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17ZDA113);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 (17BSH002)
作者簡介:李陽陽,女,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與農村社會學。
20世紀70年代,農業社會學在挽救農村社會學的危機之下誕生[1]。此時學界對于農業分析的主題主要聚焦在小農農業或家庭農場持續存在的現實性問題,因此形成了恰亞諾夫學派以及與此相對的新列寧主義學派,后者認為農業內部以及農民階級之間存在強烈的分化[2]。與此同時,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生產工具的改進往往會形成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嵌套著社會關系的革新。因而,在農業資本化進程中,何種因素影響新技術的采用至關重要。作為第一代農業社會學家的弗里德蘭(William H. Friedland)延續了馬克思主義傳統,將農業技術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探究生產中分化的農業、雇工與一種新技術采用之間的社會互構過程。
一、弗里德蘭及其生活時代的美國農業
(一)弗里德蘭及其“農業觀”
弗里德蘭(以下簡稱“弗氏”)出生于紐約州斯塔頓島(Staten Island)的一個俄羅斯猶太移民家庭。高中畢業后,曾在底特律的汽車裝配線上工作了10年,并成為了一名勞工組織者。在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深受馬克思主義學者布洛維等人的影響,尤其關注社會運動與勞工組織相關問題以及權力集中在全球農業公司時代下農業領域的農民和農場工人問題,并在之后發表了一系列著作論述相關議題。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弗氏認為農業政治經濟學分析是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學。自1970年代開始形塑的農業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于農政轉型的推演理論,例如列寧關于農民分化的理論。其次,早期關注于農政問題,現在關注于轉型時期家庭農場的持續性現實,以及資本主義農業如何與現代工業農業相區分的問題[3]。弗氏則主要著眼于資本主義農業之下的農業轉型與農民的分化研究。在他看來,農業與其他非農業生產部門一樣最終會依據生產特性進行分化,只是因其不同于工業生產的屬性,導致農業經歷了比其他工業部門更慢和更不平衡發展過程。前資本主義時期農業生產作為一個整體,種植者可以單獨完成從種植到收獲的全部階段。而在發達的資本主義時期農業生產被工具制造、資本、設備、種子生產與灌溉等一系列的勞作過程所分割并加以控制[4]16(見圖1)。勞動過程的分化直接為資本主義滲透到農業生產提供了條件,進而,農業企業得以有機會通過擁有機器控制勞動力生產,改變農業的勞動過程,同時從農業生產的上游和下游攫取利潤。
鑒于此,1981年他撰寫了《制造綠金:生菜產業中的資本、勞動與技術》(Manufacturing Green Gold: Capital,Labor,and Technology in the Lettuce Industry)(下文簡稱《制造綠金》)一書,試圖以技術變革打通自然科學的技術研發與社會生產之間的關系,構建一個宏觀的囊括自然、社會與人文的農業社會學模型。該書成為了從勞動與組織角度分析農業技術應用社會過程的經典著作。
(二)《制造綠金》撰寫的經驗背景
對于該書的主題而言,在經驗層面有兩個重要的背景。其一,美國農業先后經歷了一戰之后的黃金時期,繼而農業基礎設施的興建以及贈地大學對農業科技的推廣等諸多工作使得20世紀初的美國較早地邁入了一條農業資本化之路[5]。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農業發生明顯變化。隨著農產品大量出口,農業機械化水平不斷提高,呈現出大農場兼并小農場之勢。主要表現為農場數目銳減,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農場數達到最高峰700萬個,到1978年底已經不足270萬個。農業生產越來越集中到少數農業公司或者大農場手中。同時,技術、資金的投入使得美國農業資本化程度越來越高,1977年底大農場農產品產量已達到全國農產品總銷售額的85%[6]。
具體事件上,美國與墨西哥政府于1942年聯合簽訂了支持墨西哥勞工短期到美國務工的項目——布拉塞羅項目(Bracero Program)。該項目主要是為了緩解墨西哥的就業壓力,同時為美國農業生產提供廉價勞動力。項目前后歷時22年,于1964年解體。弗氏認為項目解體直接切斷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地區蔬菜生產的勞動力供應,使得以往政策支持從墨西哥獲得廉價勞動力的機會喪失。在此轉型時期,技術的采用往往根據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相對資本的價格狀況進行調整。因而人少地多、勞動力缺乏且成本較高的美國,采用了勞動力節約型的農業技術[7],走向了資本密集型的農業機械化發展之路。
二、技術組織變遷分析新框架
弗氏的研究主要以馬克思的勞動過程理論和產業社會學/組織理論作為理論基礎[4]4-5。他認為馬克思的勞動過程理論強調勞動者和資本家的區分,產業社會學強調成員在多種情況下和不同的環境中如何組織起來,這兩種理論在1980年代之前并沒有用于農業社會學的分析。鑒于此,弗氏嘗試結合兩個理論建立起技術變遷過程與生產組織社會結構之間的連接。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弗氏在書中直言,他關于勞動過程理論的分析以布洛維和諾布爾的研究為基礎,但是超越二者的研究范圍。即并沒有從階級關系與階級對立角度理解農業生產的勞動過程,對于勞動過程的研究也不僅限于生產和收獲兩個環節。在此基礎上,作者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勞動過程理論,將農業概念化為生產和交換在內的社會組織系統。從勞動過程中抽離出生產的社會關系,并構造出以此過程為核心的農業社會學模型(見圖2)。
(一)機械化的組織困境
1.無結構的雇工招聘。布拉塞羅項目的終止切斷了墨西哥的勞動力供應,引發了生產組織的變化而非一場單純的技術變遷。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不是有了機械就可以實現機械化”,農業機械化也從來都不是機械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8]。自1964年勞動力項目終止直到1980年代,生菜收割的機械化也并未完全應用。這在很大程度上在于鑲嵌在生產中的勞動力并沒有形成與新技術匹配的組織結構。在生菜生產的勞動力市場中,以往勞工的招聘和組織不僅僅取決于種植者的組織,也取決于所涉及的技術實踐和處理作物的方式。機械化之前勞動力的招募是一種無組織的結構市場,農業勞動的準入門檻很低。更確切地說,這種半內部化的收割工人,以服務外包的方式從事收割工作。招聘采用熟人介紹而非市場競聘的方式進行,因而一名新收割工必須由一位擔保人介紹才可以進入勞動場所。擔保人與新收割工基于親屬、同伴與友誼關系,同時擔保人為新收割工的過失承擔責任[4]59-60。
生菜生產中收割工與包裝工是最重要的工種,因而需求與勞動報酬也相應最多。墨西哥勞工在美國生菜生產行業中主要處于收割環節,因此勞動力供應中斷直接引發收割環節的機械化,這也是在整個生產領域機械化最先開始的地方。除了收割工作之外,生菜生產中用工最多的生產環節當屬間苗與除草,如何最大程度減少用工、節省成本成為生菜生產公司市場競爭的首要砝碼。例如,作為此時美國生菜生產巨頭的安特爾公司(Antle Company)巴德·安特爾公司(Bud Antle Company),現在為美國蔬菜加工巨頭都樂(Dole)的子公司。在20世紀后期曾為美國生菜行業的巨頭,與著名的陶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合作推動塑料薄膜包裝技術應用于生菜保鮮,并曾在生菜真空冷凍、運輸、包裝等方面一度成為整個生菜行業的技術風向標。 采用溫室育苗的方式,在生菜生產的源頭施加藥水以控制雜草的生長。
然而由于勞動密集型農業工人效率極高,機械化系統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種植者和運輸商不愿嘗試一種新的收獲系統。因此,種植企業通過為墨西哥勞工辦理綠卡,同時依靠之前建立的勞工擔保人關系網絡來保證勞動力供應,努力維持著這種舊有的生產組織結構。在弗氏看來,舊有的勞動力組織結構是阻礙機械化應用的主要原因。應用新型農業收割技術對種植者來說,則要建立一套與新技術相適應的新型勞動力組織結構。
2.節省人力尚未發生。在機械生成與使用之間有著技術推廣的社會過程。不可忽視的是生菜收割的技術轉型包含著技術變遷與既有社會條件不斷互構的復雜過程。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已經開始從政策上禁止美墨兩國勞動力流動,但在生菜生產中仍未實行機械化收割。弗氏預測生菜機械化替代率只有25%,相比番茄99%的替代率而言,生菜的機械化似乎并沒有大幅度地減少雇傭工人。同時,機械化的使用并沒有帶來整個生菜生產流程人員的減少。在系統性的收割技術之下,僅僅是收割工人數的降低,同時隨著機器效率的提高所需其他流程人員增多,塑料薄膜包裝人員、機器協調、維修等工作人員的內部化產生。通過對比機械化收割前后勞動者的生產境況,弗氏認為機械化收割僅僅使得技術變得先進了,原始勞動關系(primitive labor relations)一般而言,最初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發展建立在原始積累過程和原始勞動關系過程之中。原始勞動關系是勞動關系發展第一個階段,主要表現為勞資關系的嚴重不平等。資本家通過“過度延長的勞動時間”“強化勞動和工資形式”以及“工資的下降和無償勞動”等方式,形成一種對勞動者的專制性支配。而勞動者無法與企業相抗衡,進行關于勞動工資、條件、福利等方面的談判。 仍舊未變[4]41-42。布拉塞羅項目解體之前,棚戶工人(shed workers)受到《國家勞動關系法》的保護,然而田間工人(field-workers)被排除在外。此外,田間勞動力比棚戶勞動力更為便宜,不僅因為它沒有工會組織,而且它可以通過墨西哥人不斷移民到美國而獲得大量的供應[4]65-66。
(二) 作物結構的阻隔
在研究生菜機械化之前,弗氏主要分析了番茄生產的機械化過程。他認為布拉塞羅項目的終止在番茄行業中是致命性的,并且迅速導致了番茄收割的機械化。具體而言,由于番茄生產中廉價勞動力和可控勞動力的集中性,勞動力項目終止切斷了生產者對勞動力的控制[4]133。為了大幅度減少勞動力需求,達到高于之前勞動力系統的效率,整個生產系統進行了改造。最終機械化的應用使得番茄收獲過程類似于工廠的生產系統,其雇傭人數從1964年的5萬人下降至1972年的近2萬人。同時更重要的是,番茄是一種一次性收割農作物,即從植株上收獲之后就進入加工階段[9],而與生菜復雜的商品體系不同,因而其機械化更容易實現。
在弗氏看來,生菜的復雜生產體系主要來源于其不易存儲的特性。不同于小麥、玉米等穩定的可長期儲存的農產品,生菜更容易成為一種“賭徒經濟”式的作物。即生產者面臨生產一箱15美元的黃金,還是2.5美元的經濟災難這樣天差地別的選擇,因此需要更加縝密的組織結構來運行[4]43-45。此外,更為關鍵的是生菜作為美國重要的國民蔬菜,需要滿足家庭一年的消費需求,52周送往全國各地,甚至進行國際貿易出口到亞洲、歐洲等地區。因此種植商們會根據市場需求安排種植面積與時間,形成同一片田野之下生菜成熟期不一致的田間市場。故而生菜行業的機械化會形成比番茄機械化更為復雜的組織結構。生菜的生產主體是由高度專業化,且全面掌控整條產業鏈的企業生產。同時生菜生產也需要大量的技術與機器設備,導致個體種植戶難以跟隨生菜行業的技術跑步機,整個行業向更大的一體化公司方向發展。在布拉塞羅項目終止后,美國生菜生產商開始用機械與技術“制造”出“綠色的金子”這一進程。他們與農業院校合作,相繼研發了一套包括真空包裝、冷藏、運輸以及收割等的一系列配套技術,使得利用技術制造出“綠色金子”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概括而言,作者基于番茄與生菜兩種不同作物的生產特性,在同樣勞動力短缺的社會現實下卻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從更廣闊的視角比較了兩種作物的生產系統以及不同的機械化過程,從而揭示出每一種作物都有自己不同的組織方式與勞動過程,同一種作物的機械化并不能帶來另一種作物的機械化。不同作物的生產制度有不同的資本化程度與進程。機械化適用于那些看起來好改變并且能夠改變的部分[4]30-33。
(三)未完成的技術
同時在技術層面仍然存在阻礙機械化收割的瓶頸。20世紀60年代中期收割機器的研發并沒有完全解決生菜機械化收獲的所有技術難題,其主要原因在于生菜的成熟不完全一致,通過技術手段判斷生菜的成熟度仍舊是一個難題[4]92-95。機械的應用是一個系統性工程,機械化生產的開始如同一腳踏上了技術的跑步機,一旦機器開啟便需不斷的加大投入以免被甩出跑步機[10]。因此可以預測一些有能力繼續經營下去的公司會采用一種代價高昂的漸進式變革戰略“加大賭注”,而另一端則會迫使財力較弱的公司退出競爭[4]134。例如,20世紀70年代收割機研發成功之后,緊接著面臨的是如何處理生菜包裝問題以更快地提高生產組織效率。然而,直到80年代初還沒有一種令人滿意的包裝技術。因此研發與使用相應的配套設施與生產組織成為機械收割機之后的主要議題。最終如前所述,種植者們只能通過將布拉塞羅的勞工轉變為綠卡工人,并發展出現有的收獲生菜工結構來解決勞工短缺問題。
綜上所述,在墨西哥與美國勞動力流動合約解體之后,以及隨著替代勞動力技術的成熟,蔬菜生產領域并沒有即刻發生技術的更迭。這在弗氏看來主要是由于技術應用的社會條件并不成熟,舊有的勞動力組織結構制約了新技術的應用。新技術的發生不僅僅是機械技術的田野應用,更重要的是如何組織人的問題。同時機械化并不能隨意從一種作物移植到另一種作物,農業機械化的應用要考慮不同作物的勞動力生產組織結構。換言之,在弗氏看來,技術、組織與勞動力是綜合性的統一體,技術變革的過程必須與建立在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系聯系起來。
(四)機械化后的社會預測
弗氏基于現有調查數據以及番茄機械化的社會結果,從種植者的組織境況、雇工的勞動組織以及雇工的社區生活三個方面,對尚未完全機械化的生菜收割導致的社會后果進行了預測。
在種植者的組織境況方面,雖然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生菜生產系統已經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家生菜公司手中,但機械化的應用無疑將會導致另一種社會后果。包裝生菜在保持產品質量的前提下,與裸生菜相比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因此收割的機械化將加速生菜包裝的趨勢。隨著一些規模較小的種植者逐漸被排擠出去,生產的集中度將會增加。除了生產者的集中,地域的集中度也會加劇[4]111。
在雇工的勞動組織方面,弗氏根據公司采用收割機器的數量與品種計算出其雇工替換率平均達到63.32%[4]112。在向機械化收割的轉變中,主要的結構轉變可能是從男性向女性轉變。在生菜生產過程中工人們通過工會尋求企業之間穩定的勞動關系,導致雇工結構開始明顯內部化。這一舉措將對勞務承包商產生嚴重影響,因為他們將不再被需要為生菜招募除草間苗的臨時工[4]119。在番茄收割機上,同時會因為勞動分工而顯現出有關工位的社會區隔。諸如,由于一些位置比其他位置更受歡迎,因此對優勢位置的占取成為一個家庭、親屬群之間,而非工人個人間的競爭。一個有經驗的家庭可能會抓住傳送帶上最好的位置,拒絕移動從而保護自己,這種情況在流水線的生菜生產中同樣存在,雇主可能會通過雇傭流動的男性和穩定的女性來解決勞動力的供應問題。
最后,弗氏預測在向機械化收獲和穩定就業過渡之后,會促使綠卡工人轉向美國公民身份,并開始參與學校教育等相關的公共活動[4]126。同時對美國墨西哥生菜收割工所在社區的公共基礎建設、社會服務、住房等層面均產生影響。
三、學界評價與后續研究
(一)他山之石:理論與研究貢獻
《制造綠金》出版后引發了農業社會學的高度關注,學者們對該書在農業社會學中的學科地位、理論貢獻以及方法論問題等多個層面進行了評析。由此出發,弗氏啟發了后來的多項研究。
巴特爾(Frederick H.Buttel)認為《制造綠金》提出了繼曼·狄金森(Mann.Dickinson)關于農業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不一致的命題,弗里德曼(Friedmann)關于農戶簡單生產形式持久性的命題,以及菲利普(Michael Philip)關于“外部環境”限制導致農業資本主義轉型困難命題之后的第四種因素,即勞動者與生產組織的命題[11]。正如弗氏在書中所言,與20世紀70年代后期加州番茄生產商迅速實現機械化收割不同,生菜生產商出于多種原因在機械化初期遭遇了發展的屏障。例如即便在收割技術已經成熟的條件下,生菜公司對舊有生產組織的路徑依賴則導致了機械應用的失敗。加之生菜作物的生產特性以及生菜機械收割中遇到的技術困難,新型技術應用之后配套設施與組織重建等困境皆直接或間接阻礙了農業機械化的進程。因而在弗氏看來即使在技術條件已經成熟的情況下,如若忽視由人組成的生產組織,新型農業技術革新也是難以發生的。這不僅豐富并擴展了馬克思主義勞動過程理論內涵,也將研究范圍從工業領域擴展至農業生產之中。弗氏也給后繼者提供了一種研究農業技術與勞動、資本之間關系的分析方法[12]。
早期農業研究中對與女性的研究很分散,并沒有把女性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身份來研究,而是將女性作為農場主的妻子、農場幫忙人的身份進行研究,女性在農業研究中作為一個“逃離者”的身份存在。弗氏考察了農業勞動過程中的性別分工,他通過美國整個生菜行業的生產系統,重新將女性放到農業生產與再生產這個更大的生產鏈條中,探索女性在勞動生產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從農耕到農業的過程中,農業生產是以家庭為主的組織活動。隨著農作物種植專業化的發展,農業越來越被卷入到世界農業體系中。農村地區的農業生產更像是滕尼斯的機械團結,而非農耕時期的有機團結。男性會從事一些機械方面、化學農藥方面的農業工作,女性更多是從事間苗除草之類的工作。但是現在專業化的發展,男性在農業遷移中相對女性的優勢凸顯出來,女性要考慮家庭以及家中孩子的照顧,其流動性較男性要低一些,因此作者預測機械化之后會產生與之前完全不同的農業生產性別分工。
(二)理論研究的缺陷與不足
從研究對象來看,邁因斯(Mines)認為弗氏忽視了生菜供應量占整個生菜市場總量將近一半的小農。弗氏僅僅認為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規模生產優于小生產,小農將會在大規模種植者采取機械化的市場壓迫下,難以為繼進而退出市場。然而對于占據生菜生產市場半壁江山的小農來說,如果生菜供應持續過剩,機器化生產就會減少勞動力,小農生產仍舊有留存空間[13]。之后,岡薩雷斯(Gonzales)更進一步批評認為弗氏對于生菜生產行業的論述缺乏農民視角,并沒有關注整個行業工人的特征[12]。正如農業政治經濟學分析農業產業的宏觀結構層面,往往容易忽視作為生產者的雇傭農業工人。在行動者生計的形式理性之外,缺少對于行動者實質理性的深描。
在方法論層面上,弗氏意圖將社會學的方法與理論組合應用于農業社會學中是一大貢獻,但是弗氏并沒有明確指出所謂的社會預測方法以及與番茄生產的比較如何應用于農業社會學。弗氏僅是提供了工業與農業社會的全局視角,通過描述農業生產循環過程以及各個過程中的參與者及其作用,推演出種植者運輸商處于整個生產流程的核心[12]。弗氏意圖將農業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從社會學中脫離出來,建立新的分析方法的嘗試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失敗的[14]。
(三)后繼研究
弗氏的《制造綠金》創作于“新農村社會學”農業技術研究的第三個階段,其對于技術變遷的研究打破馬克思單向性技術發展的論斷,呈現了農業技術變遷動力機制的多種可能,也對于國內學術界關于技術變革社會基礎的研究產生了啟發意義。從不同的動力因素中我們認為農業技術變遷不是單一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農業系統中多種因素的復雜交錯所致。
弗氏以資本主義農業勞動過程的分化為起點,闡明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擴大,使得曾經作為單一的、綜合的農業生產系統逐漸轉移到城市和工廠,農業生產中的農具、食品加工等逐漸演變為專門的機構,推演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可以實現對農村農業生產的滲透。同時,弗氏的研究暗含工業化農業日益取代農耕農業的趨勢。在工業化農業中,農業生產的每一種要素逐漸成為工業生產中可控的部分。同時關于農業生產的化學農藥、轉基因倫理的分析也層出不窮。回歸小農生產、農業價值倫理的呼聲不斷高漲[15]。
在弗氏看來,農業技術是實現農業資本化的主要方式,技術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農業中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這一論述為之后馬克思主義學者關于農業資本化的實現方式提供了以農業技術的視角闡釋資本化進程的分析路線。古德曼(Goodman D)更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了工業通過機械技術與生物化學技術實現了對于農業生產系統的全面滲透,從農業生產上游的種子出售、農機使用中改變勞動過程,將農業納入工業生產的原材料中,達到工業的“占取主義”(appropriationism);又可以在農業生產的下游,借助農產品作為商品在市場中出售獲得利潤的過程,實現工業原料替代農產品的“替代主義”(substitutionism)[16]。
綜上所述,農業社會學學者對《制造綠金》的評述多從該書的理論突破、方法論問題等層面進行分析,并暗含恰亞諾夫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關小農存亡論的爭議。雖然弗氏在農業社會學方法論的獨創方面是失敗的,并且缺乏對行動者行為選擇的分析,但是弗氏在農業社會學理論層面提出的“勞動者生產組織”命題,以及農業中的女性與國家視角不斷擴展了農業社會學研究的邊界。其將農業概念化為與工業等同的生產系統,為馬克思主義技術之下的農業轉型議題奠定了分析基礎。與此同時,弗氏關于作物的獨特分析也為日后國際食品體系、商品鏈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前景。
四、現實價值與對中國研究的啟示意義
弗氏的研究將馬克思主義勞動過程從工業領域帶入農業生產之中,除了雇主與雇工之間的階層對立、權力關系的拉鋸之外,中國學者也開始關注到嵌入在中國鄉土社會中的勞動力結構與組織樣態,以及特色農業生產中的技術細節與組織心態研究[17]。在內外有別的鄉土社會中,外來農業資本進入鄉土后如何處理好與本地勞工的關系成為當前學界普遍關注的議題[18-19]。在鄉土社會中存在“農產品經紀人”,他們正是基于村莊社會內部的關系網絡連接起外來收購商和村莊內小農戶的重要中介[20]。經紀人群體同時也是小農戶對接大市場的關鍵角色,他們如何處理好內外有別的地緣、親緣、業緣等關系,打通村莊與外部廣闊市場的聯系成為今后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
此外,弗氏對于作物的研究打開了農業社會學研究的新視角,正是通過對于美國番茄、生菜等作物生產系統的具體分析,弗氏創新性地提出了“商品系統分析”(Commodity Systems Analysis)方法。該分析往往包括對特定農業商品系統的大量詳細的實證分析,強調跨國公司的結構和戰略,并且主要關注于農業生產組織中的人,以及食品鏈中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系[21]。弗氏關于技術應用的作物結構視角,對于當前我國農業發展尤其是農業產業扶貧中的作物選擇至關重要。不同的作物結構直接觸及到當地的社會文化與生計體系,只有與當地社會生態相契合的作物結構才能更好地發揮產業扶貧的功效[22]。同樣正如斯科特對贊米亞人逃避現世的統治中所談及的木薯與水稻這兩種作物,對于統治而言所具有的不同意義。相比外露的水稻,深藏土壤的特性使得木薯更方便贊米亞人逃避戰亂與征稅[23]。甚至是日常所見所用的棉花,通過資本的觸角可以實現從一顆小小的種子長成為資本主義統治世界的工具[24]。
農業技術應用的社會基礎包含一個多方向的發展模型[25],既有宏觀的生產力發展、國家政策,也囊括中觀的農業技術推廣與擴散,乃至微觀層面農民個體的需求機制等諸多要素。在技術應用的社會基礎層面,國家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科層制之下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中,如何實現公共農業技術應用與家庭分散經營需求之間的對接[26],成為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構建的關鍵環節。國家的政治運動在農業技術應用方面發揮著積極的滲透作用,借助政治效果樹立權威,更有利于達成社區共同體的構建。諸如,階級斗爭與政治運動使得農民在思想層面獲得政治上的認同感,泛化至政府主導的農業技術政策的支持,并在行動上消減對新技術的抵制[27]。同時,相關利益群體能夠從技術變遷中受惠,進而成為部分地區技術革新的前提[28]。同樣,弗氏關于生菜收割技術應用社會過程的分析與社會結果的預測,對于我國技術與社會互構研究具有啟發意義。技術與組織、社會是一個協同演化的過程。技術本身所具有的結構不斷在社會組織中進行著表達,諸如對雇傭勞動力的性別、時間的要求等。同時技術的應用反過來對整個社區的經濟政治產生結構性的作用[29]。
五、結論與討論
《制造綠金》以美國民眾日常生活所需的生菜作為案例,通過對一種新收割技術采用過程的考察,展現了美國整個生菜行業的生產、加工、運輸流程與勞動力組織體系。作者不僅詳細論述美國與墨西哥政府間的勞動力援助計劃撤銷之后機械化生菜收割技術應用的社會條件,同樣預測了生菜收割機械化可能帶來的社會后果。他認為隨著生菜收割技術的發展,會有大量的工人面臨流離失所的狀況,生菜收割工人的組織結構也會發生改變,出現關于性別、種族之間的勞動分化與重組,同時雇工外部化的勞動力會逐漸減少,很大一部分會轉化為內部化的工人。生菜行業的生產在地域與企業方面形成集聚現象,農業機械化還將對墨西哥短工的住房、教育和社會服務等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更進一步來看,作者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學派關于農業技術變遷的動力機制研究,也預測了大農業終將取代小農業的未來。
此外,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弗氏更加關注于宏觀市場與雇工結構,卻忽視了作為勞動者個體的行為選擇、整個行業工人的生計與生活以及占市場一半產量的小生產者組織,因而導致學界對其研究對象與方法論的批評。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其著作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于弗氏將技術與其上的社會關系聯系在一起,并創造性地將農業視為與工業等同的生產系統,延伸了馬克思主義學派內關于二者關系的論述。在農業社會學初創階段強調將“農業”與“國家”帶回來,并融入了性別分析的視角。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注意到了農業社會學中作為行動者“人”的結構要素。其對作物結構的分析旨在建立起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銜接,為之后商品鏈、食品體系研究提供了方法論意義的指導。同時在馬克思主義勞動過程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了農業社會學的理想模型,不僅為分析農業轉型困境提供了一種新的“勞動者生產組織”視角,更為中國農業社會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與方法指導。
參考文獻:""""""
[1] 熊春文.農業社會學論綱:理論、框架及前景[J].社會學研究,2017,32(3):23-47.
[2] BUTTEL F H.Some Reflections o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grarian Political Economy[J].Sociologia Ruralis,2001(41):165-181.
[3] FRIEDLAND WILLIAM H,LAWRENCE BUSCH,FREDERICK H BUTTLE.Towards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e[M].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1:7-13.
[4] FRIEDLAND WILLIAM H,AMY BARTON,ROBERT J TMAS.Manufacturing Green Gold[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5] WILLARD W COCHRANE.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griculture[M].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3.
[6] 胡樹芳.影響美國七十年代農業變化的因素是什么?[J].世界農業,1982(3):19-22.
[7] 速水佑次郎,拉坦.農業發展:國際前景[M].吳偉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30-48.
[8] 徐宗陽.“內外有別”:資本下鄉的社會基礎[D].北京:北京大學,2017:61-62.
[9] FRIEDLAND W H.Destalking the Wily Tomato:A Case Study in Social Consequences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al Research[J].Research Monograph,1975,15:55-59.
[10] 高雪蓮,李陽陽.農業跑步機理論:研究述評與中國實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6(2):35-43.
[11] FREDERICK H BUTTEL.The Sociology of Agriculture[M].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0:78.
[12] JUAN L,GONZALES J R.Manufacturing Green Gold:Capital,Labor and Technology in the Lettuce Industry(Book Review)[J].Social Forces,1984,62(3):829-830.
[13] MINES R.Manufacturing Green Gold,Capital,Labor and Technology in the Lettuce Industry (Book Review)[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2,64(4):796.
[14] GEOFFREY DUNN.Manufacturing Green Gold:Capital,Labor and Technology in the Lettuce Industry(Book Review)[J].Humboldt Journal of Social Relations,1983,11(1):149-152.
[15] ANDREW KIMBRELL.The Fatal Harvest Reader:The Tragedy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M].Washington:Island Press,2002:39-49.
[16] 陳義媛.農業技術變遷與農業轉型: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述評[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6(2):24-34.
[17] 付偉.農業轉型的社會基礎:一項對茶葉經營細節的社會學研究[J].社會,2020,40(4):26-51.
[18] 徐宗陽.資本下鄉的社會基礎——基于華北地區一個公司型農場的經驗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6,31(5):63-87.
[19] 陳航英.田野里的工廠:資本化農業勞動體制研究——以寧夏南部黃高縣菜心產業為例[J].開放時代,2020(3):168-187.
[20] 陳義媛.農產品經紀人與經濟作物產品流通:地方市場的村莊嵌入性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18(12):117-129.
[21] FRIEDLAND WILLIAM.Commodity Systems Analysis:An Approach to the Sociology of Agriculture[J].Research in Rural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1984(1):221-235.
[22] 熊春文,桑坤.作物結構、生計體系與產業扶貧的有效性機制——基于華東一個縣域的經驗研究[J].云南社會科學,2020(3):75-85.
[23] 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M].王曉毅,譯.北京:三聯出版社,2019:72-73.
[24] 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M].徐軼杰,楊燕,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11-17.
[25] 孫啟貴.國外新技術社會學的三條徑路[J].國外社會科學,2010(2):4-11.
[26] 夏刊.我國農業技術推廣運行機制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2012:137-138.
[27] 強舸.國家的策略性:農業技術變遷中的政治因素——基于一個少數民族案例的研究[J].社會,2017,37(5):78-104.
[28] 張茂元,邱澤奇.技術應用為什么失敗——以近代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機器繅絲業為例(1860-1936)[J].中國社會科學,2009(1):116-132.
[29] 張茂元.技術應用的社會基礎:中國近代機器繅絲技術應用的比較研究[J].社會,2009,29(5):21-38.
Social Condi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Process
——Friedland’s Manufacturing Green Gold and Its Inspiration
LI Yangyang,XIONG Chunw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China)
Abstract:In Manufacturing Green Gold,William H.Friedland uses Marxist labor process theory to explore the social process and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by taking the American lettuce industry as an example,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worker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proposition in the adoption of a new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the analysis of crop structure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posed method of commodity system analysis,as well as the research on the world commodity chain and food regimes.It not only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agricultural sociology research,but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sociology research.
Key words:labor process;laborer production organization;crop structure;social conditions
(責任編輯: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