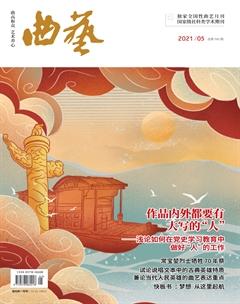白藕脫泥即苦禪
甄齊 張濤

在人類“藝術地掌握世界”的漫長發展過程中,人們不斷地完善、豐富自己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創造出了各種傳遞生活信息、表達思想情感的文化符號和審美符號,并逐漸抽象、演變為較為純粹的審美文本。如人類模仿鳥跡獸形、觀摩自己身處的生活環境而勾勒劈鑿出了各種線條圖形,并從由單純寫實到寫實、寫意具備,創造出了美術。而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文字,特別是漢字可以視作一幅幅簡筆畫。盡管從形貌來說,文字相較于繪畫或者雕塑,形制更為簡單,但文字的精妙組合,如文章、詩歌或者其他藝術作品的文本,卻能讓“芳香、顏色和聲音”在相互應和中具現出“廣大浩漫好像黑夜連著光明”的“象征的森林”。就此而言,文字與繪畫有著天然緊密的契合性,而用藝術的文字描畫一位美術家,則應該是這種契合性的又一次升華。
最近,中國文聯2020年青年文藝創作扶持計劃資助項目,曲藝三書劇《苦禪》即將與受眾正式見面。本作以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著名的書畫家、美術教育家、國畫大師李苦禪先生的生平為基礎,巧妙融合多種曲藝表演形式,再現了李苦禪先生不平凡的一生。
一、創作的原點
“禪”是“禪那”的簡稱,意為“靜慮”“棄惡”等,目的在于通過自我的修行達到自我的解脫,即清除內心的雜念、摒棄諸惡,以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人生美學來看,禪修是一種人生的體驗與自我超越的過程,是要通過戒、定、慧等方法,獲得崇高的人生審美修養。禪心如蓮,苦而復清,這大約是李英杰先生得名“苦禪”的意義。
一位畫家的成長歷程與其生活年代、人生經歷和文化修養息息相關。李苦禪一生飽經戰亂與紛擾,他所經歷的山河板蕩、貧窮饑餓、生死離別和社會變革,是我們難以想象的。但也正是這些人生“禪修”道路上的荊棘叢,強化了他對民族命運的關注和對藝術真理的探索,錘煉出了他昂揚自奮的人格和樸雅凝重的藝術風格。
北宋美術評論家郭若虛有言:“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在中國的美術史中,“人格”與“繪畫”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李苦禪就有“人,必先有人格,然后才有畫格;人無品格,下筆無方”的藝術思想。所以在排布三書劇時,創作者的重心就在于回向溯源,以勾畫李苦禪的人生經歷為重點,凸顯他鍛造人格與藝術品格的歷程。
二、表演的方法
所謂“三書劇”,就是以評書、山東快書、快板書這“三書”為主要表現方法的舞臺劇。
評書的重點在于“評”,是要用一段引人入勝的故事,在夾敘夾議中潤物細無聲地引導受眾的想法和認識。所以本作就以評書為串場和解說的主要方式,利用說書者把控作品的行進節奏,為書情做有效的鋪墊和引導。
用山東快書來著重表現李苦禪,則是創作者基于兩方面考慮的結果。一方面,了解一位藝術家的藝術特征和藝術成就時,往往不可忽視其生活的環境與地域文化因素。荀子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山東地區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發源地之一,獨具特色的齊魯文化養育出了中華文化正統血脈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提倡的忠恕、崇仁、修身、知禮等傳統文化的精髓,在李苦禪的身上和作品中都深有體現。如《易經》是儒家的重要經典,李苦禪對《易經》有獨到的見解,“《易經》之所以三千年來能夠代代相傳而不衰,就是因為《易》學的精神最能體現我們中華民族的個性,它的陰陽之道,剛柔精神,體現了我們民族的一種精神。”李苦禪研究《易》理,并將其與繪畫藝術相通,“畫鷹的時候就要陰陽剛柔兼備,這樣才是一幅好畫。”所以以山東快書來表現李苦禪的藝術形象,就是創作者從文化的根脈出發,要引動藝術共鳴的一種嘗試。
另一方面,曲藝是說唱的藝術,也是方言的藝術。胡適認為:“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于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的人的神情口氣。”方言能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人們所向往的生活,流露出最為淳樸的風情。比如陜西人吃到一碗地道的油潑面時,一句“聊咋咧”能勝過千言萬語的贊美。以山東快書來唱李苦禪,既是為了保證本作的曲藝底色,也能強化受眾對他地域身份的認同,進而讓李苦禪的形象脫出藝術家或者愛國者的單一范疇,獲得更豐富的色彩。
作品中的其他角色多數都有歷史原型,但若一概用相對應的地方曲種表現,則可能會讓作品顯得雜亂無章,無法突出主要人物,分散受眾的注意力。所以《苦禪》的創作者們刪繁就簡,統一用快板書表現其他人。快板書和山東快書同屬韻誦類曲藝表演形式,以快板書和山東快書相呼應,既可以達到藝術上的和諧統一,又可以增強聽覺和視覺的沖擊力,讓整個作品更富有節奏感和韻律美。
典型的曲藝作品需要表演者跳進跳出、在說法中現身。《苦禪》則是在選擇“三書”為主要表現形式以保證作品曲藝底色的同時,在敘事上采用了戲劇的結構和手法,以“一人一角”來選擇性強化人物形象,進而推動情節的發展。
三、故事的脈絡
本作并沒有事無巨細地展現李苦禪的全部人生經歷,而是經過仔細斟酌挑選,在征得李苦禪之子李燕先生的同意后,以5個片段為框架創作。李苦禪早年在北京跟隨徐悲鴻學習西畫,為了湊學費拉過洋車,后來拜入國畫大師齊白石門下學習中國畫。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成為八路軍的地下聯絡員,曾受到日本侵略者嚴刑拷打,險死還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經毛澤東主席批示,李苦禪到中央美院任教,在中國美術教育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時期,他受到冷落和迫害時仍然不忘初心,保持著樂觀向上的精神。重新開始工作后,李苦禪老驥伏櫪,創作了中國大寫意畫歷史上首幅巨作《盛夏圖》,把中國畫的大寫意藝術推向了新高度。這些都是李苦禪人生中標志性的重要事件。作品通過歸納總結,以點帶面,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化的渲染和加工,力求給受眾塑造一個立體的、全面的李苦禪形象。
李苦禪認為:“所謂人格,愛國第一。”曲藝三書劇《苦禪》要著重表現的,就是建筑于這種人格畫品上的工匠精神、民族氣節和愛國情懷。同時,創作的過程也是創作者們滌蕩心靈、打磨技藝的過程。
“出人、出書、走正路”是陳云同志對評彈從業者的殷殷期望。但這七字箴言也應該成為廣大曲藝工作者干事創業的根本遵循。創作一個作品,特別是以李苦禪先生為核心的作品,不能只是雨過地皮濕,有了就行,而是要在深入了解他生平的基礎上,懷著朝圣的心情去創作。落在紙上的每一個字,出了喉嚨的每一段唱,都應該蘊藏對先賢的崇高敬意,變成與歷史的完美和聲。
文藝后來者濯泥自凈的扎實舉動,就是——
白藕脫泥即苦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