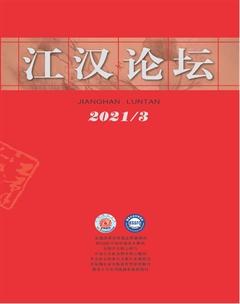緩沖、平衡與利用:租界與中國近代民族報業發展
喻平階 張暢
摘要:租界是外國列強在中國進行殖民擴張活動的基地,也是中國近代屈辱歷史的顯性地理圖標。但在客觀上,租界對中國社會近代化進程亦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如對中國近代民族報業的發展就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中國近現代報業,按報刊創辦者身份,可分為兩大體系——外國人(組織)創辦的在華外報和國人(組織)創辦的民族報業。影響近代民族報業生存與發展的最主要的兩大生態因素是當時的中國政府與外國租界。中國政府、外國租界與中國民族報業三者之間形成了復雜的三角平衡關系。其中,租界處于特殊地位,它是中國近代民族報業的“孵化基地”,是中國民族報業與中國政府之間的“緩沖”或“隔離”地帶,也是平衡近代民族報業與中國政府關系的權重因素。
關鍵詞:中國近現代;民族報業;租界;生態環境
中圖分類號:G219.29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1)03-0111-09
鴉片戰爭后,大批外國人(組織)涌入租界,從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醫療等各類殖民活動。其中,有許多外國人(組織)在租界創辦各種報刊,他們以租界為基地,由沿海、沿江向中國內陸腹地進行擴張,逐步形成品種繁多、數量龐大的在華外報體系。中國人創辦的各類報刊,從行業性質上總稱為中國民族報業。在維新運動之前,國人的辦報活動是零星的,至維新運動時期漸成氣候。1895年至1919年,近代國人辦報活動共有四次高潮時期,即維新變法時期、清末“新政”時期、辛亥革命時期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在華外報不受當時中國政府管理,具有獨特的生態優勢,而近代民族報業則是在中國政府與租界當局(包括各類外國勢力)博弈的夾縫中謀求生存與發展。在中國政府統治地區,中國人創辦的報刊,通稱為國人報刊,在華外報則被敬畏地稱之為“洋人報紙”;在租界地區,或從租界當局的視角,國人報刊則通稱為“華人報刊”。上述稱謂的變化與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即能體現出兩類報刊不同的生存境遇。租界,是構建中國近代民族報業生態環境的重要生態因素之一。
一、近代民族報業生態視角下的租界
(一)報業生態環境與中國近代民族報業生態
生態環境,是影響生物生存與發展的一切外界條件(因素)的總和,它是一個關系系統,由許多生態因素綜合而成。人類社會任何一種事物和自然界的生物一樣,其生存與發展離不開各自的生態環境,報業也是如此。報業生態環境,指的是影響報業生存與發展的一切外界條件(因素)的總和;從宏觀層面來說,報業生態環境大致可分為政治法律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傳媒科技環境及報業內部環境(行業環境)等四大方面。
中國近代民族報業產生、發展于半封建、半殖地時代,政局動蕩,戰亂頻發,外在的政治法律環境既嚴酷又特殊。外國列強勢力范圍從中國沿海、沿江地區逐步擴張到內陸腹地,租界是其對華殖民擴張的基地;租界、租界當局及其背后的列強勢力,是當時能夠抗衡乃至打壓中國政府的主要政治力量。從晚清政府、袁世凱政權、北洋軍閥政府到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其實質都是專制政權,它們鉗制輿論,嚴厲打擊所謂“違禁”的國人報刊與報人,并頒布實施了一系列嚴控民族報業活動的政策或法律。因此,從宏觀層面而言,盡管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經濟市場環境、傳媒科技環境及報業內部環境都對民族報業的生存與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但影響最深刻、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當時的政治法律環境。就中國近代民族報業生態環境而言,決定民族報業生存與發展的是三大政治法律關系:中國政府與民族報業之間的鉗制與抗爭關系、租界與中國民族報業之間的所謂“庇護”與“防范”關系、租界與中國政府之間的抗衡與博弈關系。在這個大三角關系中,租界的地位極為獨特,它是平衡中國政府與民族報業緊張關系的權重因素。因此,在這里我們側重從政治法律環境層面,梳理和審視上述三大政治法律關系,把握中國近代民族報業生態環境的某些側面。
(二)租界成為重要生態因素的“法理”依據
外國列強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建立的租界,最后演變為“國中之國”,取得獨特的強勢地位,是列強在近代對華武力侵略的產物,是列強對華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直接后果。外國列強以武力為后盾,在各自管控的租界中建立權力機構,行使所謂“合法”“有效”的管轄權。在這方面,上海租界最為典型。
上海號稱“萬國租界”,租界面積最大,存續時間也最長,各國列強建立的管理制度與機構也最完備,其他各地的租界治理大多仿照上海租界的制度。同時,上海租界也是中國近代報業中心。因此,上海租界具有典型意義,通過分析列強在上海租界的管治情況,即可大致了解全國各地租界的情形。近代上海市區,按管轄權歸屬不同來劃分,分為租界與華界(中國政府管轄區域)。租界,主要由三大塊構成:公共租界(由英、美等國租界組成)、法國租界、日本租界。三大租界之外,還有其他各國建立的若干小租界。社會管理機構建設相對完備的主要是上述三大租界。在租界地區,外國列強駐上海領事館和領事,根據“領事裁判權”等特權,對本國租界的各類事項擁有最高裁決權和處置權,他們通常依據本國的法律行使權力,對中國政府頒布的法律置之不理。對租界的日常治理,各列強遵循所謂的“三權分立”原則,分別成立了工部局、警務處及會審公廨等機構。上述機構歸屬各國駐上海領事館領導,對各國駐上海領事負責。租界工部局,是租界地區行政管理機構,由工部局董事會領導,工部局董事會還行使租界立法權;工部局董事會,通常由9名董事組成,主要由外國人擔任(俗稱“洋董”)。1928年之后,為了更有效地管理租界地區的華人,同時標榜所謂“華洋共治”,才增選了1—3名華人董事(俗稱“華董”)。租界警務處(局),是治安管理機構,下設若干巡捕房,招聘一定數量的華人巡捕;警務處名義上是工部局的主要執行機構之一,但事實上具有較大的獨立性。租界會審公廨,是租界設立的法院,行使相對獨立的司法審判權。所謂“租界當局”,狹義上通常指租界工部局,廣義上指上述幾種租界管理機構的總稱。
根據上述所謂的“法理”依據及其管理機制,租界中的國人報刊與報人活動,歸屬租界當局管理,中國政府沒有直接管轄權。中國政府要對租界中的國人報刊與報人進行處置,必須獲得租界當局的許可或授權;把國人報刊與報人從租界移交中國政府處置,適用國與國之間的所謂“引渡”條件。
(三)租界為中國民族報業提供了相對適宜的生存環境
近代以來,在中國政府直接統治地區,政局動蕩,治安惡化,經濟蕭條,法治觀念極其淡薄,導致政治法律環境極為嚴酷。相對于中國政府統治地區而言,租界地區有更適宜中國民族報業生存的環境,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相對寬松的政治法律環境。租界當局管理華人報刊活動,通常援引本國的相關法律,遵循近代西方所謂的“新聞自由”理念與傳統,對報刊出版、發行等事務的管理比當時中國政府寬松一些。“在租界內出版報刊,只要按規定辦理注冊登記手續即可,而當時中國政府統治地區普遍實行嚴格的審批制度和檢查制度;報刊在新聞宣傳活動中,只要不構成對租界當局統治威脅的前提下,可以對任何事物加以評論和報道,甚至可以批評租界當局的政策,這與當時的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不準任何批評的態度有很大不同。”①
其二,相對公平的司法程序。租界設有會審公廨,相對獨立地行使司法審判權,遵照相關法定程序審理各種民刑案件和法律糾紛。在租界地區,“報刊新聞宣傳活動若觸犯了相關法律,一般按照司法程序進行審訊,并允許被告人申辯,這同當時的中國封建統治者以言代法,以個人好惡隨意處置報刊和報人的做法大不相同;至于像當時中國政府那樣使用暴力手段,指使軍警、特務搗毀報社,殘殺報人的非法行為,租界當局一般也是不贊成的。”②
其三,相對機動的回旋空間。租界地區,往往由幾個列強的租界組成,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上海租界地區尤其如此。各列強及其租界當局對華殖民侵略的立場是相同的,但在很多具體利益方面存在著矛盾與沖突;在如何管理租界的問題上,他們均從自身利益出發,也存在矛盾與斗爭;同時,各國租界當局與中國政府之間,在很多方面更存在矛盾與沖突。如此,國人報刊與報人,可以在多重矛盾的縫隙中,謀求生存與發展。在租界地區,國人報刊與報人有相對較大的、機動的回旋空間:他們一旦“違禁”或“犯事”,可以從中國政府統治地區轉移到租界地區“避難”;在甲國租界地區“犯事”,可潛入乙國租界躲避;乙國租界政治環境惡化,可轉移到丙國租界“避風”;有時,在租界地區,國人報刊與報人還可得到“洋人朋友”的庇護、幫助或支持。
其四,相對繁榮的市場條件。與中國政府統治地區相比,租界地區工商業相對發達,城市化程度相對更高,市民數量更多,市場相對繁榮。報刊,特別是民營商業報刊和部分知識分子同人報刊,其經營收入的主要方式有兩種——商業廣告與報刊發行。租界地區相對發達的工商業,可為報刊提供較多的穩定的廣告客戶;相對集中、數量龐大的市民群體,是報刊穩定的訂戶和讀者群體,發行較有保障,發行成本也相應降低;租界地區,市民成份復雜、階層多樣分化,各類報刊都可從中尋找、拓展發行市場。
(四)租界是中國近代民族報業的“孵化基地”
近代國人報刊按創辦者身份性質不同大致可分為民營商業報刊、知識分子同人報刊、政治報刊和青年學生社團刊物等四大類。其中,相比較而言,發行量最大、社會影響最大、出版發行時間最長和最穩定的是民營商業報刊。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民營商業報刊,它們的產生與發展都與租界有著深厚的淵源關系,有些報刊甚至是由在華外報轉化、改組而成為國人商業報刊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申報》和《大公報》。
《申報》,1872年4月,由英國商人美查籌資創辦于上海公共租界,屬于在華外報性質;1898年底,美查返回英國,《申報》改組為華洋合資的股份制報刊企業,由美查股份有限公司經營;1907年,華商席子佩、席子眉兄弟二人收購《申報》全部股權,《申報》改組為華資公司經營,至此正式轉型為國人民營商業報刊;1912年10月,報業巨子史量才從席氏兄弟手中收購《申報》全部股權,在史量才的苦心經營下,《申報》從一份地方大報一躍而成為有全國性影響的民營商業大報。在上海租界地區,與《申報》有相似經歷的知名民營商業報刊有《上海新報》(1861)、《字林滬報》(1882)、上海《新聞報》(1893)、《中外日報》(1898)等等。這些報刊,最初都屬于在華外報,是中文商業報刊,它們大多在民國初期轉型、改組為華資經營的民營商業報刊。
《大公報》1902年6月創刊于天津法租界,由法國公使鮑渥及幾名天主教徒集資創辦,主要受法國天主教勢力支持,由中國人英斂之擔任總經理;1916年9月,王郅隆收購《大公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人商業報刊,后因經營不善一度停刊;1926年6月,吳鼎昌、胡政之與張季鸞等人籌資成立新記股份公司接辦《大公報》,《大公報》從此騰飛。他們以天津法租界為基地,先后出版滬版、港版及渝版《大公報》,發展為全國性商業大報。
近代國人商業報刊大多選擇租界作為出版地,長期堅持在租界出版發行。其中,上海租界、天津租界、廣州租界及漢口租界是國人商業報刊比較集中的地方。
上海租界地區,是國人商業報刊最集中的地區。經過幾十年的艱辛創業,上海公共租界山東路望平街,集中了當時上海最重要的國人報刊,如《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神州日報》《民立報》《中外報》《啟民愛國報》《天鐸報》等十多家報館坐落于此。到1912年,望平街發展成為上海地區獨一無二、全國著名的報業街,1936年4月滬版《大公報》也落戶于此。除上海租界外,天津、廣州、漢口等地租界也是重要的國人商業報刊出版地點。在天津租界出版的除《大公報》外,還有《時報》(1886)、《京津泰晤士報》(1894)、《國聞報》(1897)等。廣州租界出版的比較知名的有《述報》(1884)、《廣報》(1886)、《嶺南日報》(1891)等。漢口租界出版的比較知名的有《楚報》(1905)、《商務報》(1909)、《大江白話報》(1911)等。
在中國近代民族報業中具有重要社會影響的還有知識分子同人報刊,這類報刊在創刊時,大多把出版地點選擇在租界。知識分子同人報刊,早期最著名的是陳獨秀1915年9月15日創刊于上海法租界的《新青年》,它拉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序幕,1917年初遷至北京出版,1920年9月因政局惡化重新遷回上海法租界出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及之后,知識分子同人報刊興盛一時,他們所辦的報刊既發表文學作品、學術論文,也大量發表時評、政論等新聞評論,成為當時新聞輿論的主導力量。
在報界比較活躍的知識分子群體主要有以魯迅為“盟主”的“左聯”知識分子群體,以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聞一多等為主要成員(他們大多曾留學歐美)的“新月派”,以郭沫若、成仿吾、田漢、郁達夫、張資平等為主要成員(他們大多曾留學日本)的“創造社”,等等。這些知識分子及其群體,他們主要選擇在上海租界地區出版發行報刊。魯迅及“左聯”文化人士創辦的報刊主要有《語絲》(1928)、《奔流》(1928)、《萌芽》(1930)、《前哨》(1931)、《十字街頭》(1931)、《文學》(1933)、《譯文》(1934)等9種;“新月派”1926年春在北京成立,1927年后把主要活動陣地轉移至上海租界地區,其創辦的主要刊物有《新月》(1928)、《詩刊》(1930)等;“創造社”在上海日租界、公共租界等地先后創辦有《創造》(1922)、《創造周報》(1923)、《中華新報》(1923)、《洪水》(1924)、《創造月刊》(1926)、《文化批判》(1928)等十多種。
各類政治組織或政黨創辦的政治報刊,他們為了發展自己的政治勢力、擴大自已的社會政治影響,必須在當時中國政府統治區域活動,否則其政治功效就大打折扣。因而,許多政治報刊及其報人,就如同政治“候鳥”,一旦租界外政治環境惡化,劫后余生者通常轉入租界“避難”;一旦租界外政局稍穩,則遷出租界活動。這就是近代民族報業發展史上奇特的“政治候鳥”現象。與政治報刊不同,為了應對租界外相對嚴酷的政治法律環境,許多民營商業報刊和知識分子同人報刊,安身于租界,長期在租界地區出版發行,就如同“政治留鳥”;他們依賴租界環境謀求生存與發展,也是一種無奈的生存策略選擇。
無論是“政治留鳥”,還是“政治候鳥”,近代各類國人報刊和報人,大都與租界有著較密切的關系,其生存與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大都依賴租界獨特的生態環境。據不完全統計,1895—1919年,國人先后共創辦各類報刊1390多種,其中在各地租界出版發行的有790多種,占比約57%。③ 因此,客觀上來說,租界是中國近現代民族報業的“孵化基地”,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二、近代中國政府與租界:兩大生態因素的對比分析
(一)近代中國政府高壓下的民族報業
中國近代民族報業經歷了四次發展高潮,但幾乎每一次發展高潮均被中國政府采用政治打壓、法律鉗制等極端手段予以中斷,有時甚至墜入谷底。
甲午戰敗后,清政府內外交困,尋求變法脫困之路。1895年5月2日,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向光緒帝提出“設報達聰”等建議。同時,英國人李提摩太向光緒帝獻《新政策》,提出創辦官私報刊的建議,并推薦英國人傅蘭雅和美國人李佳白“總管報事”。④ 在內外壓力下,1896年7月26日,清廷發布上諭,承認各地報館的合法地位,并“允許報刊據實昌言”。隨后,國人掀起了第一次辦報高潮。尤其是在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各地維新派人士興辦各種報刊,內容以政治宣傳為主;在短短的三個月中,“……國人在全國各地新創辦報刊達90余種,逐步打破了外報在中國新聞輿論界的壟斷地位,使中國人的報刊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⑤ 然而,好景不長,1898年9月26日,慈禧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清廷發布上諭,宣布廢止變法,并廢除官報局。10月9日,清廷又發布上諭,命令各地督撫查禁報館、嚴拿報館主筆。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人士紛紛逃入外國租界避難或經租界逃亡國外,國人第一次辦報高潮戛然中止。
庚子之變后,1901年,清政府為挽救其揺揺欲墜的統治,被迫實施所謂“新政”,有限度地開放“言禁”與“報禁”,重新確認國人辦報權利。國人辦報活動又逐漸活躍起來。尤其是1906年9月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之后,國人辦報活動又進入一個高潮期。據不完全統計,“國人新創辦的報刊,1906年為113種,1907年為110種,1908年為118種,1909年為116種,1910年為136種,1911年為209種。報刊的出版地點有北京、上海、天津、漢口、廣州、南京、廈門、福州、九江、青島等60多個城市和地區,……這些報刊中絕大部分是政治上比較溫和、主張改革的報刊。”⑥ 以國人報刊為陣地,逐漸形成了針對清政府的社會輿論壓力。對此,1908年1月,清廷頒布《大清報律》,確立保證金制度和事先審查制度,試圖運用法律、政治、經濟等手段限制國人辦報活動。但由于當時清政府已風雨飄搖、自身難保,已無法有效地扼止國人報刊的發展勢頭。
武昌起義爆發,各種政治勢力極度活躍,大都創辦報刊進行政治宣傳,擴大影響;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隨即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確規定:人民享有言論、著作、刊行等各項自由權利。同時,由于當時處于新舊政權更迭之際,政府統治相對松弛,因而,國人又掀起新一輪辦報高潮。據統計,武昌起義后半年內,國人新辦的報刊猛增近500種,發行銷售總數量達到4200萬份,這兩個數字都突破了歷史最高紀錄。其中,僅1912年2月以后,到北京民政部門登記要求創辦的報刊就達到90多種。這一時期,被中國新聞史學界稱為民族報業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袁世凱繼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后,采用各種政治手段打壓社會輿論,加強個人專制。尤其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事件”之后,袁世凱頒布總統令,對“亂黨”報刊及各類“違禁”報刊實現全面清剿。“據統計,到1913年底,全國繼續出版的報紙只剩下139家,較之民國元年的500多家銳減300多家,北京的上百家報紙也只剩下20余家。報紙減少三分之二,報人大批被捕被害……”⑦ 1913年是農歷癸丑年,因此中國新聞史上把這一年袁世凱政府對國人報刊和報人的大掃蕩稱之為“癸丑報災”。
“癸丑報災”后,近代民族報業的所謂“黃金時代”也隨即凄慘落幕。在袁世凱政府管轄區域內,國人報刊生存的政治法律環境極其嚴酷。袁世凱為鞏固與加強其專制獨裁統治,以清除報界“敗類雜種”等理由,開始制定與頒行全面管制民族報業的專門法律。1914年4月2日,發布《報紙條例》,“規定創辦報紙實行批準制和保證金制,從政治、經濟兩個方面限制新聞事業的發展。”⑧ 同年12月,袁世凱又頒布《出版法》和《治安警察法》,“對報刊等出版物的申請登記、禁載范圍,規定的更加苛細,對違犯的處罰更加嚴重。同時,該管警察官署認為必要時可隨意處罰,賦予治安察警對報刊等出版物日常處置權……”⑨ 1915—1916年,袁世凱緊鑼密鼓地復辟帝制,對國人報刊活動鉗制更嚴。
袁世凱帝制覆滅后,北洋軍閥政府繼承其專制衣缽,對國人報刊活動的打壓更加殘酷。1917年5月北洋軍閥政府宣布實施全面的郵電檢查,1918年8月設立專門的“新聞檢查局”。此外,北洋軍閥利用其手中掌控的軍政權力,開啟了“槍桿子對付筆桿子”的黑暗、丑惡的歷史。民國初期的許多著名報人(記者)都有慘遭軍閥迫害的經歷,其中,最典型的是邵飄萍和林白水二人的悲慘遭遇。
邵飄萍(1886—1926),被時人譽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報界全才”。1918年10月,邵飄萍在北京創辦大型日報《京報》,因長期在報刊上發文揭露、抨擊軍閥當局的腐敗與暴行,招致軍閥們的忌恨,為此他曾兩次逃亡日本。1926年4月,奉系軍閥張作霖率兵攻入北京,隨即懸賞緝拿邵飄萍。4月24日,張作霖當局設計誘捕了邵飄萍,并查封《京報》。26日,未經審判,邵飄萍即被押赴天橋刑場當眾槍殺。⑩ 邵飄萍遇害不久,另一著名記者林白水也慘遭軍閥毒手。林白水(1874—1926),被時人譽為“蔑視權貴鐵骨錚錚的新聞斗士”。民國初期,林白水有過短暫的從政經歷,1916年8月,他毅然訣別腐敗的官場,在北京創辦《公言報》,1921年3月又在北京創辦《新社會報》。林白水及其報刊因長期發文揭露軍閥、官僚的丑行與暴行,最終招致軍閥當局的報復。1926年8月6日,軍閥張宗昌凌晨下令抓捕林白水,當天4點執行槍決,陳尸天橋刑場。{11}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民族報業出現了一次短暫的繁榮。其間,創辦數量較多、相對活躍的是知識分子同人報刊和青年學生社團刊物。1928年,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后,以“訓政”和“勘亂”等政治名義,鉗制輿論,推行嚴苛的報刊檢查制度,全面實施對民族報業的嚴酷的統制政策。此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在國統區的民族報業處于緩慢、停滯狀態。南京政府在政權初步穩定后,于1933年開始在國統區全面實施新聞檢查制度,先后頒布了《新聞檢查所暫行組織條例》《檢查新聞辦法大綱》《新聞檢查標準》《取締不良小報暫行辦法》等法規,規定各類報刊在每期正式出版之前必須向轄區新聞檢查所呈送“樣報”、“樣本”以供審查,審查合格后方可出版發行。11月13日,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頒布軍令,將全國郵電檢查事宜改歸“中統”管轄。由國民黨特務組織接管郵電檢查,事實上賦予了特務組織介入新聞檢查事務的權力,因為當時的報刊異地采寫、發送新聞文稿,通常通過郵電系統才能完成。
1933年,既是國民黨政府全面推行新聞檢查制度的年份,也是國統區“報案”頻發的一年。“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33年,南京、北平、西安、重慶、鎮江、長沙、杭州等地發生的報案就有17起,被國民黨當局查禁的報刊有15種,被捕的報人多達47人,其中劉煜生、王鰲溪和侯友禮三位知名報人未經審判即遭當局處決。”{12} 當時,面對國民黨政府嚴苛的新聞檢查,國統區的報刊有時只能無奈地以“開天窗”的方式表示無聲的抗議。
縱觀近代民族報業幾十年的滄桑歷程,充分說明當時的中國政府統治地區政治法律嚴酷,民族報業生存與發展的處境十分險惡,但也在某種意義反映了當時國人報刊和報人與歷屆強權政府抗爭的可歌可泣的悲壯歷程,展現出謀求生存與發展的超強韌性。
(二)近代中國政府面對租界的無奈
從政治法律環境來看,近代中國政府與租界,是當時民族報業生態環境中的最重要的兩大生態因素。其中,近代歷屆中國政府因其專制本性,對民族報業的生存與發展,通常居高臨下,采取政治高壓態勢,是一個破壞者角色;相對而言,租界當局則把租界偽善地包裝成“民主與法治之地”,是向中國人展示所謂的“文明與先進”的窗口,在客觀上和特定意義上扮演了中國民族報業的所謂“庇護者”角色。
縱觀中國近代民族報業艱辛創業、慘淡經營的苦難歷程,可以看出,當時中國政府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始終對民族報業采取高壓態勢。由于中國政府的專制強勢,民族報業長期處于弱勢地位。但是,中國政府的強勢與淫威,只能在其直接統治地區施展,對外報與租界內的國人報刊及報人,則明顯有心無力。面對租界內的國人報刊的所謂“違禁”行為,中國政府卻鞭長莫及,手段有限,通常只能采取“禁郵”措施——禁止相關報刊在租界外發行。
1905年,天津法租界出版的《大公報》,在“美國限禁華工新約事件”中,連續刊文抨擊清政府外交軟弱、腐敗無能,清政府惱怒之下以所謂“有礙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郵《大公報》。但讓清政府始料未及的是,禁郵之下,“《大公報》反而身價大漲,印數有增無減。”{13} 1916年1月,袁世凱復辟帝制,自封“中華帝國洪憲皇帝”,敕令全國各地報刊一律改用“洪憲紀年”。《申報》帶頭公開抵制“洪憲紀年”,仍用中華民國紀年,上海租界地區各主要報刊紛紛響應。袁世凱為了殺一儆百,飭令上海警察廳禁郵《申報》等報刊,此舉招致租界當局及外報的公開批評,最后不了了之。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申報》在史量才的親自布署下,多次公開發文抨擊國民黨當局的內外政策,支持青年學生反內戰的抗議運動。12月20日,在史量才的策劃下,上海各家日報(除國民黨《民國日報》外)同時刊載《宋慶齡為鄧演達被害宣言》,矛頭直指蔣介石。“蔣介石龍顏震怒,在威逼利誘無效的情況下,采用對付租界報刊的慣用伎倆,1932年7月下令無限期禁郵《申報》……中外輿論嘩然,上海租界各界紛紛聲援《申報》。在內外壓力之下,禁郵35天之后,蔣介石當局被迫撤銷了禁郵令。”{14} 色厲內荏的蔣介石,為發泄內心的忿恨,采取陰毒的手段,指令軍統特務化裝成土匪武裝打劫,于1934年11月13日下午,在遠離上海租界的杭州郊外,伺機殺害了史量才。
僅從上述幾例“禁郵”事件即可看出,當時歷屆中國政府相較于租界及租界當局而言,長期處于弱勢地位;國人報刊與報人依托租界的“庇護”,面對強悍的中國政府時,有時又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所謂“強勢”;租界及租界當局憑借其獨特的強勢地位,居間調整、平衡民族報業與中國政府的關系,是三者之中的權重因素;三者之間關系復雜微妙,中國近代民族報業則是在兩強之間的夾縫中尋求生存與發展的有限空間。
(三)租界內外兩重天:典型報案對比分析
對近代國人報刊與報人來說,租界內、外的生態環境差別很大,尤其是政治法律環境差別更大,仿佛是兩個不同的世界。1903年,幾乎同時發生了轟動中外的上海租界“蘇報案”與北京“沈藎案”,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蘇報》創刊于1896年6月,創辦人為胡璋,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版發行。1903年5月,章士釗擔任《蘇報》主筆后,以“反清排滿”為辦報宗旨。6月9日,《蘇報》刊文大力推介鄒容的《革命軍》,宣揚反清革命思想。6月29日,《蘇報》摘登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在文中以輕蔑的口吻直呼光緒皇帝為“載湉小丑”,說他和慈禧太后都是“漢族公仇”。
《蘇報》公開大聲吶喊革命,為清政府所不能容忍。6月30日,清政府經與上海領事團多次交涉,訴請上海租界工部局對章太炎、鄒容等7人實行拘捕。當日,章太炎等人被拘捕,鄒容聞訊后于翌日自動投案,“蘇報案”由此引發。清政府向租界當局承諾,以滬寧鐵路筑路權為交換條件,要求將章、鄒二人“引渡”給清廷審判,但遭租界當局拒絕。7月15日,上海租界會審公廨開始會審“蘇報案”,一場以清政府為原告,以章、鄒等為被告的特殊審訊開始。審訊初期,清政府要求判處章、鄒死刑,又遭拒絕。1903年12月中旬,租界會審公廨判處章、鄒二人永久監禁,其余人開釋。這一判決遭到國內外輿論的強烈反對,租界當局不得不于1904年5月21日重新開庭做出判決:章太炎監禁3年,鄒容監禁2年,《蘇報》停刊。
慈禧太后得知章、鄒等人被上海租界當局拘捕后,親自出馬,在頤和園宴請各國公使夫人,并贈送瓷器、手鐲、珍玩等貴重禮品。宴后,慈禧不顧“太后之尊”拜請各位夫人游說各公使,同意把章、鄒二人“引渡”給清政府。但西方人對慈禧太后幕后支持義和團運動始終難以釋懷,結果各位太太禮品照收,而游說之事卻遭拒絕。{15}
在“蘇報案”中,清政府在中國領土上同自己的臣民打官司,卻要由租界當局來審判,在國際上顏面掃地。而章、鄒在審訊過程中慷慨陳詞,把法庭變成了宣傳革命的講壇。在每次審訊完畢押解回巡捕房的路上,章太炎都高聲吟唱“風吹枷鎖滿城香,街市爭看員外郎”等詩句{16},繼續公開宣傳反清革命思想。
上海租界審訊“蘇報案”的同時,北京發生了“沈藎案”。沈藎是湖南人,是一位痛恨列強侵略、凌辱中國的愛國志士,1903年他在北京一家小報《時訊報》擔任新聞記者,他探得中俄密約草稿后將其發表在天津英文報紙上,引發全國各階層和留日學生反對密約的斗爭。7月19日,沈藎被清政府逮捕,隨后被判處斬立決。《時訊報》的工作人員聞訊后紛紛逃入天津法租界避難,《時訊報》隨即被查封停刊。當時,適逢慈禧萬壽慶典,不宜公開殺人,遂改判“立斃杖下”。31日,沈藎被獄吏杖打二百余下,“血肉飛裂,猶未致死”,最后用繩“勒之而死”。“……探聞刑部司官,自杖斃沈藎后,托故告假者頗多。皆以杖斃之慘,不忍過其地。出而述其始末,照錄于后,以補各報之缺。當杖斃時,先派壯差二名,打以八十大板,骨已如粉,始終未出一聲。及至打畢,堂司均以為斃矣。不意沈于階下發聲曰:何以還不死,速用繩絞我。堂司無法,如其言,兩絞而死。”{17} 沈藎慘案傳出后,中外震驚。
對比兩案,不難看出:沈藎的行為出于至誠的愛國精神,言行絕對沒有章太炎、鄒容等人那般激進,但最終的結局卻完全不同。原因很簡單,僅僅是因為沈藎在租界外落入了殘暴的清政府的魔爪之中。與此同時,清政府對更為痛恨的“蘇報案”卻無法施展淫威,只得徒喚奈何,這僅僅是因為報案發生在清政府勢力鞭長難及的上海租界。
(四)歷史悖論:租界收回后民族報業生態環境的巨變
中國政府收回租界的外交斗爭始于北伐戰爭期間。1927年1月初,北伐軍攻取長江中下游,廣州國民政府遷至武漢,隨即接管漢口、九江英租界。經過艱苦的外交斗爭,英國政府被迫讓步,放棄漢口、九江租界,退而確保地位更重要的上海租界。2月20日,國民政府正式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管轄權。1930年代初期,南京國民政府發起對外簽訂“平等新約”的外交活動,經過艱難的外交努力,先后收回廈門英租界、威海衛英租界及天津比利時租界,但重中之重的上海各國租界的地位沒有動搖,各國行使租界管轄權的基礎——“領事裁判權”也沒能廢除。直到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東方主戰場“中國戰區”地位上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也逐步上升。在此背景下,1943年1月11日,為了加強盟國之間的“友誼與團結”,中美簽訂了“中美平等新約”。次日,中英簽訂“中英平等新約”。新約規定:美、英兩國宣布廢除在華的“領事裁判權”及其它特權,兩國在各地租界的管轄權統一歸還中國政府。在美、英兩國帶動下,其他有關國家也相繼與中國政府簽定了新約。1945年二戰結束后,中國政府依法收回了各地所有租界的管轄權;其中,日、德等戰敗國,無條件歸還在華租界或勢力范圍。
租界收回后,原有的相對平衡穩定的大三角結構關系崩潰,民族報業失去了租界這一“緩沖”地帶和“回旋”空間,直接暴露在國民黨政府的“槍口與棍棒”之下,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特別是1946年下半年后,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以“勘亂”和“戰時管制”等政治、法律名義,“國民黨當局動用大批憲兵、特務,搗毀報館,捕殺報人,在新聞界實行血腥的白色恐怖。……據1947年4月22日重慶《世界日報》報道:僅在3、4月間,各地被當局以各種理由查禁的報刊,至少在100種以上。……1947年6月l日,僅重慶一地被捕的報業人員就達30多人。……素有中國報業中心之稱的上海,遭國民黨當局迫害與摧殘的報刊為數最多。1947年5月24日,上海《文匯報》、《新民報》和《聯合日報晚刊》三家報紙在同一天被國民黨查封。”{18} 在這場民族報業的空前浩劫中,原先主要依托租界生存的兩份老報大報——《申報》與《大公報》也未能幸免于難。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當局以接收敵偽財產的名義,霸占了《申報》與“申報大樓”。1946年3月,國民黨改組《申報》,官方股權達到51%以上,納入“國民黨黨報系列”,終于實現了多年的圖謀。《申報》喪失了民營商業報刊的性質與地位,從此一蹶不振,名存實亡。{19} 1947—1948年,在國民黨當局的高壓下,《大公報》天津版、上海版、重慶版等先后被迫自動停刊,只有香港版《大公報》一脈尚存。
三、利己本位:外國租界的“雙重性”
(一)租界是列強對華文化殖民擴張的基地
各國列強以武力為后盾、以不平等條約為法律利器在各通商口岸建立租界后,各國宗教組織及其傳教士往往是最先進入租界開展文化殖民活動的急先鋒。他們在華進行文化殖民活動的基本目的:向中國人傳播西方宗教,宣傳西方近代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展示西方文化的“優越性”,試圖用西方文化取代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各國教會組織及其傳教士在華的宗教文化殖民方式主要有創辦中文報刊、興建教堂、創辦教會學校等。其中,創辦中文宗教報刊,是最先采用的主要方式。事實上,各地租界創刊的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往往也是宗教報刊。各國宗教組織及其傳教士在租界創辦的中文宗教報刊,是近代在華外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僅據1890年美國傳教士法罕在新教傳教士年會上宣布的不完全統計數據,自1860年至1890年,基督教系統在華創辦的中文宗教報刊已達76種。1895年,英國人李提摩太在天津《時報》上發文,公布了一組在華外報的統計數據:1815年至1894年,外國人(組織)在華先后出版各類中文報刊共有123種,主要分布于上海、廣州、漢口、天津、廈門、福州、九江等租界地區,其中,傳教士或教會組織創辦的有73種,約占60%。”{20}
各國教會組織及其傳教士,以租界為基地,以中文宗教報刊為主要宣傳陣地,憑借“洋教”“洋人”的特殊身紛與特權,大肆在華進行宗教、文化滲透與擴張,招攬華人信徒。國人中的一些不良分子,也紛紛改信“洋教”,他們倚仗“洋教”勢力欺壓同胞、魚肉鄉鄰。近代中國社會“教案”頻發,就與各國教會組織及其傳教士在華猖狂的文化殖民活動密切相關。
(二)租界對待華人報刊的功利主義態度
外國列強在中國各通商口岸開辟租界,并設立工部局等機構管理租界各項事務,其基本立場是維護本國及其僑民在華特權與殖民利益,確保本國利益優先與本國利益最大化。租界是列強在華進行殖民侵略的基地,租界當局是其維護在華特權與利益、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租界當局管理租界事務,也是遵循上述基本立場,因此,它們對待華人報刊與報人態度是典型的功利主義態度。
外國列強及其租界當局很善于利用自己的強勢地位,有意無意地“庇護”中國政府的“反對派報刊”,以此向中國政府示威或施壓。租界當局對中國政府不滿時,或者想從中國政府手中攫取更多利益時,常常縱容、鼓動租界的報刊向中國政府“發難”。例如,1900年前后,京、津及山東等地的義和團組織在慈禧當局的支持下圍攻東郊民巷使館區和外國教堂時,上海租界當局縱容租界的報刊抨擊慈禧當局,形成了統一的譴責慈禧的“新聞輿論”。當時,《申報》發表了幾篇評論,立場站在慈禧及義和團一邊,租界當局對此極度不滿。從1900—1902年,租界當局鼓動租界報刊圍攻《申報》長達三年之久,導致《申報》發行量驟減,元氣大傷。{21} 又如,袁世凱復辟帝制時期,為了逼迫袁世凱出賣更多的利益,上海租界當局有意保護“反袁報刊”,以此向袁政府施壓;1916年1月,袁世凱正式改元登基,租界當局有意縱容租界報刊拒用“洪憲紀元”,搞得這位“皇帝”進退失據、狼狽不堪。{22}
租界當局往往在中國政府與華人報刊之間玩弄“平衡術”,一方借用租界華人報刊給中國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又打壓反對中國政府的進步報刊,向雙方宣示自己在租界高于一切的統治權威,以維系租界的“長治久安”。此外,租界當局一般不輕易滿足中國政府鎮壓租界內“反政府報刊”的要求,這一方面是為了顯示“治外法權”的優越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向中國政府及民眾顯示其所謂的“文明與進步”。
租界當局管理華人報刊活動,表面上標榜所謂“言論出版自由”,實質上以自身利益為標準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對不觸犯自身權利的華人報刊與報人,或有利于己的華人報刊與報人,則任其“自由活動”;對觸犯其權利的華人報刊與報人,則以限制“激進主義報刊活動”的名義,采取嚴控、查禁等措施予以打壓。五四運動時期,上海租界當局對華人報刊及報人所采取的措施,就充分暴露了其功利主義本質。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各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列強及各地租界當局對此極為忌憚和恐懼。當時,上海租界當局釆取各種嚴厲措施,打壓租界的所謂“激進報刊”。公共租界工部局把重點翻譯檢查的中文報刊從24種急增至40多種,對“違禁犯事”的報刊一律予以查封;一旦發現新的報刊,警務處立即派人偵查該報的政治背景,以便把“激進報刊”消滅在萌芽狀態。上海法租界也釆取應急措施,于1919年6月緊急出臺《上海法租界發行、印刷、出版品定章》,規定各種出版物“未奉法總領事允許,不能在法租界內出版發行”,嚴格實施出版許可制,以此防堵“激進報刊”。
(三)租界“新聞自由”的本質是“偽自由”
租界的建設與管理,本質是維護列強在華殖民利益與特權。租界當局依據“領事裁判權”等特權行使租界管轄權,在管理租界的過程中,它們往往把租界包裝為“自由與法治之地”,設計成向中國政府及華人展示所謂西方“文明與進步”的窗口,目的在于宣傳西方文明的“先進”與“優越”,讓中國政府及華人“口服心服”,進而認可、接受它們的殖民統治,以減少在華進行殖民擴張的阻力。
租界地區是一個獨特的社會,對華人報刊與報人來說,也是一個獨特的生態環境。租界當局主觀上把租界標榜為“自由與法治之地”,它在客觀上、在一定程度上也為中國近代民族報業提供了相對“自由”“寬松”的生存與發展環境,尤其是與中國政府統治地區相比,這方面體現得較為明顯。租界當局以本國堅船利炮為后盾,憑借在華攫取的特權,對中國政府與民族報業而言,租界處于強勢地位。租界華人報刊與報人依托強勢的租界當局的所謂“庇護”,比較“自由”地從事新聞與宣傳活動,激發或引導社會輿論;也能比較“自由”地發表時評與政論,議論國事,批評乃至抨擊當時的中國政府。表面上看,這是比較理想的“新聞自由”狀態,然在實質上這是一種脆弱的“偽自由”。
其一,這種所謂的“新聞自由”,是在外國列強及其殖民統治工具(租界當局)“庇護”下的“自由”。租界當局是以武力為后盾的對華殖民統治工具,其根本目的是維護和保障本國及其僑民在華特權和殖民利益,讓華人報刊與華人在其管轄區域“自由”活動,只是一種暫時的對華進行文化殖民活動的策略,是一種權宜之計。租界當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選擇、判斷標準,既可以根據自身需要給予華人報刊與報人“自由活動空間”,也可以根據形勢變化隨時限制乃至剝奪其“自由活動權利”。
其二,租界當局對待華人報刊與華人,采取的是功利主義態度。它們把華人報刊與報人作為一種輿論工具或政治工具,并以此作為籌碼,與中國政府進行博弈,向中國政府施壓,以攫取更多的殖民權利;一旦華人報刊與報人的活動威脅到它們的特權與殖民利益,它們就采取各種措施限制、打壓華人報刊與報人的活動自由。
其三,在租界地區,“洋人”是享有特權的上等人,在華外報也處于優越地位;華人是次等公民,華人報刊也居于次等地位。租界當局處理租界各項事務時,優先考慮、保障的是“洋人”的權利——這是其管理租界的基本立場和基本原則。華人報刊為了在租界外活動“方便”,往往借用“洋人”或“洋商”的旗號——這便是中國近代史上常見的“洋旗報”現象。當時,這種“掛洋旗”的現象在各行各業都很盛行,主要目的在于應對租界外的險惡環境。“洋人”或“洋商”掛名后,一般在華人報社擁有一定比例的“干股”,享有“分紅”的權利。二者在如此“合作”中,有時難免產生矛盾與糾紛,但在處理這種民事糾紛時,租界當局通常偏袒“洋人”或“洋商”。{23} 在租界地區,華人根本無法享有與“洋人”平等的權利,在報刊活動中也是如此。有等差的“新聞自由”權利,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自由”。
注釋:
①② 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復旦大學出版1996年版,第570、570頁。
③ 《中國近代報刊史資料》,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80年編印,第221頁。
④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37頁。
⑤⑥⑦{18}{20}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7、96、119、226、52頁。
⑧⑨ 魏永征:《中國新聞傳播法綱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頁。
⑩{11} 鄧利平等:《中外名記者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5頁。
{12}{14} 傅國涌:《百年中國言論史的一種讀法》,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173頁。
{13}{17} 方漢奇等:《大公報百年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頁。
{15} 季小云:《中國百年報史秘聞》,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頁。
{16} 李一道:《中國報人春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頁。
{19} 曾虛白:《中國新聞史》,臺灣三民書店1984年版,第462頁。
{21} 陳玉申:《晚清報業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頁。
{22}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上海史研究》,學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頁。
{23} 吳思:《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游戲》,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頁。
作者簡介:喻平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湖北武漢,430073;張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湖北武漢,430073。
(責任編輯 ?張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