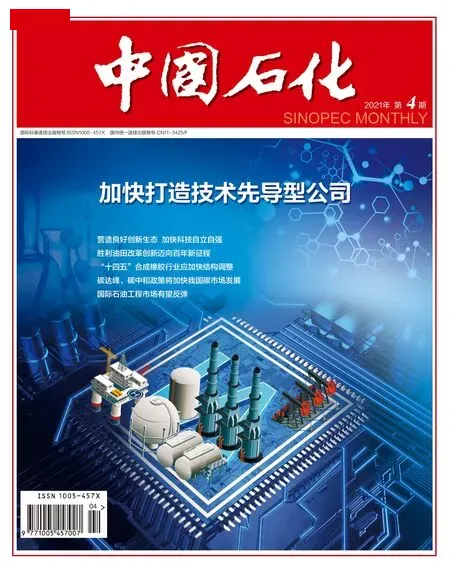沙特阿美為何積極綁定中國能源市場
□ 陸如泉

沙特阿美公司看好中國市場。圖為該公司海上油氣開采平臺。李曉東 供圖
3月21日,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舉辦的“2021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SaudiAramco)公司CEO阿敏·納瑟爾在視頻連線時表示:“確保中國能源需求的持久安全是我們最為優先的目標,不僅僅未來5年是這樣,未來50年甚至更久都是這樣。”
納瑟爾的這一表態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反響,路透社等媒體和一些能源咨詢機構紛紛報道和分析,國內石油界人士也在熱議。這應該是沙特阿美這一對華最大的石油出口商之一首次進行如此“給力”的表態。這肯定不是納瑟爾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沙特高層的戰略決策。要知道,沙特阿美CEO歷來在沙特政經兩界的地位非常高,是“準石油部長”身份,該公司一把手往往在下一任期就成為沙特的能源與礦產部長。納瑟爾的前兩任,阿里·納伊米和默罕默德·法利赫,均是如此。順便說一句,對華另一大石油出口商是俄羅斯石油公司,近年來,沙特與俄羅斯交替成為我國最大的石油出口國。
供求關系決定沙特綁定中國市場
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全球石油市場供求關系決定了沙特必須綁定中國市場。本世紀以來,沙特對外石油輸出主要有三大市場:東北亞(份額最大是中國)、歐洲和美國。最近10年,隨著印度經濟的快速發展,沙特也愈加重視對印度的出口。當前,歐洲的石油消費在明顯下降,印度將來從沙特進口的石油量有較大不確定性,而且印度2020年自美國的進口量也在暴增。美國自沙特的進口量在下滑,而且兩國在石油出口上的競爭越來越強。
即便在中國市場,沙特也面臨俄羅斯、美國的強烈競爭。俄羅斯在2016~2018年擠掉沙特成為中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國,2019、2020沙特重新成為對華最大出口國,2020年美國首次進入中國前十大進口來源國。明眼人一看便知,中國是未來沙特出口石油最大的希望所在,了解這些,就知道納瑟爾的上述表態是意料之舉。當下,全球石油的供需是典型“買方市場”,沙特的石油不賣給中國,還能賣給誰?
基于市場行為的現實考慮
隨著美國實現“能源獨立”,石油政治屬性顯著下降,已越來越回歸其大宗商品屬性,沙特阿美如此決定是基于市場行為的現實考慮。二戰以來,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沙特成為全球主要的石油生產國,對美國的石油出口一直是沙特的優先考慮和戰略依賴。由此形成了“石油換安全”的美沙盟友關系基石,即美國承諾保護沙特的王室和國家安全,而沙特為美國這一長期以來的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提供充足而廉價的石油。1991年,美國從沙特進口的原油達到8515萬噸(170.3萬桶/日)的峰值,約占美國當年進口總量的1/3。而且美沙石油交易的幣種為美元,并將掛靠美元的交易方式推廣至整個歐佩克,由此逐步形成了“石油美元”的美元霸權體系,成為美國全球霸權的關鍵支撐。
最近10年,通過“頁巖革命”,美國重新回歸全球第一大油氣生產國,已成為天然氣及LNG的凈出口國,雖然石油進口量依然位居全球第二,但呈現“大進大出”的特點,即將成為石油凈出口國。美國的能源獨立徹底改變了全球能源的供需格局和能源地緣政治版圖,大大降低了油氣的政治屬性。在石油逐步回歸其商品屬性的情況下,石油于沙特而言,不再是強大的“武器”,也不完全是“石油權力”的象征,而是基于供需關系的一種商品。在未來較長一個時期中國持續保持全球第一大石油進口國的情況下,沙特阿美做出“優先保障中國的能源安全”的表態,既是有意獲得中國好感的“講政治”之舉,也是基于市場行為的現實考慮。
沙特認識到印度并不可靠
沙特阿美此舉等于宣布,作為中國進口油氣最大競爭對手的印度,盡管已成為全球矚目的經濟體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但并非沙特優先考慮的市場,印度將“靠邊站”。雖然沙特有意將印度打造成第二個中國市場,但近期印度石油部長的一番抱怨和美印在能源合作上的強化,使得沙特認識到,印度并不是一個可靠的合作伙伴。
今年3月初舉行的劍橋能源周(CERA WEEK)會議上,印度石油部長Dharmendra Pradhan對近期油價上漲和沙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說“歐佩克的政策很讓人費解,印度并不希望油價出現大幅波動,油價的上漲意味著印度要付出更高的‘亞洲溢價’”。
不言自明,印度石油部長的矛頭直指沙特,因為沙特自愿減產的100萬桶/日是推高這一輪油價的重要因素。目前,印度的石油對外依存度為84%,其中60%的進口量來自中東,第一大進口國是伊拉克而非沙特。這增加了印沙兩國的芥蒂。再者,在以中國為假想敵的情況下,印度開始肆無忌憚地抱美國的大腿,美印關系變得超乎尋常的密切。在能源合作領域,印度持續加大從美國進口油氣的力度,似乎想取代沙特在印度進口市場格局中的地位,而這更加劇了印沙之間的尷尬與不和。路透社的數據顯示,印度今年2月從美國的進口量同比增長了48%,達到創紀錄的54.5萬桶/日,占該月進口總量的14%;相比之下,2月從沙特的進口量較1月下降42%,為10年來最低,只有44.5萬桶/日。
不會引發美國的不安
沙特阿美此舉應該不會引發美國的不安。歐美的能源決策者基本不會拿中國的能源安全說事,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能源安全敏感但不脆弱。納瑟爾的上述表態應該不會引發美國的不安或者不滿。一是縱觀本世紀以來歷次石油危機和油價劇烈波動事件中,美國和歐洲諸大國基本沒有拿能源安全說事,也基本沒有視中國這樣的油氣消費大國為威脅,更沒有阻擾中國政府為保障能源安全而采取的各種舉措。因此,多年來,所謂“馬六甲困境”等話題,更多是在國內熱議和炒作,美歐并沒有就此大做文章。二是美歐一直以來并沒有刻意阻撓中國企業在海外找油找氣,最為典型的是2008年伊拉克戰后的大型油田開發招標,斬獲最多的是中國石油公司而不是美國公司。而且,客觀上講,美國在伊拉克戰后的駐軍和秩序維護,為全球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的投資與運營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這實際上是美國為全球提供的公共產品。三是特朗普執政以來,中美逐漸成為戰略競爭對手,在科技等諸多領域開始脫軌,但出乎意料的是,能源領域并未脫鉤,而且有加大合作之勢,這說明美國并沒有在能源安全問題上向中國發難。
最后一點,也是最重要的是,美歐認為中國已經把保障能源安全的主動權牢牢握在自己手中,除了有國內2億噸石油和1800億立方米左右天然氣產量作為基礎,中國還通過構建中俄、中亞、中緬等油氣管道,形成了多元化的能源供應體系。可以說,中國的油氣對外依存度雖居高不下,但該問題敏感卻不脆弱。納瑟爾的此番表態,應該不會讓美國和歐洲感到不安。
背后還有伊朗的因素
納瑟爾此番大膽的表態,其背后還有伊朗的因素。沙特和伊朗是“千年的冤家”。如果伊核談判下步取得突破,美國解除或放松對伊朗的石油制裁,那么中國的石油進口還會多出伊朗這個選擇。考慮到這些商業情況和地緣形勢,沙特此時必須傳遞信心、釋放信號,鞏固中國市場份額。當然,沙特這么說也有它的底氣,因為沙特這幾年與中國東部沿海諸多大型煉廠成功綁定,有信心把基本的出口份額維持住。
有利于推動我國石油產業盡快形成雙循環發展格局
沙特阿美鎖定中國市場,有利于推動我國石油產業盡快形成雙循環發展格局,并可能將石油人民幣向前推進一大步。石油產業極具全球化特征,是經濟全球化的代表,我國石油產業已充分融入全球。截至目前,我國石油產業鏈的主體依然在國內,無論是資產人員還是供應鏈等,4/5左右的份額在國內;與此同時,中國能源企業與沙特、俄羅斯等全球重點資源國的合作在加強,特別是全球油氣貿易量不斷上升。一方面,沙特的這番表態如果在未來得到有效實施,則將助力我國石油產業早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另一方面,沙特未來50年錨定中國市場,意味著實現以人民幣為結算貨幣的石油人民幣金融體系將變得可能。這將實質性提升人民幣國際化使用的程度。當然,這也意味著石油美元的日漸式微,并與美國的根本利益發生碰撞,美國勢必全方位進行狙擊與遏制。
總而言之,未來50年,中沙石油合作的程度將明顯高于美沙。美沙石油換安全的時代將一去不返。未來,沙特將在國家安全上繼續依賴美國的庇護,但在實現石油收入和經濟安全上則更加倚重中國。這種變化將是對二戰以來沙特與美國“石油換安全”雙邊關系基石的重大調整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