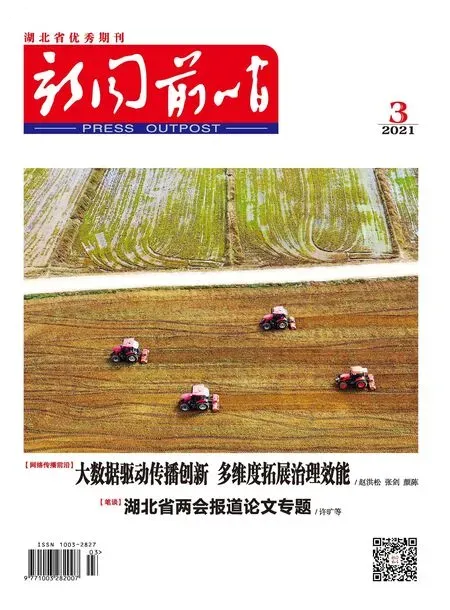媒介奇觀下人物符號傳播功能研究
——以丁真為例
◎沈福林
媒介奇觀是由美國媒體學者道格拉斯·凱爾納提出的,他將那些能體現當代社會基本價值觀、 引導個人適應現代生活方式, 并將當代社會中的沖突和其解決方式戲劇化的媒體文化現象定義為“媒介奇觀”。 凱爾納關于“奇觀”的概念非常接近我們所說的流行文化現象。
一、媒介奇觀下人物符號的建構
社交媒體環境下,媒介奇觀化已經成為典型的現象,在此基礎上,短視頻的出現,更是將我們帶入一個短平快的消費時代。 以碎片化迎合人們需求的短視頻日益風靡,制造和提供了一系列的視覺奇觀,將現實生活中的某些現象變成了具有圍觀效應的視覺奇觀。 藝術家安迪·沃霍爾曾提出過15 分鐘定律的預言,他認為每個人都可能在15 分鐘內出名。
然而,到了短視頻時代,丁真只用了10 秒,就創造出了屬于他的媒介奇觀。 2020 年11 月11 日,丁真偶然被攝影師胡波拍攝了一則短視頻,視頻中丁真有著黝黑的皮膚,略顯蓬亂的頭發,臉上掛著純真干凈的笑容,一雙眼睛清澈明亮, 就是這樣一則視頻使得他成為火遍全網、 走出國門的“新晉頂流”,甚至入選了2020 十大旅游事件。 截止到2021年2 月22 日,其抖音賬號擁有粉絲760 萬左右,點贊量高達4350 多萬,并持續呈上升趨勢,相關話題也是頻頻登上微博熱搜。
凱爾納認為媒介奇觀通過一系列視覺符號向觀眾展示現實生活中罕見的影像,因此,媒介化符號是構建任何一個景觀的重要組成元素。 而丁真在這種運用視頻媒介形式搭建的媒介奇觀中,扮演的正是“符號”的作用,讓人們將目光從視頻中眼神明亮的少年延伸到了視頻外那個沒有讀過太多書、在家放牛、最大愿望是想成為“賽馬王子”的普通丁真身上。他家庭貧困,讀書不多,漢語不是很好,但堅定的眼神里閃爍著野性,笑起來純真無邪,最大的愛好是賽馬,有一匹叫“珍珠”的小馬,是用他爸爸最愛的馬換來的,這一切都符合人們頭腦中對“少年丁真”的想象,也正是這樣虛與實的融合,讓人們頭腦中構筑起關于“丁真”的符號。 提起丁真,人們想到的都是“理塘丁真”、“康巴漢子”、“四川甘孜”,由此可以說,媒介奇觀下的丁真已經成為了一種人物符號,連接起人們對 “干凈清澈的少年”、“天空之城理塘”、“雪山之下的小鎮”、“一望無際的草原”、“健碩康巴漢子” 的無限想象。

二、人物符號化呈現
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用來解釋并傳達意義,社交媒體的傳播互動,都是由符號互動組成的。 丁真的走紅,就是人們對于身體符號象征價值的追求,進而引發的互動。這首先體現在對人物外在形象的追求。丁真皮膚黝黑,眼睛清澈明亮,臉頰上有著藏人常見的高原紅。 顯然,這與常見的大眾審美有著強烈的反差感,但也正是因為這種反差,使得他似乎“不留俗”,引發人們的符號追求,這種追求源于人們對無濾鏡以及純真臉龐稀缺性的追求, 屬于對身體符號的消費。其次體現在對人物精神世界的追求,生活在理塘的大男孩,他的快樂也許就到“賽馬王子”為止;而生活在市井煙火氣中的大多數人,對于快樂的追求可能已經無法言盡,正是由于內心世界的兩級鴻溝, 引發了人們的符號象征價值追求,這種追求是對純粹內心世界的追求,屬于精神的追求。最后,這種對人物符號的追求,體現在與人物有關的表象符號上。 伴隨著丁真的走紅,人們除了關注丁真本人以外,開始延伸到對其小馬、家人、家鄉的關注上。由此,也引發了對其家鄉理塘—“平坦如銅鏡般的草壩”、“天空之城”的關注。
可以說,丁真以符號化的人物形象,形成了對與有關人物的集體記憶。 在凱爾納看來,“奇觀” 還帶有鮮明的主體性,有明確的主體操控和表現,即它由媒體打造,為背后的各種政治勢力或商業權力所操控。當然,“丁真”的走紅具有明顯的奇觀特征,其人物符號的呈現也離不開媒體、資本、政治的加持,這也是他區別于其他網紅的地方。丁真在抖音視頻走紅之后,各家媒體爭相報道,甚至一度出現“搶丁真”的現象,這使其人物形象逐漸豐滿。 隨后,理塘縣政府迅速介入丁真的話題討論中,讓丁真進入縣政府工作,成為城市形象大使,就連外交部發言人也連發三條推特支持丁真,媒介議程設置助力,官方發聲支持等,無疑都強化了人物符號的呈現。
三、符號化個體的傳播功能
丁真視頻中的“干凈”、“靦腆”、“野性”等個人特征建構出其符號化的身份,觀眾通過與視頻中建構元素的共鳴,使符號化具有了傳播功能, 其傳播功能從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來:
(一)信息傳遞功能
人物符號是人類最古老的傳播方式, 到了網絡時代,更是直觀的表現出了信息傳遞功能。 丁真走紅之后就成為了理塘縣旅游大使,其網絡賬號的標識也是“理塘丁真”,可以說“丁真”這一符號為當地旅游貢獻了巨大力量,使得理塘、甘孜、四川的搜索量都大大增加,攜程數據顯示,截止12 月4 日,丁真帶動“理塘”、“甘孜”搜索增幅高達1400%和760%。更多的人,因為“丁真”開始了解四川理塘、新疆昭蘇這樣的小眾旅游地。
(二)經濟功能
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認為大眾傳媒具有社會地位賦予功能, 即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加強對社會上的某一類人或者某一種現象進行廣泛報道,使之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進而獲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會地位。可以說,大眾傳媒賦予了丁真更高的社會地位,而“丁真”這一符號的產生,帶動了一系列經濟的發展。“丁真”作為人物符號,其實際經濟意義就在于,丁真的家鄉曾經屬于貧困地區,如今,乘著脫貧攻堅、全面小康的東風,加上有“丁真”這一符號的存在,這里已經成為“網紅城市”,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前來打卡旅游,由此也吸引人們開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偏遠地區, 把更多的注意力聚焦到貧困地區。無論是以美景吸引游客、還是以直播打通特色農產品銷路,“丁真” 作為人物符號的經濟價值都是不可否認的。
(三)價值引領功能
丁真走紅之后成為四川形象代言人, 并拍攝了紀錄片《丁真的世界》,從丁真的視角看“丁真的世界”,講述康巴文。一方面展示了我國康巴地區的風土人情,讓更多的人看些隱匿在喧囂之外的康巴文化, 讓人們看到藏區人民的真實生活,感受到藏區人民的淳樸善良,更好的堅定了我們的文化自信,面對突然而來的爆紅,他沒有急著出道,沒有急著流量變現,而是以此為基礎,開始認真讀書,學習漢語,成為摒棄浮躁主動學習的正面典型, 讓我們意識到在實現個人價值的基礎上,努力實現社會價值,才是流量需要真正去追逐的目標。
另一方面,繼李子柒之后,丁真打開了又一扇為外國人美好中國的“窗口”,像人們展示了藏族文化,使得中國的形象更加鮮活,在潛移默化中傳播了中華文化,實現了“文化輸出”,讓世界感受到了中國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四)“投射”功能
“投射”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認為“他認為投射是從別人身上發現自己的情感、 想法或愿望的心理保護機制”。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把自身的期待轉移到另一個物體上去,滿足自己內心的傾向。“丁真”的出現,投射的無疑是人們對逃離世俗壓力的渴望,是人們對 “純真烏托邦“的想象。 人們最初喜歡丁真,源于他的干凈。 粉絲喜歡丁真,但卻不同“飯圈文化”,人們似乎都在有意識的去保護這份純真,共同呼吁讓他自由自在一些,不要過度營銷他,不要讓他過多營業,讓他好好念書;保護他的夢想,他的夢想只是自己的小馬能跑第一,不要給他強加別的俗世的思想,讓他安安靜靜放牛,念書,賽馬,永遠是這個干凈的少年。 這些愿望與呼喊,正是現在大多數人缺少的,與其說人們喜歡丁真,不如說是喜歡那個那個象征著自由少年的“丁真”。
結語
“丁真”作為一個在媒體 、資本、政治助力下脫穎而出的“網紅”代表,是當代媒介奇觀中的一個標志性符號,反映出消費時代下人們對人物符號的象征價值的追求 。 但同時,我們在看到它所帶來的傳播功能的同時,也要警惕人物符號背后泛娛樂化。泛娛樂化的文化氛圍下,顯露出強大的消費意味,必將產生理性與非理性的價值沖突,破壞社會的秩序與規則,需要我們警惕、反思和啟發,管控其過度娛樂化的發展,正如凱爾納所言,大眾在面對這種意識形態的灌輸時,并非沒有抵抗力,而是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堅持主體思考能動性, 增強文化自覺, 共同守護我們的精神家園,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生產導向,堅持追求真善美,沖破以取樂為目的的文化產品生產模式, 不在泛娛樂化中迷失自我,在娛樂狂歡中發揮個體社會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