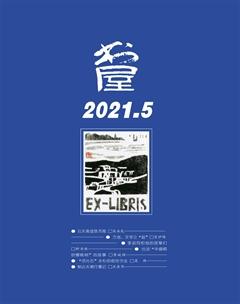梁濟先生的趨新守舊
吳敏文
梁濟先生的一生貫穿中國歷史近現代之交、清末民初的動亂歲月,雖其本人并非經天緯地之才,名聲影響也遠不及其次子梁漱溟。然而,細究梁濟先生的家世生平、好惡取舍及立身之道,卻是一個深受儒家文化教化而自律甚嚴、非常有個性的仁人君子。
家世生平
梁家本是元朝宗室后裔,祖先與元朝皇帝同宗,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朝在中原地區覆滅,末代皇帝順帝帶著皇室及近支親屬逃回北方(即今蒙古)。梁家祖先未走,留在河南汝陽,今在河南洛陽市境內。此地屬于戰國時魏國的都城,古稱大梁。梁家祖先以地為姓,改蒙古族的“也先帖木耳”為漢姓“梁”。自此至第十九代梁垕,由河南遷徙至廣西桂林居住。梁垕的兒子即梁濟的祖父梁寶書,應鄉試中舉人后,又進京會試中進士,歷任直隸、正定等地知縣和遵化知州。此后,全家居住在北京,未再回桂林。
梁濟的父親梁承光,在北京即順天府應鄉試中舉人,后在山西離石縣(當時叫永寧州)做官。梁承光不僅是學者、詩人,也是優秀的騎手和統兵將領。但他的生命像彗星一樣短暫而奪目,三十六歲時在山西防堵捻軍的軍旅中,“瘁力極勤而死”。
梁濟先生于1858年11月15日(農歷十月十日)生于北京,父親梁承光外放山西為官、剿捻時,和家人一起隨父親在山西任所居住。梁承光去世時,梁濟僅八歲。由于祖父梁寶書為官清廉,去世時不僅沒有積攢下家業,還欠有外債。梁承光的官俸不僅要養家糊口,還要為父親梁寶書還債,至三十六歲身故,債尤未清。梁承光的早逝,使得梁家頓時陷入困境。
梁承光的妻妾帶著梁家的繼承人和未來的唯一希望、年僅八歲的梁濟從山西回到北京,無力置辦房產,借了幾間姻親的房子居住。梁承光的岳父乃是會試中進士后為官,妻子從小讀書,才可賦詩作文,于是開蒙館教授幾個學生,聊以度日。到了梁濟老年,還念念不忘幼時居住在擁擠的房子里,嫡母在家中設蒙館課徒,生母靠洗衣賺取微薄的收入,過著省吃儉用的拮據生活。
梁濟不是一個天資很高的人,雖家道落魄,仍不失為書香門第,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嫡母以嚴格的儒家學說教導和砥礪梁濟。梁濟十九歲時,已在“義學”中教書,但直到1885年才取得舉人的功名。又過了十三年,直到1898年,才得到一個內閣中書的官職。此前,為了生計,梁濟當過私塾先生、貴族的家庭教師和在京官員的私人幕僚。梁家一直生活清苦,梁濟二十多歲的時候,有官宦之家愿意把女兒許配給他。梁濟擔心娶一個不能過苦日子的媳婦難辦,竟至拖延了數年才成婚。至1898年,梁濟已經有了四個子女,其中包括生于1893年的次子梁漱溟。
梁濟在內閣任職至1906年,得以出任管理外城巡警總廳的外城教養局的總辦委員。這是梁濟自己認為一生最有意義的工作。據《清史稿·忠義·梁濟傳》記載:“梁以總局處罪人,而收貧民于分局。更立小學,課幼兒,俾分科習藝,設專所售之,費省而事集。”他在《留屬袁、馮、林、周、彭五兄弟》里有夾行細注,說自己“在教養局以撙出余財三百金,不以入己,而蓋小房六間。總廳不肯上達,故堂官不知”。
1908年,梁濟的嫡母病故,遂辭官守制。1911年,梁濟復職,見官場腐敗,“慨然欲掛冠去”,乃寫奏章分別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陳述自己的規勸性意見。翌年,前兩部寫完,官德部分尚未動筆,武昌起義成功,清王朝終結。梁濟抱著希望國家能夠逐步好起來的心愿,在民政部任職。但不久他便感到失望,在其給內務總長趙秉鈞的信中說:“但為一官,則待遇與百姓判若天淵,而民國以民為主體之義,則相率而忘之。革命以后之氣象,與革命以前毫無殊異,且更黑暗加甚;此濟所以心有不寧。”1913年5月,梁濟寫信給趙秉鈞,希望派他重回教養局。由于趙秉鈞牽涉宋教仁遇刺案,此事未果。此后,梁濟未再擔任公職。
1917年,北京上演“張勛復辟”鬧劇,梁濟對現實痛心疾首。在留下《敬告世人書》、《留示兒女書》等遺書后,1918年11月10日,梁濟自沉于北京凈業湖(積水潭)。此時,梁濟家人正準備梁濟11月13日(農歷十月初十)的六十大壽。11月7日,梁濟告訴家人他去好友彭翼仲(名詒孫)家借住幾天,生日那天回來。臨出門時,梁濟看到報紙上一條國際新聞,乃自言自語道:“世界還會好嗎?”次子梁漱溟接話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濟長嘆一聲:“能好就好啊。”此番對話令梁漱溟終生不忘。
激進趨新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的士大夫和晚清朝廷大致認識到在堅船利炮等器物、技術方面,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存在很大差距。這時意識形態的主要爭論在少數主張學習西方科技經濟和外交的“洋務派”和大多數昏庸保守的官僚之間展開。此時,著名學者和官員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的《瀛寰志略》已經刊行,一些急于了解西方的讀書人大多讀過這兩本書。
“洋務派”官員中,中國第一個出使西洋、作為英法公使的郭嵩燾的見深識遠,卻不為多數人所接受。李鴻章等大員雖然承認西方的技術進步,但因認識不足,又礙于庸朽的晚清朝廷的“臉面”,堅持認為中國的文物制度仍是世界上最優的。只有郭嵩燾大膽直言,認為西方不僅技術先進、器物超群,而且文物制度也遠超中國之上。郭嵩燾在他已經制版準備印刷,而因受到官方和社會極力抨擊而毀版不印的《使西紀程》中寫道:“計英國之強……推原其立國之本,所以持久而國勢益張者,則在巴力門(Parliament,即議會)議政院有維持國是之義,設買阿爾(Mayor,即市長)治民,有順從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交相維系。……中國秦漢以來二千余年適得其反。能辨此者鮮矣。”
此時,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梁濟堅定地支持“洋務派”的思想觀點,鄙視保守派的盲目愚昧,對來自西方的技術和社會思想深表歡迎,甚至為洋務派所不及。到1883年,梁濟經過痛苦而深入的思考得出結論:中國的經典不能回答西方的侵略所產生的新問題。這對于自小接受經史子集傳統教育、為儒學所深刻熏陶的梁濟而言,并非易事。梁濟清楚地意識到他的這種思想意識和對西學的態度,將會受到某種社會的和政治的懲罰,但是,以郭嵩燾為楷模的梁濟置個人毀譽于度外。他在日記中寫道:“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深切時事斷不可以不看。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我只求實事,不能避世人譏訕也。”
“只求實事”反映出梁濟惡虛崇實的個性特征。梁濟認為:中國之積弱,全為讀書人專務虛文,與事實隔得太遠所致。值此社會大變局之時,自覺擔當社會責任的梁濟,斷不會坐而論道或坐視旁觀。
梁濟關注的主要是來自上層的改革,如積極支持康、梁變法等。此時他認識到不教育和動員普通群眾和改造國民,國家的興旺沒有可能。1902年,他支持好友彭翼仲創辦了《京話日報》。這是中國報業史上第一家以促進普通群眾的覺醒和社會改革為目的報紙。為了獲得廣泛的讀者,他們采取了一個革命性的步驟,報紙刊文不用當時風行的文言,而用通俗語言,即白話。這一舉動如此大膽,以致北京的讀者都稱它為“洋報”。
《京話日報》在當時整個北方,甚至遙遠的山西、甘肅和山東都有人訂閱傳播。報紙所產生的廣泛影響力,使其成功地在京師鼓動起了幾次民眾的民族主義運動,如庚子賠款捐款的運動和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借助報紙發行的聲威,梁濟和彭翼仲還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兒童啟蒙畫報。畫報致力于傳播科普知識、時事和外國文化。這份畫報第一次把所謂的“賽先生”介紹給了北京人。
由于民智未開,加之主辦者缺乏經營的技巧和經驗,報紙的發行不賺錢還要虧蝕。此時,梁家的家境并不富裕,經常入不敷出。1908年,因為嫡母過世,梁濟辭官守制,家用更是捉襟見肘。但是,梁濟急公好義,為辦報所出之資,本沒有指望回本或是賺錢。他之所以這樣做,一是由于他和彭翼仲的好友關系,二是他認為這是仁人君子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1906年,由于《京話日報》的言論引起西太后的不快而被查禁。次年,彭又創辦了另一份報紙《京話報》。不久,《京話報》又因披露袁世凱在北洋營務處秘密毒殺黨人的事而激怒袁世凱,報館再次被封,彭翼仲被流放到新疆荒涼地區。在這兩次事件中,梁濟都不顧株連的危險,極力幫助了自己的朋友。
梁濟積極支持新學和社會變革的價值觀和訴求,也體現在他對孩子教育的選擇上。次子梁漱溟六歲時在家塾開蒙念書,但不是死背“四書五經”、之乎者也,梁濟拿出一本名叫《地球韻言》的世界歷史和地理的入門書,指定家塾先生作為教材。1899年,當北京第一所中西小學堂開辦后,梁濟便送梁漱溟入校讀書。在這里,時年七歲的梁漱溟學的不是中國的傳統文選,而是查閱英語識字課本,學習ABC等英語課文。1903年,當京師譯學館第一次招生時,梁濟就將年長次子六歲的長子梁煥鼐送去念書。三年后,他又讓梁煥鼐去了日本東京,學習傳統的士大夫最瞧不起的商業。他還把兩個失去父母的表甥也送到了譯學館就讀,后來又要他們去英國攻讀法學學位。梁濟不僅讓他的兩個女兒上了學,而且上的都是新式學堂。
對朋友辦報的支持,體現了梁濟的道德擔當和犧牲精神;對孩子教育的選擇,則體現了梁濟對未來社會和子女前途的期望。這都表達了梁濟積極支持國家和社會變革和堪稱激進的思想意識和社會改革訴求。
恪守舊道
梁家后代子孫留居中原王朝治下,近代以來累世讀書取得功名并在朝廷為官,不僅深受儒學文化教化,而且因為不斷與漢族聯姻,血脈也逐漸漢化。秉性篤實的梁濟,忠君愛國的思想深入血液,雖然理智上認定傳統文化已經難以救國,但感情上仍然深刻認同清室,骨子里自覺地去做一個沒落王朝的忠臣。
梁濟自覺維護傳統道德的表現,首先表現為對傳統禮制的自覺遵守。1908年,梁濟因嫡母病故而辭官守制。此時梁濟當時急需用錢,辭官立即斷了官俸,守制三年的習俗也早已過時,很少有人遵守,但梁濟還是自覺遵守舊規。
其次,梁濟雖然深知舊的時代覆水難收,朝廷昏聵無可救藥,但他從感情上仍然不忍朝廷顏面掃地,既希望去除舊制的弊端,社會改革向前,也希望道統得以維系。由于清廷是以和平方式向民國轉移權力,雖是迫不得已,但避免了刀兵戰火生靈涂炭。然而,清朝覆亡,民國依舊腐敗,社會風氣江河日下,道德淪喪民不聊生。這使梁濟內心非常痛苦。
在梁濟這樣的心境和情緒之下,1917年,北京發生了“張勛復辟”事件,張勛帶“辮子軍”入京。梁濟雖然不曾顯赫,當時更是一介書生,人微言輕,但還是忍不住向張勛寫長信,勸張“勿為復辟迂謀”,并希望張發揮作用使清室“禪讓之心大明,共和之美漸能實現”。后來再勸張寫兩信進言:“行虛君共和,勿昧循舊制。”看到阻止不住,再勸不要恢復一姓制度、打出龍旗、封王封爵。
但是,梁濟勸張勛不要干的事,張都一件件干了。段祺瑞、梁子超率領一師北洋軍在馬廠誓師討逆,復辟的鬧劇六天就完蛋了。復辟失敗,梁又去信勸張勛“死節”,而張選擇的投降條件只有一個,就是活命。
梁濟不反對清朝遜位,更不反對共和,但他對民初幾年的種種變亂和變化感到憤慨和失望。在新與舊的糾結之中,梁濟深感痛不欲生。他懷抱自盡以警世的決心已五六年之久,只因覺得自己對國家社會所負責任未了而一再推遲。張勛復辟的鬧劇,為梁濟的自殺警世提供了最后的推力。
梁濟自沉的次日,即1918年11月11日,《京話日報》最先刊登梁濟自殺的消息,并全文發表《敬告世人書》等遺文,隨后各報紛紛轉載,引發熱烈的社會反響。《京話日報》的編輯吳寶訓聞此消息,非常感慨,隨即也投湖自盡。
在《敬告世人書》中,梁濟痛陳:“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比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很顯然,這是典型的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與責任擔當。
在《留示兒女書》里,梁濟說到自己尚未出嫁的次女謹銘,充滿父愛之情:“真正仁考明哲之女也。凡我所需要,無纖細之遺忘,凡幼孩之前途,無防維之不至。每遇春秋佳日,必設法勸我消憂。我聽夜戲,半夜歸來,無一次不獨自看書,煎茶守候,視我安眠而后去。雖成人而猶孺慕,尤能匡我見所不到,我心實無間然。至其屈己安貧,十年前之舊衣已小,猶著在里面,聊以御冬。……嗚呼!我有如此雍雍熙熙之家庭,我何忍決然舍去哉!”這是梁濟的至情至性和父愛親情的真切流露。
兩封遺書是儒教核心理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典型體現。對于梁濟的自殺,社會反應大致有三類。一是批判,認為梁濟自殺是殉清,逆潮流而動,很不足道。《新青年》雜志曾專門就梁濟自殺展開討論,陳獨秀、陶孟和、李大釗、胡適等都寫了文章,均持批評態度。二是贊揚,認為梁濟自殺是殉道,有副對聯,上聯是“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下聯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代表了這種看法。三是介于二者之間,認為梁濟自殺殉清和殉道兼而有之,殉清雖不足取,以身殉道的精神卻不應全盤否定。
儒家文化入世擔當、舍生取義精神的相互作用與綜合,梁濟終其一生的目標是把自己鑄造成一個內在精神完美和外部行為適宜的道德完人。為此,他為自己規定了嚴格的行為準則,即使一人在家,他也衣扣扣得整整齊齊,“君子一人,必慎重其行”,“十目所視,十指所指”。這樣一個有道德潔癖、對自己嚴厲規范且有很高自我期許的人,在當時道德淪喪、腐敗的社會,這注定了梁濟最后的悲劇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