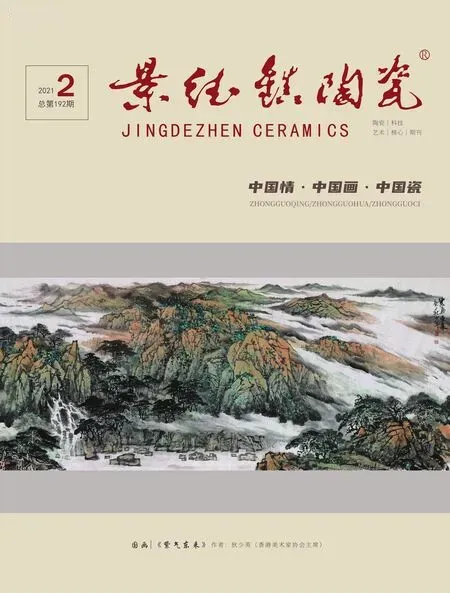盛世圖景,歸元致和
——世界文明新時代下的景德鎮學與未來
姚若晗
在人類文明史上,有一個絕無僅有的奇特現象。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數千年文明演進過程中,從未出現斷層。從信史可考的周公制禮,到孔孟傳統、老莊精神,以及后來的佛學思想,彼此促進融通,常演常新,生生不息,一脈相傳了3000多年。
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文化早已湮滅在歷史的煙塵中。即便是后起的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其文化傳統同樣在致命的沖擊下斷裂過,在中世紀的幾百年,歐洲人甚至都看不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
人猿相揖別。
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
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幾千寒熱。

法國皇帝建造的中國瓷宮
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寥寥數語,道盡從人類誕生至今縱貫幾百萬年的歷史。
這些湮滅與斷裂的文明,似乎也揭示著文明迭代、國家興亡、民族榮枯、文化盛衰的某種必然。
那么,渡盡劫波而碩果僅存的中國文明,究竟是必然中的偶然,還是偶然中的必然?
答案,也許就潛藏在中華民族具有獨特性的文化基因中。
在歷史上,中華文明的輝煌,乃至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國家版圖的形成與鞏固,固然是以強大的國力為前提,但最終依托的還是文化軟實力的潛移默化。
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反思,乃至自我否定與全面革命,直至伴隨國力增長而逐步恢復文化自信,也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積累了不少經驗與教訓。
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中國需要逐漸擔負起引領世界文明新時代的責任,這是中國的歷史使命,也是中國的文化使命。
一年樹谷,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那么千年呢?唯有樹文!
文化乃千年大計,亦為國家與民族立世之本、綿延之因。文化的范疇極其博大,世所公認的是,在非物質文化層面,核心載體應為文字與語言,在物質文化層面,核心載體則是建筑與器物。
在中國器物文化當中,瓷器是毫無爭議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國的代名詞。在中國文化偉大復興的進程中,瓷器所承載的瓷文化必然不可缺席,瓷文化輝煌的象征就是世界瓷都景德鎮,故爾,以“景德鎮學”為代表的瓷文化學術體系的全新構建,更是題中應有之義。
洞察歷史,方可洞見未來。“景德鎮學”之興,其來亦必有自。
一、“景德鎮學”的立學背景與宗旨
為什么要有“景德鎮學”?這是一個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
亙古以來,陶瓷是第一種人造材料,更以其廣泛深遠成為人類共同的記憶,瓷器,則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對話的語言。
隨著考古學的蓬勃發展,以及中國與世界各地早期陶器的不斷發現,陶器起源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許多歷史的謎團相繼解開。
從世界范圍來看,發明陶器的時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最早的陶器出現在距今約1.5萬年前;美洲的陶器最早距今只有5000多年;西亞地區最早的陶器不早于距今9000年前。但并無證據表明彼此之間存在關聯性。因此,陶器的起源應該是多元化的。
而世界瓷器的發展歷史,是從中國開始。
從距今三千多年前商代早期青瓷器在中原及長江下游出現,到公元二世紀左右東漢時期成熟的瓷器在浙江首先燒成,甚至到隋唐時代“南青北白”的局面出現,世界上除中國以外尚無人知曉瓷器燒造的秘密。
中國的制瓷工藝,大約在五代時期傳至毗鄰的朝鮮,并催生出富有朝鮮民族特色的“高麗瓷”;南宋時期又東傳扶桑,日本人左衛門景正、加藤四郎在中國福建學習燒瓷五年后,歸國燒制出日本最早的瓷器——“瀨戶物”;而直到十八世紀,西歐諸國師法景德鎮,才相繼燒制出真正的高溫瓷器。
因此,世所公認中國是發明瓷器的唯一源頭,這一點與世界范圍內陶器的發明與發展截然不同。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用泥土制陶是全球人類的遠古創造,而發明瓷器卻是中國人獨享的榮光,也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杰出貢獻。
瓷的出現不僅賦予陶器以驚艷世人的光潔晶瑩,更為之融入了文化與藝術的精魂,由此傾倒眾生、風靡世界。瓷器與人類的生存環境、生產方式、生活習慣、社會制度、宗教信仰、審美情趣等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而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瓷器也蘊涵著不同的歷史與人文內容,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瓷文化。
作為瓷器的發祥地,瓷器不僅是中國傳統工藝美術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國歷代財富的重要來源。在中國歷史上,瓷器以其特質,一統天下財物,匯為巨大產業,并成為中華文明的圖騰性器物;在文化情感上,瓷器又是中國人的無間紐帶,以其美輪美奐,上達宮廷下遍黎庶,跨越千年橫貫東西,直面中華文明中最世界文明的部分。
曾幾何時,來自中華上國的瓷器在歐洲曾有“白色金子”之譽:歐洲人甚至用金銀器作底座來陳列來自中國的瓷器;用皇帝的衛隊來換中國的瓷器;在歐洲各國的皇宮競相建造瓷宮來收藏來自中國的瓷器;能否收藏中國的瓷器,幾乎是關系到貴族身份和地位的問題。遠隔重洋的東西方文化,由此找到了互鑒共通的器物載體與審美語言。
世界由此認識了中國,china(瓷器)也由此成為中國的代名詞。
在世界器物文明領域,中國的瓷器、絲綢與茶葉舉世聞名,深刻影響并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進步,而在這三大產品中,又是以瓷器對世界文明的影響居首。
中國瓷器輸出到世界各國的主要途徑有三個:
一是作為國際交往禮物,贈送外國使節;

慈禧太后贈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瓷胎琺瑯瓶一對
二是通過宗教的紐帶傳播到世界各國,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大宗教的信徒們頻繁往來,充當向外傳播中國瓷器的載體,在文化意義上影響尤其深遠。
三是通過絲綢之路(瓷茶之路)的貿易,以景德鎮為代表的中國瓷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這也是最主要的輸出途徑;僅在18世紀的一百年中,中國瓷器輸入歐洲的數量,據最保守的估計,也在6000萬件以上。中國也是茶葉的原產國,所以茶葉貿易額長期高居世界第一。瓷茶兩項形成了巨大的貿易順差,在當時,世界上近一半的白銀流入了中國。
陸海絲綢之路曾經是中華文明在世界傳播的核心途徑。絲綢之路橫跨千年的繁榮,也將中國的文化輸出到陸海絲綢之路沿線地帶,并在東亞東南亞一帶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東方文化圈,成為文化的宗主國。
歷史的輝煌漸行漸遠,絲綢之路空余絕響,但其在中國歷史上開始的中西文明的接觸碰撞與相互激發、學習、滋潤與融合,無疑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向前發展,中國瓷器與瓷文化也正是沿著陸海絲綢之路遠播世界。
近代以來,中華國力式微,神州百年陸沉,西方文明強勢主導世界,中華文明的文化軟實力嚴重削弱,曾經是文化軟實力重要載體的中國瓷器也黯然失色,失去了世界高端市場的領地。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盡管局部戰亂頻仍,但和平與發展依然是世界的主題,全球經濟與文化大融合的大趨勢日益明顯。在世界文明發展的新階段,國家地位的提升不僅要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后盾,而且要以深遠的文化影響力為先導。
作為瓷文化的發祥地,中國不僅擁有數千年綿延不絕的陶瓷文化傳統,也在世界范圍內具備無與倫比的瓷文化影響力。然而,曾經在歐洲被稱為“白色金子”并頂禮膜拜的中國瓷器卻至今屈居人后,甚至成為廉價產品的代名詞,中國瓷器產業的國際地位更是令國人汗顏,這與中國瓷文化的輝煌歷史以及正在走向偉大復興的中華新貌無疑極不相稱。

鄧小平同志出訪贈泰國國王景德鎮瓷雕《六鶴同春》

在東南亞佛教區域廣泛流傳的觀音瓷像
目前梅森、塞夫勒、柏圖、道爾頓、雅致等歐洲品牌,幾乎壟斷了國際高端瓷器市場。缺乏世界級品牌,是中國瓷業現狀的折射,而藝術與市場的脫軌、文化與產業的斷裂、工藝技術水平的落后、設計與創意價值的缺失以及管理機制、營銷手段與全球化市場的脫節,才是中國瓷業難以再現輝煌的深層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瓷文化的沒落與支離,中國瓷文化的沒落,又是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嚴重弱化的一個縮影。
一個產業乃至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強大,必然伴隨著文化的深遠影響力。作為中國器物文化的代表,中國瓷業一旦失去了瓷文化的引領,也就失掉了產業的靈魂和器物的核心價值。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文化重塑的至高目標就是重建文化自信。當今之中國,經濟快速騰飛,國力大幅增長,但在文化重塑方面依然任重道遠,尤其需要在一些具有深遠影響力的文化學術方面率先突破,這當中無疑就包括了以景德鎮為代表的中國瓷器文化。
鑒此,文化重塑不僅是“景德鎮學”的核心宗旨,更是一項重要使命。
景德鎮是偉大的歷史空間,擁有金字塔般的陶瓷文化品牌忠誠者,但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塔尖文化,甚至遭受“有歷史,沒文化”之譏。
為什么會有這種現象?
古往今來,一代代能工巧匠創造了景德鎮博大精深的瓷文化,但這些創造者受制于文化地位,雖有名器傳世,卻難著書立說。而由于中國“重道輕器”的儒家傳統,文人士大夫普遍將瓷藝視為“君子不器”的工匠之作,鮮有將其提升到文化層面來審視。雖然也有南宋蔣祈《陶記》、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陶埏》、清代唐英《陶冶圖說》、藍浦《景德鎮陶錄》等古代文獻傳世,但數量之少、篇幅之短、范圍之窄、角度之狹,不過渺如滄海一粟,即便加上目前的陶瓷文化研究成果,也僅是冰山一角,無盡的陶瓷文化寶藏尚待挖掘,這與景德鎮在歷史、在世界與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與影響十分不相稱,也難以從文化體系的角度支撐景德鎮乃至中國瓷文化的復興大業。
景德鎮至今保存著完整的古瓷業文明體系,這座有著兩千年歷史積淀的古代瓷都,其研究領域應該涵蓋社會、政治、經濟、藝術、歷史、考古、文學、民俗、地理、哲學等諸多方面,涉及社會發展史、藝術史、思想史、科技史、陶瓷文化傳播史、社會經濟史等眾多學科領域。景德鎮世界瓷都地位的重塑,乃至中國瓷文化自信的恢復,無疑需要有真知灼見的學術導引,而從文化尋根到當代塔尖文化的設計,也都需要構建起一套能夠代表景德鎮歷史與文化價值的理論研究體系。但目前,學術幾乎缺席。
“景德鎮學”的誕生與學科體系的建立,正可謂天降大任于斯學。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景德鎮學”創立之宗旨,首先是從關注和研究景德鎮輝煌的歷史入手,從對歷史的深刻研究中提煉出“景德鎮陶瓷之精神”和“景德鎮之魂”,與此同時,從家庭到社交,從產業到意識形態領域,顛覆與創新無處不在,解析與重構勢在必行,瓷文化也必須和當代生活方式共同轉移,并以與時俱進的呈現形態,匯入世界文明新時代的巨大潮流。
正是基于以上歷史與人文背景,中國瓷文化亟需構建起兼收并蓄、推陳出新的思想內核與理論體系。如何系統構建?如何與時俱進?而又如何切入?這些都是“景德鎮學”需要回應的時代關切,也是催生“景德鎮學”的文化原動力。
二、“景德鎮學”的研究對象與立學根基
“景德鎮學”究竟應研究什么?
關于“景德鎮學”的研究對象,很容易望文生義,誤以為就是研究景德鎮陶瓷或是景德鎮地域文化的學術體系。而實際上,與其他顯學相較,“景德鎮學”既不同于以地域文化研究為主的“徽學”,也不同于以文物研究為主的“敦煌學”,更不同于以世家文化研究為主的“紅學”,“景德鎮學”的研究對象,不僅涵蓋景德鎮陶瓷器物與地域人文的系統研究,而且以哲學和藝術、歷史、政治、經濟、科技思想為深刻背景與依托,運用綜合的研究包括現代的科技手段與方法,研究景德鎮陶瓷生產、銷售與消費的各個環節所呈現和反映的材質文化、工藝文化、裝飾文化、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傳播文化、歷史文化等,以及所積淀和反映的哲學思想、器物思想、科技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藝術思想,進而拓展至研究人類不同時期的生活方式與文化規律、文明演進等內容,并由此上升到研究以景德鎮陶瓷為核心載體的瓷道文化在人類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作用、意義與趨勢,最終揭示出人類未來的文化生活方式與美學范式。
總體來看,“景德鎮學”遠不止是景德鎮瓷學或景德鎮市學,不僅是兩者的深度融合,更應大大超越這一層面的研究。
首先,“景德鎮學”不僅僅是景德鎮瓷學。毫無疑問,“景德鎮學”跟景德鎮陶瓷有關,它當然要研究陶瓷,而且是以景德鎮陶瓷為主要研究對象,不僅要研究景德鎮陶瓷的材質文化、工藝文化、器物文化、消費文化、習俗文化、制度文化等,還要由此拓展和延伸至這些文化所積淀和體現出的哲學思想、器物思想、技藝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等,并進而研究景德鎮陶瓷對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審美價值、審美情趣以及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影響。凡此種種,決非是單一的瓷學所能概括的。瓷學主要是研究瓷本身,是有關瓷的一種專門性學科,其研究內容主要是陶瓷的材質及其組成、工藝過程等,偏重于技術層面的研究。概括而言,“景德鎮學”是包括而遠不限于研究瓷學,在研究內容上就應體現出全新的學術理念和學術思想。

富有希臘、羅馬色彩的犍陀羅藝術瓷器

明永樂景德鎮窯青花阿拉伯紋無擋尊
其次,“景德鎮學”也不僅僅是景德鎮市學。“景德鎮市學”是以景德鎮為對象,研究景德鎮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等內容的學科,其研究區域主要是景德鎮。當然,這其中也包括區域比較研究,也會包括“景德鎮學”的相關內容。但是,“景德鎮學”遠不止于景德鎮區域的研究,而是以富有創新內涵的學術思想為指導,以景德鎮陶瓷為緣起和主要線索,對景德鎮和景德鎮陶瓷文化進行全方位的拓展與延伸研究。簡而言之,景德鎮地域學的研究是“景德鎮學”不可或缺的一環。同時,“景德鎮學”還應把目光投向整個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更要把“景德鎮學”研究從文化本身的研究拓展到文化史、文明史、科技史、經濟史以及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研究,進而研究人類的一種文化生活方式與樣式,其內容涵蓋極廣,其敘事極為宏大,但其研究之根基,則必立于瓷文化底蘊極為深厚、形式極為多樣的世界瓷都景德鎮。

南海一號沉船打撈現場與打撈出的大量中國出口瓷器
脫離景德鎮,就沒有“景德鎮學”。
景德鎮瓷業肇始于漢世,崛起于宋初,鼎盛于明清,綿延至當代,“集天下名窯之大成,匯各地良工之精華”,以一業獨撐一城,歷千年而不衰,引舉世之矚目,成瓷器之圣地,并獨享“世界瓷都”之盛譽。
景德鎮雖非中國瓷器發祥地,卻是無可爭辯的集大成者。盡管在北宋初期,景德鎮已經異軍突起,博采“南青北白”瓷系之長,創燒出晶瑩雅麗的影青瓷,但在那個令人神往的時代,仍然是“汝哥官定鈞”五大名窯交相輝映,景瓷尚未樹立中心地位。宋室南遷是一個影響深遠的歷史轉折點,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隨之移居江南,景德鎮由此融匯吸納天下名窯之良工絕技,博采異地乃至異國文化之精華,兼收并蓄,銳意創新,與時俱進地“開創一代未有之奇”。
成就景德鎮瓷都偉業的因素有很多,譬如水土宜陶,譬如戰亂較少……而其首要原因,卻毫無疑問是官窯。
在瓷器發展史上,中國古代官窯(明清以后一般特指御窯)無疑是一座永恒的豐碑,官窯瓷器不僅代表著所處時代制瓷技術與工藝的最高水平,而且體現著中華民族的素質、文化水準與時代風貌,有著深刻而又廣博的人文與美學內涵,對世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變革、進步與發展產生了極為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
景德鎮之所以成為景德鎮,官窯是獨一無二的影響因素,這也是“景德鎮學”體系的構建與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景德鎮曾經是中華文明與世界對話的代表性城市,雖然與鼎盛期不可同日而語,但景德鎮仍然保持著其他城市無法企及的一些特色資源與發展優勢:
其一是在瓷業范疇,景德鎮目前仍保持優勢的,一是傳統制瓷的技藝得到了較為完整的傳承與發展,仿古瓷領域至今獨步天下,甚至可以在古玩市場通行無阻;二是手工陶瓷的生產體系得到了最完整的保留,在一些文化性、差異性需求特征較為明顯的生活用瓷類別上富有特色;三是在藝術陶瓷領域的影響力首屈一指,盡管藝術創新力量大多來自外力驅動,但景德鎮一直是開放包容與因循守舊的矛盾共同體,因而依托外來的藝術創新力量,一直保持著在藝術瓷領域的領先地位。而在大眾化的生活用瓷如餐具領域,景德鎮則已全面棄守,充斥全市攤店的餐具幾乎都來自異地,但大都打著景德鎮的旗號,可見景德鎮這一跨越千年的金字招牌盡管已日漸褪色,卻依然有著不可低估的號召力,并由此自然形成了龐大而蕪雜的瓷業集散地。
其二是在陶瓷歷史文化領域,景德鎮號稱“地上一個瓷都,地下一個瓷都”,地面歷史遺存與地下文物遺存都極為豐富,陶瓷文化景觀更是比比皆是。景德鎮的歷史文化特色資源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一是千年瓷都的形象景觀。千年制瓷史形成景德鎮特色文化之地與傳統工業之所的獨有風貌帶——依昌江蜿蜒、傍丘陵起伏的“村村窯口,戶戶陶山”的窯城形象。綿延至今,鎮內依然遍布由弄堂、牌坊、祠堂、閭門、民居、店鋪等構成的古樸幽雅的明清建筑群落,在一些區域還殘留著陶瓷古鎮的痕跡,近年來富有文化氣息的仿古景觀也在增多,但是總體來看現狀比較凌亂,尤其欠缺系統有序的成片規劃與打造。二是極其豐富的陶瓷文化生態,景德鎮不僅匯集了來自八方的陶瓷能工巧匠,而且吸引了全世界最多的陶瓷文化藝術群體來到這里體驗、創作乃至候鳥式定居,從傳統手工學徒、陶瓷專業學生到各路民間高手、國內外頂尖藝術家等,這些群體各具特色,形成了豐富多彩的陶瓷文化生態,“景漂”更是成為了獨一無二的一道靚麗風景。
其三是在自然生態環境與地域文化方面,景德鎮地處贛浙皖三省交界之地,同時也是三省文化交融之地,受徽文化影響尤甚,景德鎮屬于江南山區與丘陵地帶,山明水秀,氣候宜人,自古盛產名茶與原生態農林特產,并有四方名勝聚合,物產豐饒、風情各異,文化與自然旅游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廬山、黃山、龍虎山、三清山、鄱陽湖、婺源等旅游熱點皆在左近,大有新風云之象,不僅可無縫對接周邊觀光游的總路線,更可針對高端社群發展獨一無二的陶瓷文化與休閑生態深度游。
毋庸諱言,作為一個內陸小城市,景德鎮在很多方面并不具備優勢,譬如觀念、人才、資金、基礎設施等,而在前面提及的幾點特色與優勢基礎之上,景德鎮最有可能也最需要打造的核心優勢就是文化優勢,有不少外來的高端群體對景德鎮的整體評價是“有歷史,沒文化”,這個“沒文化”實質上是指景德鎮沒有建立起文化話語權和影響力。
景德鎮正因為有歷史,才能舉世聞名,吸引八方來客,這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優勢,但又因為沒文化,掌握不了文化話語權,也就掌握不了文化產品的定價權,未能創造更大的文化附加值。在瓷器領域,景德鎮被壓低成一個手工制作基地,在文化旅游領域,景德鎮坐擁國家首批歷史文化名城等優勢資源,文化旅游產業目前的發展甚至還不及鄰近的婺源。
名瓷成景,厚德立鎮。景德鎮的城市發展定位已經確定為中華文明與世界對話的代表性城市之一,這個對話的要旨,無疑就是在新的世界文明生態中能夠為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代言一二。

宋真宗畫像,其時為景德鎮崛起之始
景德鎮對中華文明的最大貢獻,正在于引領中國瓷業技術與美學創新的腳步從未停歇,從而展現先進文化代表者的價值形象,并使景德鎮屹立中國陶瓷文化塔尖千年而不傾。這項使命,理所當然應由“景德鎮學”體系來擔當重任,而如何代表當下中國乃至世界的先進文化,就是“景德鎮學”系統研究必須突破的一大瓶頸,也是“景德鎮學”之學術根基必須深植于景德鎮的一大緣由。
洞察景德鎮歷史盛衰之表象,深究瓷道興廢之因由,審度文明進步之趨勢,然后可窺瓷文化復興之堂奧。
“景德鎮學”必以景德鎮為立學根基,而景德鎮的重塑,亦應以“景德鎮學”為文化支點,深入挖掘其文化價值與內涵,在經濟層面上,將景德鎮文化價值與當代中國瓷業發展全面融合,并以此推動中國瓷業從傳統制造業向具有高附加值的文化創意產業轉型,走出既有中華民族文化特征的傳承,又能彰顯當代文明風尚的產業強盛之路,而在文化層面上,就是致力于使瓷器再度成為向世界輸出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待續)
注:原文發表在《中國景德鎮學》第一輯P35-60,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