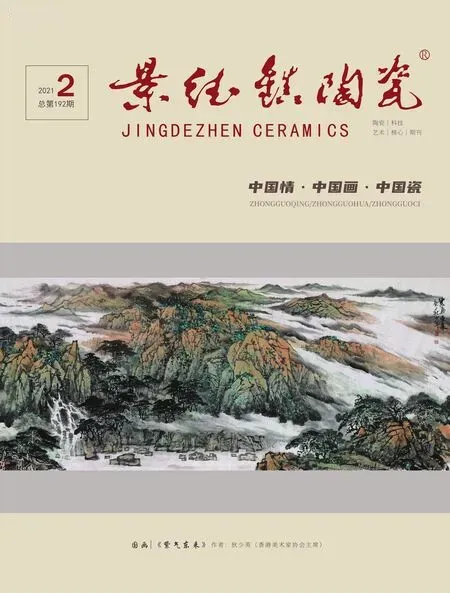民族文化影響下青花藝術造物的特質與風貌探討
于 杰
一、蒙古民族文化對青花藝術造物的影響
1、信仰喜好與色彩
縱觀歷史,統治階級的喜好會對藝術的走向和審美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蒙古族自1206年成吉思汗立國、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至1368年被明所滅的百余年間,陶瓷藝術一改宋風,瓷業呈現出一種全面的創新氣象和強大的創造魄力,游牧民族的色彩喜好、游牧傳統、數字觀念、裝飾理念等均體現在青花藝術造物中。成就了獨具特色的青花陶瓷藝術。
元青花的種種特征都與蒙古族的好尚血肉相連,據《史集》載,蒙古人的祖先是“有命于上天而生的”孛爾帖赤那,意為蒼色的狼,其妻豁埃馬闌勒,意為慘白色的鹿,也因這個傳說,蒙古人一直崇尚青白二色。而且蒙古族最初信仰的是原始的薩滿教,奉“長生天”為天神,“其蒼蒼之色為神圣,其太陽之白為吉祥”,也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元代青花藝術的發展。
2、游牧傳統與造型
蒙古族作為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來就有著十分濃厚的民族內涵和文化積淀,因又曾居于統治地位,強勢地保留了其風俗喜好。首先,蒙古人的遷徙習俗在建元后也得以延續,每逢春赴上都,秋返大都,他們轉徙隨時的生活多配以小型家具,器物多置于地面或低矮幾案,瓷器高大有利于提取。同時為了遷徙方便,蒙古人在造型上也加入了特別的設計,如遼代雞冠壺(圖1)上“孔”的設計就是為了方便攜帶而在仿制皮囊、金銀器時特意保留下來的,隨著蒙古族人逐漸由游牧向半定居的生活狀態轉變,壺身“梁”(圖2、圖3)的設計應運而生,壺身也由適合馬背上使用的高扁形轉變為更符合定居生活的圓矮形。其次,蒙古族人飲食與中原不同,其飲食豪放,食物多為大塊牛羊肉,食器大多厚重粗獷,形體巨大;但與之相對的是小型器物如青花高足杯也不見少數,這同樣是因蒙漢文化交融,其喜好由酒精含量低的馬奶酒到酒精含量高的蒸餾酒的轉變而轉變的。無論歷史上孔與梁的轉變、扁身向圓身的轉變、高壺向矮壺的轉變,還是的食器的大小形制,都是根據蒙古人民的生活方式而改變的。

圖1

圖2

圖3
3、數字觀念與裝飾
蒙古族人“喜三重九惡七”,他們崇尚“吉祥三寶”,三與九都寓意吉祥,九是蒙古民族最重視的數字,據傳是由于蒙古族的英雄成吉思汗“巧九喜九”,他出生后用九泉之水沐浴,九歲獨立生活,二十七歲稱汗。在一次征戰失利向天祈禱時,空中落下一鏃巨矛,隨即下令用九十九匹公馬鬃毛作其纓,九十九只綿羊來祭祀,并將這巨矛作為自己的軍徽稱為蘇勒德,也正是成吉思汗對九的喜愛更加影響了蒙古族人對九的崇尚。
而七關乎懲罰,涉及喪葬。歷來刑罰皆為整數,蒙古族雖沿用了唐以來的刑罰,但依忽必烈“天饒一下,地饒一下,我饒一下”的意思減為以“七”結算,所以在元代青花裝飾中花紋層數如云龍紋象耳瓶(圖4)一般,九層者甚多。

圖4
4、裝飾理念與革新
元朝的青花可謂異軍突起,雖有傳統題材的描繪,卻常配伊斯蘭特點的邊飾,如珍藏在大英博物館的元代纏枝花卉紋菱口盤(圖5),形成了多層分割、紋飾繁密、色彩艷麗、形式夸張的異域風格。元代的瓷器之所以有如此的創新和突破,首先是由于前代制瓷技術的深厚積淀,它有著唐宋先進的制瓷技術和藝術理念做后盾,在這基礎上又注入了許多外來文化的新鮮血液,其中最為直接的要屬信奉伊斯蘭教的伊朗和土耳其工匠與中國本土工匠的共同努力,以及大批來自土耳其王公貴族或商人的來樣定制的共同促進。正如吳仁敬先生在《中國陶瓷史》中所述:“因波斯、阿拉伯藝術之東漸,與我國原有之藝術相融合,對瓷業上,更發生一種異樣之精彩。”才使元代青花藝術展現出了獨特的風采。而且元代對海外貿易的重視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朝代,這在為國家帶來財政收入的同時也為青花藝術的發展帶來了契機,大量的新技術、新材料、新思想的交匯,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元代工藝品的風貌,使其一改宋代裝飾之簡潔而走向繁復,更出現了異國風情的青花陶瓷藝術形式。
二、蒙古族文化在當代青花藝術造物中的融入與發展
1、融合傳統與現代
傳統理念與現代時尚看似兩個相距很遠的概念,但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民族文化符號的演化從未中斷,并且孕育出一系列異彩紛呈的工藝美術成果。在當代青花藝術造物中,既要保留地域民族文化符號的傳統精髓,又要把握現代藝術潮流,用新思維、新理念、新技法進行重組與再創,從而使藝術更加貼近現代人的審美趨向與文化認同。

圖5
2、關注人文情懷
陶瓷從一開始就兼具藝術觀賞性與功能實用性于一體,當代蒙古族青花藝術的創新也要從功能上考慮,設計是以人為本、符合人的生理及審美要求的人性化設計,這也是近些年來十分重要的設計理念,被稱作是設計領域的最高追求。功能性、人性化與其民族文化符號在藝術與設計中是相輔相成的,將藝術引入生活,同時也因民族、宗教、道德等的滲透使陶瓷藝術更加有了人文情懷。
三、總結
地域文化符號是地域文明、民族文化的精華所在,它能夠引起人們共同的民族文化情感。廣泛的將蒙古民族文化符號應用于陶瓷藝術造物中,已成為當今藝術領域的主流思想。在深入挖掘蒙古民族文化符號內涵的前提下,走現代特色的原創陶瓷藝術之路,是藝術與設計過程中理應貫徹的原則和理念,這不僅能豐富陶瓷造物的藝術表現,增強區域文化特性,同時也對振興和發展民族特色文化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