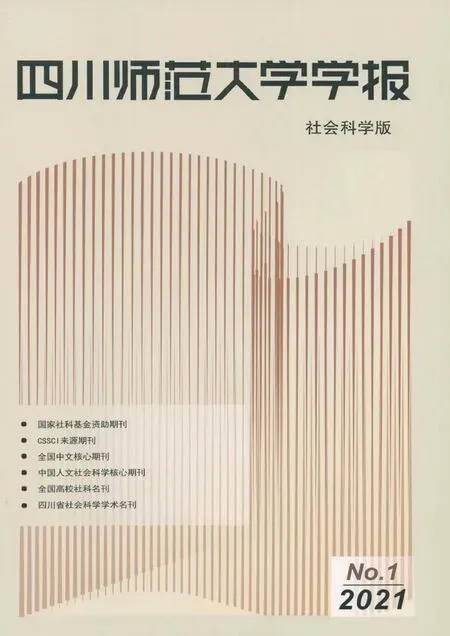環境規制、財政分權與區際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資源緊缺和環境污染問題卻愈發凸顯。為了解決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與生態環境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十三五”規劃強調要堅持綠色發展,著力改善生態環境;十九大提倡“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但是,各地區的環境污染問題依然嚴峻,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問題成為當前亟需解決的難題。我國面臨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重挑戰,自上而下的環境治理模式導致地方政府環境規制措施不一、規制過程難以協調①張華《環境規制提升了碳排放績效嗎?——空間溢出視角下的解答》,《經濟管理》2014年第12期,第166頁。,同時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地方政府對流動性資源渴望程度不同等因素促使污染密集型產業的區際轉移②沈坤榮、金剛、方嫻《環境規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轉移嗎?》,《經濟研究》2017年第5期,第44頁。。那么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路徑和主導因素有哪些,環境規制如何在轉移過程中發揮作用?上述問題的研究對產業轉型升級、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政策及措施的制定、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與政策意義。
一 相關文獻綜述
國外相關研究主要圍繞“污染避難所假說”而展開。該假說認為環境管制的提升將會加重企業負擔,迫使污染排放量較大的企業轉移至環境管制較為寬松的區域,從而將環境管制寬松之地變為環境管制嚴厲地區的污染避難所。如List等研究美國的產業數據,發現污染密集型產業更傾向于在環境規制寬松區域集聚①John A.List,W.Warren Mc Hone,Daniel L.Millimet,“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oreign and domestic plant births:is there a home field advantage?”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6,no.2(September 2004):321.。然而,Eskeland等對墨西哥等國家的環境規制和污染密集型產業投資等數據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對污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并沒有因環境規制水平的提升而降低②Gunnar S.Eskelanda,Ann E.Harrison,“Moving to greener pastures?Multinationals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0,no.1(February 2003):2-10.,“污染避難所假說”在這些國家并不成立。國內的相關研究結論也尚未達成共識,如史青認為寬松的環境政策對污染密集型的外商投資具有較大的吸引力③史青《外商直接投資、環境規制與環境污染——基于政府廉潔度的視角》,《財貿經濟》2013年第1期,第93頁。,區際間環境管制水平以及各地對企業污染排放要求存在的差異是影響污染密集型產業進行區際轉移的重要因素④何龍斌《國內污染密集型產業區際轉移路徑及引申——基于2000-2011年相關工業產品產量面板數據》,《經濟學家》2013年第6期,第78-86頁。,而張成等人的研究結果卻表明西部省份寬松的環境管制并沒有引發污染密集型產業在區域間轉移⑤張成、周波、呂慕彥等《西部大開發是否導致了“污染避難所”?——基于直接誘發和間接傳導的角度》,《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年第4期,第97頁。。
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來看,我國碳排放和GDP增速之間的差距有擴大的趨勢,甚至出現了背離的現象,碳排放不斷增大,而國內經濟發展卻呈現增速減緩的局面。為了降低環境污染程度,主體責任應該落實在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即“集權”與“分權”的作用孰輕孰重?對于這一問題學術界爭論不休。當前各地區積極地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除了淘汰產能低下、技術水平落后的污染密集型產業,引導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實現產業跨區域轉移也是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面。財政分權賦予了地區更大的自主權,提升財政分權度是否會促進區域自主轉移污染密集型產業,是否會促進區域形成環境污染降低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雙贏局面?正是基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本文將財政分權、環境治理與區際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三個話題有機地結合起來,深入分析三者之間的內在機制。
本文可能存在的邊際貢獻及特點:分析與回答了當存在環境管制政策時,污染密集型產業在地區間的轉移過程是否受到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權的影響;在存在空間異質性的情況下,環境規制對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作用機理是否存在異質性。在納入空間相關性的基礎上,利用空間計量方法分析財政分權對地方環境規制政策的影響,在研究設計上能夠更好地解決內生性問題,并且可以更加細致地觀測分權對環境治理行為的傳導機制,彌補此前文獻的不足。
二 理論假設
為了兼顧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制定和實施環境規制政策是政府的重要手段。環境規制能激勵產業轉型升級、提高其生產率,然而環境規制作用于企業生產成本的異質性卻不容忽視⑥王勇、李雅楠、俞海《環境規制影響加總生產率的機制和效應分析》,《世界經濟》2019年第2期,第97頁。。環境規制會加重企業負擔、降低其競爭力;還會擠占生產、技術研發投資,從而導致制造業技術無效率⑦沈能《環境效率、行業異質性與最優規制強度——中國工業行業面板數據的非線性檢驗》,《中國工業經濟》2012年第3期,第63頁。。然而,根據“波特假說”,雖然環境規制在短期過程中會加大企業負擔,但在長期過程中,環境規制能倒逼高耗能、高污染企業技術創新和治污技術升級⑧王書斌、徐盈之《環境規制與霧霾脫鉤效應——基于企業投資偏好的視角》,《中國工業經濟》2015年第4期,第18-23頁。。如You等認為環境規制可加速“僵尸”企業退出市場;“污染避難所效應”也強調了環境規制下企業的另一種行為選擇,即向環境規制寬松的地區轉移⑨Daming You,Yang Zhang,Baolong Yua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irm eco-innovation:Evidence of moderating effec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from listed Chinese industrial companies,”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7,no.10(January 2019):1072-1083.。總之,污染密集型企業,尤其是高耗能、高污染密集型企業,在環境規制約束下,可以進行重新選址決策,以降低環境治理成本。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
H1:當地區間環境規制水平存在差異時,提升環境規制強度能有效遏制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進入。
大量研究已證實地區經濟發展不僅依賴于區域自身稟賦,政府行為,尤其是環境規制政策對經濟發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二者之間具有長期的動態關系①李麗娜、李林漢《環境規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分析》,《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43-52頁。。另外,區域之間還存在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例如地區間的環境規制存在明顯的政策互動效應,一個地區環境規制的制定與實施會對附近區域產生影響②張華《地區間環境規制的策略互動研究——對環境規制非完全執行普遍性的解釋》,《中國工業經濟》2016年第7期,第74頁。,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環境規制強烈制約著污染密集型企業的轉移行為,差異性的環境規制政策塑造了地區污染密集型產業的分布③洪源、張玉灶、王群群《財政壓力、轉移支付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基于央地財政關系的視角》,《中國軟科學》2018年第9期,第173頁。。進一步地,從中國中東西部的區域角度看,東部發達省份亟待清除高耗能企業、進行產業提質升級,其地方政府勢必會加大環境規制力度,主動清除高污染、高耗能企業。同時,隨著東部省份勞動力和土地使用價格的上漲,中西部省份憑借傾向性產業政策、低成本的勞動力及豐裕的生產原料等優勢④湯維祺、吳力波、錢浩祺《從“污染天堂”到綠色增長——區域間高耗能產業轉移的調控機制研究》,《經濟研究》2016年第6期,第66頁。,將愈發成為東部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集結地。基于以上文獻,本文提出假設2:
H2:地方環境政策的制定以及區際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具有空間相關性,并且污染密集型產業將會逐步從東部省份轉移到中西部省份。
一直以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環境保護,政策法規是政府實現節能減排的關鍵舉措,其中財政分權是影響環境政策執行效果的重要制度變量⑤湯火箭、劉為民《地方政府對財政政策的執行策略:一個分析框架》,《中國行政管理》2012年第10期,第78頁。。根據傳統的分權理論,與中央集權相比,財政分權體制下的環境政策效果更佳。由于地方政府更易于發現當地居民的真實需求,所以中央財政放權將會使供給的公共品更具效率,下放到地方的權利愈高,地方政府供給公共物品的財政約束力就愈小。財政分權不僅對產業發展有重大意義,對減少治污成本也有積極的影響。在財政權力下放的機制體系中,地方政府更具有制定環境規制政策的自主性,所以財政分權將有利于環境保護⑥Qichun He,“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Evidence from Chinese panel data,”China Economic Review 36,(December 2015):86-100.。然而,處于政績考核氛圍中的財政分權易滋生地方政府的自利性行為,地方政府可能會放松環境管制、降低環境標準,為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進入創造可乘之機⑦谷繼建、鄭強、肖端《綠色發展背景下FDI與中國環境污染的空間關聯分析》,《宏觀經濟研究》2020年第9期,第127頁。。所以,地方財政分權度越高,地方政府將擁有足夠的自主空間,出臺優惠政策以削弱環境規制對企業成本的影響,進而吸引資本流入,提升地方經濟水平⑧孫曉偉《財政分權、地方政府行為與環境規制失靈》,《廣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8期,第124頁。。綜合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假設3:
H3:財政分權對污染密集型產業的轉移產生間接影響,能吸引污染密集型產業在本地區投資,也會削弱地區環境規制政策的效果。
三 模型設定及數據處理
(一)模型設定
實證部分主要探究環境規制是否會促使污染密集型產業在地區間發生轉移,以及地方財政分權對環境規制政策制定和區際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作用機理。為消減數據的異方差,對各變量取對數,借鑒吳勛和王杰⑨吳勛、王杰《財政分權、環境保護支出與霧霾污染》,《資源科學》2018年第4期,第854頁。的做法,并考慮到相關變量的滯后效應,初步構建了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i表示地區,t表示年份,Inin dtra it表示區際的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α0表示常數項,Inreg it-1為環境規制的滯后項,Infd it-1是財政分權的滯后項,而Inreg it-1×Infd it-1表示環境規制滯后項與財政分權滯后項的交互項,X 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地區勞動力成本、教育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u i表示個體異質性的截距項,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二)變量和數據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區際的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lnin dtra)。參考張彩云等的研究,剔除對自然資源依賴度較高的產業①張彩云、郭艷青《污染產業轉移能夠實現經濟和環境雙贏嗎?——基于環境規制視角的研究》,《財經研究》2015年第10期,第99頁。。因此,本文選用的污染密集型產業包括: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造紙及紙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燃氣生產和供應業、化學纖維制造業、化學原料和制品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造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主要方式為直接向發展中國家或落后地區的污染企業進行投資,以轉移本地區的污染密集型產業②鄒春艷《外商直接投資中污染密集產業轉移問題分析》,《皖西學院學報》2016年第6期,第85頁。。古冰和朱方明認為對地區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可反映區際間的產業轉移③古冰、朱方明《我國污染密集型產業區域轉移動機及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云南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第67頁。,借鑒其變量設定方法,本文選取地區污染密集型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的比重當作區際產業轉移變量。
2.解釋變量
(1)環境規制(reg)
針對每單位的污染密集型產業產值所征收的排污費能體現地區環境規制的強度,選取各地排污費收入占該地污染密集型產業產值的比重作為環境規制的代理變量,鑒于企業行為對政府政策反應的滯后性,選用環境規制的一階滯后項進行分析。
(2)財政分權(fd)
學術界常用各地財政支出占中央政府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衡量地區財政分權④徐永勝、喬寶云《財政分權度的衡量:理論及中國1985-2007年的經驗分析》,《經濟研究》2012年第10期,第7頁。,考慮到政策的滯后性,選用財政分權的一階滯后項進行分析。同時,引入財政分權與環境規制的交叉項,以探究財政分權下地方政府環境規制對區際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影響。
3.控制變量
勞動力、人力資本(以教育水平來衡量)以及經濟因素是企業進行區位選擇的重要考量因素⑤李存芳《可耗竭資源型企業轉移區位選擇行為的實證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第70-73頁。,因此,本文選擇如下的控制變量。
(1)勞動力成本(wage)。要素成本是企業生產的主要成本,在此主要考慮人力成本,用地區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表示,并使用平均實際工資指數對通貨膨脹進行修正,單位為元/人。
(2)教育水平(educ)。教育水平的提升既為企業提供優質勞動力,又會增強居民環保意識,能對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進入形成一種有效的阻力,用地區每十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數表示。
(3)經濟發展水平(y)。地區經濟發展狀況決定了潛在市場需求的大小及企業整體經濟環境,用地區實際人均收入水平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單位為元/人。

表1 地區環境規制與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聯合統計分布圖
本文主要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數據范圍為2000-2016年⑥由于最新的污染轉移數據只能在2017年年鑒中找到,因此,數據范圍為2000-2016年。,樣本為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⑦樣本不包括港、澳、臺地區,而且由于西藏相關統計數據不全,未將其納入樣本。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數據。為檢驗變量間可能存在的相關性,選取聯合統計分布進行分析。為了更直觀展示核心變量間的相關關系,根據各變量的三分位數將變量水平分為低、中、高三個等級。表1展示了地區環境規制與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聯合統計分布圖:在低水平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樣本中,高水平環境規制出現頻數最高(67次),而在高水平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樣本中,高水平環境規制出現的頻數最低(44次),這意味著地區環境規制水平與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存在負相關關系。
同時,表2給出了地區財政分權水平與環境規制水平的聯合統計分布關系:在低水平的財政分權組中,高水平環境規制出現的頻數最高(88次),而在高水平財政分權組中,低強度的環境規制出現的頻數最高(100次),這意味著地區財政分權程度和環境規制強度存在強烈的關聯性,并且財政分權程度愈高,該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就越寬松。

表2 地區財政分權水平與環境規制水平聯合統計分布圖
四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相關檢驗
1.面板平穩性檢驗
采用HT 方法檢驗各變量是否具有單位根,結果表明Inreg、Inregt-1、Infd、Infd t-1是平穩的,Inin dtra、Inwage、Inehuc、Iny是非零階單整,并且結果顯示所采用的變量均是一階單整,故可以繼續做實證分析。

表3 單位根檢驗
由于本文選取的變量全部使用未經差分處理的原變量,故在正式回歸分析之前采用Pedroni法對Inreg t-1、Inf d t-1、Inreg t-1×Infd t-1、Inwage、Ineduc、Iny與Inin dtra間可能存有的協整關系進行檢驗。F值為-8.0781,且p值為0,這表明變量間都是協整的,因此原序列可用于回歸分析。
2.格蘭杰因果檢驗
為判斷財政分權、環境規制與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之間是否存有因果關系,設置兩個假設:第一,環境規制(reg)是導致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in dtra)的因;第二,財政分權(fd)不是導致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indtra)的因。如果拒絕原假設,則說明財政分權和環境規制會導致區際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采用DH檢驗方法,得到變量間的因果檢驗結果。對假設1檢驗時,Z值為2.0151,p值為0.0439;對假設2檢驗時,Z值為-1.8919,p值為0.0585,這就意味著財政分權和環境規制均為區際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因。
3.內生性檢驗
變量內生性是引發估計偏誤的關鍵誘因之一,為避免內生性,采用Hausman檢驗對變量的內生性進行檢驗,lnreg、lnfd、lnedu和lny的統計量分別為7.37、5.15、7.21、3.65和7.88,但是均不顯著,因此可以初步斷定拒絕存在內生性的可能。內生經濟學的計量分析中經常將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如林季紅和劉瑩將環境規制一階滯后項當作工具變量檢驗其內生性①林季紅、劉瑩《內生的環境規制:“污染天堂假說”在中國的再檢驗》,《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1期,第14-15頁。,類似地,此處將選取變量的一階滯后項當作工具變量進行檢驗,結果表明選用的變量都不存在內生性。
(二)初步估計結果與分析
首先以混合回歸作為參考組,使用普通標準誤差和聚類穩健標準誤進行對比,結果發現二者之間存在差異,因此,假設擾動項獨立同分布的原假設不成立,混合回歸的估計結果也就不精確。隨之采用豪斯曼檢驗判定隨機效應模型(RE)和固定效應模型(FE)的適應性,得到豪斯曼檢驗值為16.010,且結果在5%水平下顯著,則認為應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用于分析后續實證結果。為了方便對比,將混合回歸和隨機效應模型的計量結果展示在表4中。

表4 初步回歸結果
表4固定效應(FE)模型(1)中環境規制滯后項的系數為0.018且不顯著,表明地方環境規制對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進入沒有顯著影響;財政分權滯后項的系數為0.426,說明地方財政權利的提升能加大污染密集型產業在該地的投資。該結論不符合實際情況,原因可能是忽略了地方政府財政分權對產業引進政策的影響,引發了估計偏誤。FE模型(2)的結果表明環境規制水平每提升1%,轉入該地的污染密集型產業將會降低大約0.179%,從而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加入環境規制滯后項對數與財政分權滯后項對數的交互項后,財政分權滯后項系數變得不顯著,而交互項的系數為0.166且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說明隨財政分權對區際污染密集型產業的轉移不產生直接影響,但隨著財政分權度的提升,地方政府將擁有足夠的空間出臺優惠政策以削弱環境規制對企業成本的影響,進而吸引污染密集型產業進入,這一結論驗證了本文的假設3。同時地區工資水平變量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污染密集型企業在選擇轉移地區時,工資水平是影響選址決策的重要因素,高工資水平將會抑制污染密集型產業進入。地區教育水平系數顯著為正,主要因為工人生產效率能有效提高企業競爭力,降低產品邊際成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不產生明顯效應,這可能是因為隨著地區開放度及交通便利度的提升,產地的產品流向各地銷售市場的運輸成本降低,本地市場效應及其經濟水平在企業選址決策中的作用逐步減弱。在表4中少量變量的系數不顯著,這可能是忽略空間相關性引發的估計偏誤,在后續分析中將使用空間計量方法再度估計。
(三)空間計量估計結果與分析
相關地理學理論認為事物間都存有一種普遍的聯系,并且相隔越近事物之間的這種相關性更強,面板空間計量模型較普通面板回歸能較好地把事物間的空間關聯性考慮在內。地方環境規制政策的制定存有明顯的策略互動性和空間關聯性,Yu等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空間外溢,即地區的經濟狀況不僅受本地區資源稟賦、要素投入等經濟因素的影響,還依賴鄰近地區相關經濟因素①Jihai Yu,Lung-fei Lee,“Convergence:A spatial dynamic panel data approach,”Global Journal of Economics 1,no.1(June 2012):1.。基于此,為驗證環境規制以及經濟發展是否存有空間溢出性,在回歸模型中加入環境規制和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滯后項,建立如下的空間杜賓模型:



表5 不同權重矩陣下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莫蘭指數
采用空間計量方法進行分析的首要條件是變量存在空間關聯性,為檢驗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空間關聯性,本文計算了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變量在不同權重矩陣下的莫蘭指數(結果見表5)。結果表明,在地理權重矩陣下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莫蘭指數為負,這可能是因為相鄰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環境規制水平等都具有較強的趨同性,故污染密集型產業會選擇較遠的區域進行轉移而不是就近擇址。這一結論與我國污染密集型產業逐步從東部省份轉移到中西部省份的現實基本吻合,并且其空間相關性具有增強的趨勢。然而,在經濟距離權重矩陣下,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莫蘭指數大于零,說明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地區其污染密集型產業分布也存在相似性,并且其相似性更明顯。
表6報告了地理距離和經濟距離兩類權重矩陣下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的結果,本部分將以模型(2)的回歸結果為準進行分析,當考慮各變量的空間相關性時主要得出以下結論。第一,與初步回歸結果相比,在兩類權重矩陣的回歸結果中模型(2)Inreg t-1×Infd t-1的系數均為正值,其系數分別為0.170和0.158,而財政分權滯后項系數變得不顯著,由此表明倘若考慮空間相關性,地區的財政分權度對區際間污染密集型產業沒有直接影響,而可能是通過出臺產業引進優惠政策來削弱環境規制強度對污染產業進入的阻礙作用。
第二,地理、經濟距離權重矩陣下,環境規制滯后項的系數分別為-0.213、-0.233(FE 模型(2)中環境規制滯后項的系數為-0.179),這意味著忽略空間相關性將低估地區環境規制對區際污染密集型產業進入的抑制作用。
第三,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滯后項系數表明,無論是地理鄰近還是經濟發展相似地區的經濟狀況對本地區污染密集產業的進入都沒有顯著影響,這從另一方面說明了本地經濟效應對企業選址決策中作用的弱化,以及由環境規制、工資水平等因素引發的生產成本效應的強化。
第四,環境規制空間滯后項回歸系數顯著大于零,表明相鄰區域以及經濟發展狀況相似區域的環境規制水平的提升將有利于本地區污染密集型產業的引入。原因在于地理鄰近或者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更為激烈,這類地區環境規制政策的變化將會對同類區域污染密集型產業的轉入或退出產生明顯作用。
最后,在地理距離權重矩陣下,空間自回歸系數為負(1%顯著性水平),在經濟距離權重矩陣下,空間自回歸系數為正(10%顯著性水平),說明污染密集型產業在選址決策中并不是一味地就近轉移,可能會偏好于選取地理距離較遠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結合區際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空間分布圖(圖未給出,如需要可聯系作者)可知,區際污染密集型企業正逐步從東部發達省區轉向中西部落后省區,污染密集型產業向四川、重慶、貴州、廣西等中西部省區集聚的趨勢明顯增強,這一結論驗證了本文的假設2。

表6 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
五 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主要結論
文章分析了2000-2016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基于地方政府間的競爭視角重新審視環境規制與區際間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相關關系,在納入空間相關性進行分析的情況下,分析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變化趨勢,探究地方間的競爭是否會影響環境政策的制定,及其競爭是否會間接影響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研究發現:(1)地區間不同的環境規制水平引發了污染密集型產業的區際轉移。(2)區際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具有顯著的空間相關性,且呈現出由東部省份轉向中西部省份、由發達省份轉向貧困省份的態勢;當考慮空間關聯性時,地方政府將通過出臺產業引進優惠政策來削弱環境規制強度對污染密集型產業進入的阻礙作用。(3)財政分權對區際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影響具有間接性,但是地方政府間競爭強度的增強會激發政府的自利性,地方政府財政分權度的提升顯著削弱了環境規制對污染密集型產業進入的抑制效應,即地方財政自主權的提升將會對生態治理產生負面影響。
(二)政策建議
第一,理性承接其他地區的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增強承接的拉力與環境承載力。中西部省份在承接東部省份的污染密集型產業時,要防止為提升地方政績而盲目引入;在承接污染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時,要衡量本地產業與承接產業的關聯性與耦合性,完善相應的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環境的承載力,地方政府在“筑巢引鳳”以提升地方營商環境的同時,要注重承接產業與本地產業的生態互動,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第二,構建具有彈性化的環境政策制定體系,加強地方政府環境策略和經濟目標的切合性。有必要采取彈性的環境規制策略,根據區域產業發展的實際特點有針對性地引進產業,補短板的同時也要注重加厚底板。注意結合產業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效果與長效作用,對污染密集型產業進行節點性與非均質化的環境規制,著力提升跨區域的環境協同治理能力,建立科學生態的政績考核機制。
第三,減少地方政府間的惡性競爭,在區域內部或者各區域之間構建具有優勢互補、產業協同的工業分布態勢。減少地區間因爭奪流動性資源而引發的盲目引入污染密集型產業的惡性競爭,避免因惡性競爭而導致的嚴重污染轉移問題。著力解決各地區工業發展存在的工業產業布局雷同的問題,出臺政策激發企業創新意識,提升其創新水平。著力在地區間布置具有協調性、優勢互補的產業,結合地區實際情況合理承接其他區域的污染密集型產業投資,從而緩解地區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結構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