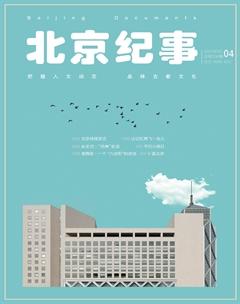電影院與藏書樓

說起紅樓電影院,老街舊鄰們總習慣將它的名字前面加上“西四”二字,于是“西四紅樓電影院”的故事也要從這座城市的一條老街——西四丁字街開始。
“死胡同”“丁字街”“斜街”“八道灣”……北京的地名總是那么形象且生動,顧名思義,這條街巷的走向一目了然。西四丁字街南通西單,北通西四、平安里,與東西走向的西安門大街交匯,“書寫”出一個形象的“丁”字。在這“橫與豎”的折角處,坐落著一座古樸的拐角小樓。
這座小樓東邊部分的主人便是紅樓電影院,而其前身則與這樓在當時給人的感覺一樣非常“時尚”,誰會想到,在上個世紀30年代,北京居然有家以臺球為主營業務的場所,因地而得名——紅樓球社。查過資料,方知是我孤陋寡聞了,光緒年間臺球運動便隨著“洋面孔”一同來到北京,最初落戶于東交民巷的“國際俱樂部”。此后伴隨著這項運動在上流社會的不斷普及,以臺球為主要經營對象的買賣家兒也如雨后春筍般在北京誕生。東安市場附近的會賢球房、大彰球房,前門外楊梅竹斜街的青云閣球社,還有之前提到位于西四丁字街的紅樓球社,都是當時著名的“北京臺球廳”。
1945年11月,伴隨著“產業轉型”,紅樓球社改為紅樓影院,體育產業正式轉為文化經營,正所謂引領當時文化藝術之先鋒。到了1956年,伴隨著公私合營的步伐,紅樓影院與民眾的距離更加親近,也成為了當時京城數一數二的觀影場所。
那是《霹靂貝貝》神奇的經歷,是《二子開店》的開懷一笑……因為童年的小學離紅樓影院不遠,所以學校歷次觀影均將那里作為首選。因為當時看場電影并不貴,也就一毛多錢,所以這也成為了家庭聚會的最佳場所,雖然當時影院的座椅均是木制,坐時間長了會很不舒服,但一家人仍舊沉浸在觀影的歡樂中。
記憶中,紅樓電影院完全是“現代化”裝潢的標志,紅色大理石的墻面上,還有四塊以《紅樓夢》人物圖案為主的藝術玻璃,一些門框立柱由木頭包裹,加之藝術設計的隔音門及現代感十足的展示窗,絕對是當時的“高大上”。最后一次與紅樓電影院的接觸是我與女朋友看的《天下無賊》,本來是一部馮小剛導演的賀歲喜劇作品,但女朋友卻在片尾階段哭得稀里嘩啦……
無論是“紅樓球社”還是“紅樓電影院”,均是以其所在地的紅色樓房特點而得名,談及建筑與記憶,還要提起這座樓房的另外一位主人——造寸服裝店。
其實準確地說,造寸應該是上海的一家老字號。創始人張兆春有著一雙巧手,上個世紀20年代在上海南京西路開創了屬于自己的買賣——張記裁縫店。因手藝過硬,又得上海愛美女性的追捧,名聲漸熱,恰與張愛玲結緣,便從才女之筆誕生“造寸”名號。1956年,正值新中國百廢待興,首都各方面產業急需注入新鮮血液之時。為了解決“做衣難”問題,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造寸與21家服裝店加入了支援首都建設的隊伍,入駐西四丁字街與紅樓電影院成為了鄰居。與眾多北京老字號一樣,造寸同樣以“前店后廠”的經營方式運營,延續在上海時的“成衣定制”模式。據資料,當時造寸正可謂高朋滿座,鄧穎超、蔡暢、康克清都曾選擇在造寸定制服裝。作為“老住戶”,造寸已伴西四丁字街60多載,除了“文革”時期短暫歇業,一直經營至今。
歲月更迭,一條老街、一座老樓,總會經歷著變化,也迎來發展,正如那樓體上滿處斑駁的印記,正如這座樓主人的命運發生的改變。
再次與紅樓電影院重逢,它已經告別了電影院的身份,變為了充滿書卷氣息的藏書樓,我興沖沖地成為了它的第一批讀者。曾經的電影放映廳被開辟為巨大的、由圖書環繞的世界,正應和了它如今的名字——紅樓公共藏書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