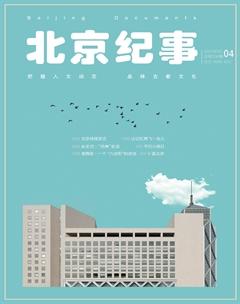永定河:“河神”史話
張源

在我國奢華的河流大家庭里,被封為“神”的河流寥若晨星,即使是享譽國內外的黃河,也不過落下個“河伯”的名分。而流長、流量和知名度都名落孫山的永定河,卻偏偏被尊奉為“神”。這個名號并非起自民間,金大定十九年(1179年),金世宗封其為“安平侯”;100年后,元世祖忽必烈又封為“顯應洪濟公”;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對永定河的尊崇達到頂點, 封為“ 河神”;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再次加封“安流廣惠永定河神”。
800年間, 三個朝代四位皇帝出手闊綽,心誠意篤地為一條河流賜鍍金身,實屬罕見。人們為了得到河神的眷顧,河神廟和龍王廟在兩岸蜂擁而建。這條從蒼涼、貧瘠的群山中沖決而來的河水,究竟沐浴著怎樣的神性光環,令諸多龍子龍孫如此頂禮膜拜呢?
“河神”之要:北京灣是河神的偉大杰作
依河而建、因河而興,似乎是世界各大都市繁盛的不二秘徑。人們常常喜形于色地歷數諸多光鮮經典:塞納河與巴黎、泰晤士河與倫敦、哈得孫河與紐約……然而,他們不知道在這份長長的榜單中,有一個重大疏漏——那就是永定河之于北京城。無須隱諱,就連今天的北京人,也大多并不明了永定河超乎時空的神性偉力。
故事的源頭萌芽在300萬年前,人類的胚胎尚在昏睡,永定河呼嘯的生命就已經風馳電掣了。她由今天的山西省寧武縣桑干河和內蒙古興和縣洋河,在河北省懷來縣匯合而成。然后裹帶著巨量黃土高原的泥沙,急不可耐地沖進太行山支脈(今北京西山)108公里的大峽谷。在遭遇一番撕心裂肺的搏殺后,好像跨越了一次生命輪回,便從今門頭溝三家店,氣定神閑地一腳踏進北京灣的門檻。那時的北京灣還是一片恣肆汪洋。數百萬年間,永定河像桑蠶吐絲一樣,把懷中的泥沙一點點鋪絮在河湖的床底。北京灣大平原就這樣漸露姿容,完成了“東控遼碣,北連朔漠,西接三晉,背負燕山,左擁太行,右瀕渤海”,那神性的最后一筆。
永定河以她粗糲的筆觸, 給北京帶來了人類最早的文明。其上游——在河北省張家口市陽原縣泥河灣,發現了40余處100萬年以上的古人類遺址,最早的接近200萬年,考古學家認為這里是東亞古人類的發祥地。而在北京境內,距今約20萬年舊石器時代中期的王平村人、11萬年前的桑峪人和距今約1萬年左右的東胡林人,都是沿永定河峽谷或其支流擇畔而居。考古學家賈蘭坡、黃慰文認為,上述早期人類的子孫后來逐漸順流而下,遷移到永定河出山口東西兩岸一帶,最后才來到北京平原。也就是說,北京人或許源自永定河畔。
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曾推想:來自中原腹地的最早一批先民,沿太行山東麓北上,試圖向更北方的蒙古高原或者松遼平原遷徙,不想,一條大河擋住了去路。而在河的對岸,從內蒙古高原或松遼平原一路奔波而下的另一群人,則正在和他們遙遙相望。侯仁之說,他們所站立的地方正是永定河兩岸。
這種推想不免有些戲劇化,不過,永定河是創造我國人類文明最早的圣地之一,是挽結南北,交匯東北、蒙古高原、中原三個文明區域的樞紐,已被無數遠古遺跡所證實。
在永定河的上游,今張家口涿鹿縣一帶是中華民族始祖黃帝、炎帝活動的重要地區。《史記·黃帝本紀》記載,標志中華民族形成的幾個重大事件:涿鹿之戰、阪泉之戰、合符釜山、建黃帝城都發生在這一帶。如果說,永定河曾養育了中華文明,恐怕不會有人反對。
在以后的歲月,又是永定河用乳汁般的河水哺育了北京城,在北京灣演繹出3000年建城史、850年建都史耀人的經典大片。而這一切,又為整個中國圈定了命運的基本走向。
需要添加一筆的是,北京的第一座城池薊城,是依蓮花池而建;遼、金建都毫不遲疑地也同樣選擇了蓮花池畔;此后,元、明兩朝的都城城址之所以向東北方向稍許飄移,蓋因那里有更為豐沛的玉泉山水系——不管是蓮花池,還是玉泉山水系,她們的水源無不來自永定河。
“河神”之愛:北京城在河神的搖籃中長大
歷史上,永定河像剛剛分娩的母親,乳水豐盈。北京城嬰兒般美美地吸吮了3000年。
無論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她鍥而不舍的腳步,潤澤著這座嗷嗷待哺的城市——玉泉山諸泉、昆明湖、長河、護城河、什剎海、北海、中南海、內外金水河、御河、積水潭、龍潭湖、蓮花河、高梁河等等,統統都是永定河的支系。而從戰國起直至明清時代,北京城內數以千計的水井也都直接或間接依靠永定河供水。幾千年來,哪個北京人不是喝著永定河水長大的?
時間追溯到三國時期,永定河上曾修建過北京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和車廂渠。這個水利工程效益最好的時候,可以灌溉北京周邊100余萬畝土地,前后使用了數百年。
永定河的神性并不僅限于那條嘩嘩歌唱的水流,她在西山開劈出的百公里大河谷,是北京灣連接東北、內蒙古、山西、陜西、河北乃至河南諸地區的生命通道。駝隊、馬隊、驢隊,人流、物流、文化流,伴隨著水響日夜不息。疊嶂的崇山峻嶺,無異于一個超級聚寶盆,這里沉睡著茂密的森林,永遠開采不盡的煤炭和各種建材。它們順流而下或是沿谷而行,北京城就像搭積木一樣,日益巍峨起來。北京人自遼代起,就學會了以煤炭取暖煮食,它們幾乎全部開采自西山。正是狹長的河谷讓這些烏金墨玉神奇地越過波峰深壑,走進千家萬戶。
北京一直是個缺糧城市,特別是成為都城后人口劇增。自從隋朝開通了大運河,南糧北運便是她最重要的使命之一。然而北京段的北運河沒有永定河向其注水,北京的糧庫將會出現囊中羞澀的尷尬。從金代開始,就有引永定河水入北運河濟漕運的記載;元、明以后,永定河的一派支流大致沿今涼水河河道,由東北轉東南流,至馬駒橋,過高古莊再轉東北流,在通州張家灣一帶匯入北運河。為運河增添運糧動力,對此永定河一直默默不語,人們吃糧時很難想到,這里竟有永定河一份不可輕慢的功勞。
如果沒有這條河谷,北京恐怕會是個瘦小枯干的城市。
“河神”之怒:天災與人禍
“河神”也曾“暴怒”過。
永定河每年7 至8 月為汛期,河水自官廳山峽急泄而下,兩岸峭壁林立,落差竟為320:1,最大流量5200 立方/ 秒左右。恍如從天而降的河水,挾帶年含量高達3120 萬噸的泥沙,不分青紅皂白地傾倒在北京灣。永定河的“暴怒”具有突發性強、洪峰尖陡等特點,讓人猝不及防,肝膽俱裂。北京最早的薊城,之所以選擇距永定河20里之外的“薊丘”高地,便是懾于其淫威。
誠然,永定河“暴怒”有大自然造次的成分,也有人類“自虐”。
那是一出超長的“ 自虐連續劇”,綿延數千年。
自從人類發現永定河,并視其為生命之河起,對她流域植被的砍伐和礦產的開掘,一度愈演愈烈。讓人百辨莫解的是,“自虐”竟然與人類文明的漸進并行不悖。
金元時期,因為戰爭、營建宮殿、發展漕運、城市取暖燒炭等需要,在永定河流域大規模林木砍伐一直沒有停止。金太宗天會十三年(1135 年),為了造戰船由海道入侵江南,調集兩路民夫40 萬人到永定河上游的蔚州(今河北省蔚縣)交牙山,“采木為筏”;到明代永樂年間營建北京城時,永定河以及北京周邊已經沒有大木可伐,破壞的范圍甚至波及到太行山另一側的山西一帶。從元到清,地處永定河上游流域的保安、宣府、蔚州、涿鹿、懷來、延慶等地的衛所,每年向宮廷輸送的木柴、木炭多達上萬斤——“大都出,西山兀”,這句古老的諺語讓人聽著不免心酸和心痛!
森林植被的嚴重破壞,使得越來越多的黃土被裹挾而下,而永定河也進入了歷史上最為渾濁、最為搖擺不定的時期,“無定河”之名迅速傳布開來,或者人們就干脆叫作“渾河”“小黃河”。 明萬歷皇帝朱翊鈞望著永定河無奈長嘆:“觀此水可知黃河矣!”此時的永定河已決然不是當初“清泉河”那樣一副小清新的模樣了。
史載,金代時永定河已是“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也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永定河變得張狂恣肆了。為確保京城安全,歷朝歷代都要絞盡腦汁整治永定河。據統計,800年間較大規模的治理共有53次,但是都以失敗告終。皇帝們之所以把永定河尊奉為“神”,全然出于恐懼和無奈罷了。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經過大規模治理后,河道相對穩定,為祈望這條大河永絕水患,康熙帝特賜名“永定河”,并沿用至今。
“河神”之治:綜合治理與生態修復
1954年,新中國剛剛誕生,就在河北省懷來縣永定河進京處,建設了規模浩大、總容量為41.6億立方米的官廳水庫,可防范千年一遇的大洪水。為支持水庫建設,當地10萬居民遷徙他鄉。那時,永定河還有20多億立方水量,北京人飲水、用水似乎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
然而,好景不長,噩耗便接踵而至,像是玩了個黑色幽默。
1997年,由于上游水質污染嚴重,官廳水庫被迫退出北京飲用水源序列。此后入庫水量逐年遞減,像是坐上陡然而降的過山車,2009年竟只有0.22億立方,相當于設計庫容量的千分之五。上世紀80年代,永定河三家店以下開始斷流。全長680公里的永定河,有500多公里長期無水。

永定河斷流之后, 中央相繼投入數百億元資金到永定河上游,支持當地節水和治污。山西、河北不可謂不努力,但是那么多人口要喝水吃飯,經濟也必須發展,所節約下來的水很快被新的需求吞噬殆盡。最終,上游用水不僅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出現了讓人哭笑不得、越治越沒水的怪狀。
讓永定河起死回生——是新世紀從中央到地方的共同奮斗祈愿。2016年12月國家發改委會同中央兩部局及四省市頒布了《永定河綜合治理與生態修復總體方案》,在上游實現全面生態補水,建設大型森林, 進行水土保持。2020年5月12日永定河北京段在時隔25年后,首次實現全線通水。
自然界的生態系統是各物種間,歷經億萬年共同演化的結晶,復雜而精巧。無論人類怎樣設計,都會有漏洞,且代價巨大。
既然修復已經啟動,人們心中就會升起期待的曙光。
永定河的神性不會消亡,她的未來屬于醒悟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