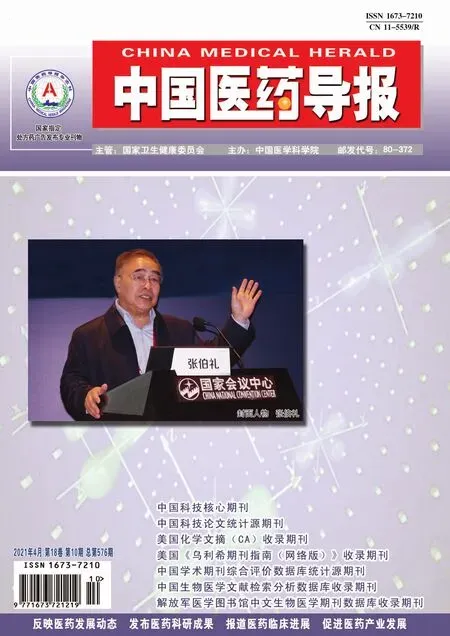基于數據挖掘分析補土醫派治療情志病的用藥規律
李昀熹 林婉兒 楊玲玲 鄭莉明 李 艷
1.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廣東廣州 510405;2.廣東省中醫院心理睡眠科,廣東廣州 510405
情志病是指在疾病的發生、發展、轉歸及防治過程中,精神、情志起關鍵作用并且患者以神志、情志異常為主要癥狀的一類病證[1]。情志病在中醫中可歸于“郁證”“狂證”“梅核氣”等范疇[2]。隨著當代醫學模式轉變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3],人類對心身健康的需要不斷增加。中醫學作為我國傳統醫學,對于情志疾病具有豐富的診療經驗[4],如《醫學傳心錄》曾言:“如有七情所干,寒暑所犯,則疾病生焉。”補土派以李東垣為代表,重視情志致病[5]。《脾胃論》言:“喜怒憂恐,損耗元氣。”近年有許多醫家將李東垣的理論思想應用于情志病的診療中[6-7]。隨著腦-腸軸理論的發現[8],現代醫學證實了胃腸與大腦、情緒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9]。故本研究對補土醫派醫著中治療情志病的方藥進行數據挖掘,分析其用藥規律,以期為中醫藥治療情志疾病擴展臨證思路。
1 資料與方法
1.1 處方來源
補土醫派以李杲為代表,有明確親炙私淑關系的醫家包括王好古、羅天益[10]。書目參照《中國中醫古籍總目》[11]和《中國醫籍大辭典》[12],不包括整理編校的他人著作、專病專著(痘疹、瘡瘍等)、本草類著作。本研究所納入的古籍包括《醫學發明》《活法機要》《蘭室秘藏》《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東垣試效方》《此事難知》《陰證略例》《醫壘元戎》《衛生寶鑒》。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將情志病定義為疾病的病因中情志起重要作用或疾病癥狀以情志異常為主要表現的病證[13]。②方藥明確的方劑。排除標準:①情志病表現不甚明顯的方劑。②方劑用藥品名、劑量不明確。
1.3 數據處理
根據上述納排標準進行方劑篩選,舍去加減方,提取數據,采用“雙人雙錄”的方式,利用Excel 2016建立補土醫派情志病處方數據庫。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14]和《中藥學》[15]進行規范化處理,如白茯苓→茯苓、玄胡→延胡索等。在統計過程中炮制品予以分別統計,如生甘草、炙甘草等。
1.4 統計分析
對中藥數據庫中中藥使用頻次、四氣五味之屬性、歸經進行頻次、頻數統計,使用SPSS 22.0對高頻中藥行聚類分析,并在提取公因子后進行因子分析。
2 結果
最終獲得中藥處方126條,共156味中藥,總用藥頻次為1100次。
2.1 單味中藥的使用
在126首方劑中,使用頻次≥5的藥物依據頻次從高到低進行排序,共有56種、917次。使用頻數最高的5味中藥是人參、當歸、炙甘草、甘草、柴胡,使用頻數≥20的單味中藥信息見表1。

表1 使用頻數≥20的單味中藥
2.2 中藥屬性統計
2.2.1 藥物功效 依據《中藥學》[15]對使用頻數≥5的中藥進行藥物功效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共有15種功效,使用頻數最多的功效是補虛藥,其次是解表藥和清熱藥。見圖1。

圖1 藥物功效統計
2.2.2 藥物藥性、藥味 對高頻藥物(使用頻數≥5)的藥性、藥味進行統計,同一味中藥的多個藥性、藥味分別統計。在56味中藥里,累計出現917次藥性、1553次藥味。結果顯示,藥性以溫、寒最為常見,藥味以辛、甘、苦居多。見圖2。

圖2 藥物藥性與藥味統計
2.2.3 藥物歸經 對高頻藥物(使用頻數≥5)進行藥物歸經統計分析,若同一中藥具有不同歸經,則分別統計。在56味中藥里,累計出現2993次歸經,其中脾經、肺經、心經、胃經最為常見。見圖3。

圖3 藥物歸經統計
2.3 高頻藥物因子分析
以高頻藥物(使用頻數≥15)作為因子分析對象,KMO檢驗統計量0.570>0.5,Bartlett球型檢驗χ2值為811.335(自由度為276),P <0.0001,提示數據可進行因子分析。使用最大方差法旋轉,提取得到9個公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8.007%,通過高頻藥物的旋轉成分矩陣,最終確定9個公因子中包含的藥物組合。見表2。

表2 高頻藥物的公因子分析
2.4 高頻藥物系統聚類分析
選取高頻藥物(使用頻數≥15),應用SPSS 22.0進行系統聚類分析,采用組間聯接方法,共得到6類藥物組合。類1:防風、羌活、川芎;類2:炙甘草、白芍;類3:陳皮、半夏、當歸、柴胡、升麻、黃柏、黃芪、蒼術、甘草;類4:干姜、附子、肉桂、茯苓、白術、人參;類5:黃芩、黃連、生地黃;類6:大黃。見圖4。

圖4 高頻中藥聚類分析樹狀圖
3 討論
3.1 虛則補益脾胃元氣
分析補土醫派治療情志病時所用單味藥物,人參、當歸、炙甘草頻率最高,在功效上以補虛藥為首,藥味以甘、溫之性為主,歸經上則以脾經、胃經為主。因子分析發現,人參-茯苓-白術、干姜-肉桂-附子為重要因子。聚類分析發現,干姜、附子、肉桂、茯苓、白術、人參為核心藥物組合。上述藥物均以甘、溫入脾胃經為特點,病機上不良情志損害脾胃元氣,脾胃受損后又難以化生思慮的所需物質基礎,最終相互為害,形成情志疾病[16]。故在治療上,首重補助脾胃元氣,如《脾胃論·安養心神調治脾胃論》中所說:“善治斯疾者,惟在調和脾胃,使心無凝滯……蓋胃中元氣得舒伸故也。”
3.2 實則瀉其火
從用藥規律可發現,高頻藥物中有生甘草,常用藥物藥性、藥味中分別有苦味、寒性,用以涼降,功效頻率上清熱藥僅次于補虛藥、解表藥,而因子分析發現黃芩-黃連-大黃、生地黃兩組清熱藥物,提示瀉火治則可用于實證類情志病[17],同時可用在以心煩、情緒煩躁為主的情志病中[18]。
3.3 重升發脾胃陽氣
單味藥統計發現,柴胡是高頻藥物,在功效統計中發現,解表藥是高頻功效之一。辛味在藥味中排名處于首位,關聯分析發現防風、羌活是重要藥對,因子分析中防風、羌活、川芎是公因子之一。以上均說明補土派醫家在治療情志病中注重以風藥升發脾胃陽氣,更能以風藥開肝氣郁滯,達到條暢情志之目的[19-21]。
3.4 補脾胃,升清陽,瀉陰火
因子分析中的藥物組合當歸、甘草、柴胡、黃芪、升麻、黃柏、蒼術,聚類分析中的藥物組合陳皮、半夏、當歸、柴胡、升麻、黃柏、黃芪、蒼術、甘草,均可劃分為補脾胃、升發脾胃陽氣及降瀉陰火的藥物。在方劑上與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相似,可用于虛實夾雜之情志病,一方面以虛證為主,表現為“不樂”“短氣”;一方面以實證為主,表現為“心煩”等,如《脾胃論》中所載情志表現“身心煩亂,有不樂生之意,情思慘凄”。治則上應結合李東垣之陰火治則[22],補脾胃,升清陽,瀉陰火并舉[23-24]。
綜上,補土醫家在情志疾病的治療中,虛者注重補益脾胃,實則瀉其火,且注重升發脾胃陽氣,病程長而虛實夾雜,情志表現多端又可秉承李東垣所創立的陰火治則,補脾胃與瀉陰火、升清陽三者相合,與當下情志病證的診療相比[25],突出了脾在情志病中的作用,為中醫辨治神志病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