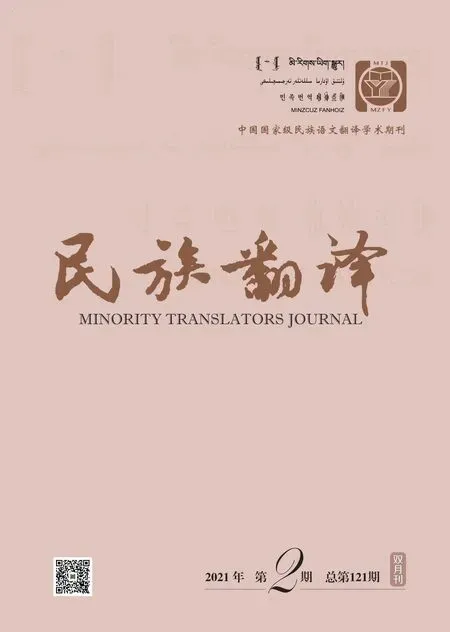《蒙古風俗鑒》原稿本、批注本及譯本考異*
⊙ 紅 梅 黑 龍
(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甘肅 蘭州 730000;大連民族大學民族史研究所,遼寧 大連 116605)
《蒙古風俗鑒》是近代蒙古族杰出學者、思想家羅卜藏全丹①所著蒙古族民俗學經典著作,有蒙古文和漢文兩個版本,蒙古文成書于1918年,漢文版成書時間是1919年。也就是說,《蒙古風俗鑒》有蒙古文、漢文兩個原稿本。著名民俗學家哈·丹碧扎拉桑將《蒙古風俗鑒》蒙古文原稿本進行整理并以蒙古文批注(以下簡稱“丹碧批注本”),該批注本于1981年正式出版后,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并被蘇聯、美國、日本、德國、蒙古國等多個國家翻譯出版。目前,國內出版的漢譯本有兩種:一種是趙景陽譯《蒙古風俗鑒》(1988年);一種是那日薩譯注的《〈蒙古風俗鑒〉新譯詳注》(2019年)。
一、《蒙古風俗鑒》版本流變情況
《蒙古風俗鑒》一書全方位、立體式地展現了清朝統治下的蒙古地區,尤其是以卓索圖盟為核心的內蒙古東部地區民俗文化及社會景象。民俗學界公認1918年北京大學歌謠征集活動為中國現代民俗學的肇始。而同一年寫成的《蒙古風俗鑒》蒙古文原稿本在檔案館塵封六十多年后被發現,并得以正式出版,為學界之幸事。[1]譯序1《蒙古風俗鑒》共10冊,除民俗外,還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宗教、法律、地理、教育、文學、藝術等領域,故有近代蒙古社會的百科全書之譽,被認為是現代學術意義上的蒙古民俗學開山之作,頗受學界青睞。

新中國成立以后,《蒙古風俗鑒》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1960年,吐旺道爾吉受內蒙古歷史研究所委派,歷時一年多,從大連圖書館將《蒙古風俗鑒》蒙古文原稿完整地抄錄了下來。這是內蒙古地區最早的一部《蒙古風俗鑒》蒙古文原稿本之抄錄本,收藏于當時的內蒙古歷史研究所。之后,內蒙古語言文學研究所、內蒙古圖書館各抄錄一本,但錯誤較多。[3]
至1981年,著名民俗學家哈·丹碧扎拉桑整理、批注的《蒙古風俗鑒》(蒙古文版,以下稱丹碧批注本)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丹碧批注本首次向公眾揭開了《蒙古風俗鑒》的神秘面紗,從而掀起了研究《蒙古風俗鑒》及其作者的熱潮。遺憾的是該批注本中未說明最初的抄錄者信息和來源,也未交代具體以哪個抄本為底本,并且哈·丹碧扎拉桑也不是第一手抄錄者,導致該批注本存在諸多問題。
自丹碧批注本出版后,有不少人熱心于羅卜藏全丹及其著作的研究,但又苦于不懂蒙古文,于是漢譯本應運而生。丹碧批注本的趙景陽漢譯本于1988年由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是國內第一部漢譯本。可由于趙景陽未能參考原稿,且蒙古文水平有限,導致譯本中出現了諸多漏譯或錯譯。
2019年,那日薩漢文譯注版《〈蒙古風俗鑒〉新譯詳注》由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該譯本以大連圖書館所藏羅卜藏全丹蒙古文原稿本為底本進行翻譯,更正了原稿中的史料性錯訛,并做了諸多注釋,為譯文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提供了方便。
綜上所述,《蒙古風俗鑒》除了蒙古文和漢文原稿本外,還有三部蒙古文手抄本、一部蒙古文批注本及兩部漢譯本,共8個版本流傳。學術界較早開始關注《蒙古風俗鑒》的作者、版本及內容,也收獲了一些整理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前人未能掌握《蒙古風俗鑒》原稿本,故而出現了不少以訛傳訛現象。近年來,筆者有幸閱讀了《蒙古風俗鑒》蒙古文、漢文原稿本和那日薩漢譯本,擬進一步研究這部民俗學經典文獻,以便增進學術界對該文獻的了解、提高其參考利用價值。
二、《蒙古風俗鑒》蒙古文、漢文原稿本與丹碧批注本之比較
《蒙古風俗鑒》的最初抄錄者是內蒙古歷史研究所吐旺道爾吉先生。1981年哈·丹碧扎拉桑整理、批注出版《蒙古風俗鑒》,但他沒有說明最初抄錄者和版本來源。據那日薩教授分析,丹碧批注本可能是以吐旺道爾吉抄本為底本。但由于是轉抄本,該批注本與原稿本有明顯的出入。現將該書蒙古文、漢文原稿本與丹碧批注本比較如下:

表1 羅卜藏全丹蒙古文、漢文原稿本與丹碧批注本篇章之比較②

續表

續表
從表1可以看出,羅卜藏全丹漢文原稿本共61篇,有序言,無自傳。由于漢文原稿本目錄與蒙古文原稿本目錄存在差異,而且漢文原稿本內容殘缺,故無法在此進行詳細比較。蒙古文原稿本共10冊61篇,并有序言和作者自傳2篇。丹碧批注本共10冊58篇,并有序言和跋語2篇。蒙古文原稿本中的作者自傳在丹碧批注本中被跋語代替。此外,丹碧批注本還有一些抄錄遺漏和錯誤、改動篇名等問題。列舉如下:





此外,蒙古文原稿本第48篇中用漢字標注的地方機構名稱“八溝廳”,即八溝廳,在丹碧批注本誤抄為“八蒲廳”;蒙古文原稿本第50篇中論述疾病治療、祛除小孩驚厥的內容用漢字標注了“潑水收驚”,即潑水收驚的繁體字,在丹碧批注本誤抄為“潑水收敬馬”。[1]譯序3-4這些拆分、合并和誤寫現象充分說明丹碧批注本并非以羅卜藏全丹原稿本作為底本。
三、趙景陽漢譯本與那日薩漢譯本之比較③
1988年,趙景陽以丹碧批注本為底本翻譯的《蒙古風俗鑒》漢譯本由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在信息技術還不發達的年代,趙景陽在丹碧批注本出版7年后便將進行漢譯,說明他有敏銳的學術意識。可是趙景陽對蒙古文的把握程度不夠精準,同時蒙古族歷史及佛教知識等基礎不夠扎實,導致漢譯本中出現了大量的特色詞匯和文化負載詞語錯譯現象。相比而言,那日薩譯本基于大連圖書館館藏的羅卜藏全丹原稿本,在翻譯過程中準確傳達了作者的原意,翻譯和注釋均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舉例如下:
1. t?bed-un oron-du sura?zin cambuva qaγan……[4]7
“t?bed”指藏、西藏,這里指吐蕃。“oron”這里指區域、地方。“sura?zin cambuva”為吐蕃國君,7世紀初期之人。“qaγan”指可汗。此句意為“吐蕃地區松贊干布可汗”。
(1)趙景陽譯本:“藏地松贊干布”[5]2
(2)那日薩譯本:“吐蕃之松贊干布汗”[1]7
松贊干布是吐蕃王朝第33任贊普,是吐蕃王朝立國之君,其在位時間是公元629—650年間。而“西藏”這一名稱是從清朝康熙年間起稱至今。所以,趙景陽譯本中翻譯為“藏地”,顯然欠妥。

(1)趙景陽譯本:“這個寶日吉黑日族是古印度皇之源流”[5]3
1.3統計學方法研究所得兩組治療前后VAS、ODI評分情況均屬于計量資料,經±s表示;兩組不良反應屬于計數資料,經n(%)表示,數據傳入SPSS.19軟件并實施相應檢驗(t、X2),若P<0.05則提示相關數據差異存統計學意義。
(2)那日薩譯本:“孛兒只斤世族是古印度地域鄂蘭納·額爾古克德克森汗之源流”[1]8
比較兩種譯本可以看出,趙景陽譯本過于籠統,沒有具體說出哪一位可汗,并且未規范使用“孛兒只斤氏族”這一稱謂。
3. ……qobilai secˇen-i dayan ulus-un qaγan ergübei[4]16
“qobilai secˇen”為人名,即忽必烈,元朝開國皇帝。“dayan ulus”為大元國。“qaγan”為可汗。“ergübei”有舉、抬、托、獻、供、奉、照顧、侍奉、抱養、抬高、抬舉等意,這里指奉為。這段話表示“忽必烈薛禪被奉為大元國的可汗”。
(1)趙景陽譯本:“……忽必烈斯欽被封為大雁國汗。”[5]8
(2)那日薩譯本:“忽必烈薛禪封為大元國之汗”[1]16。
趙景陽譯本中把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國翻譯為“大雁國”,可以看出譯者是按照原文內容進行了音譯,這種譯法顯然脫離了歷史的本真。另外,忽必烈的尊號為“薛禪汗”,“薛禪”不應譯寫為“斯欽”。

(1)趙景陽譯本:“在恰各圖、大庫倫等地建房”[5]132。
(2)那日薩譯本:“在恰克圖、大庫倫等地簽訂協約”[1]220
趙景陽譯本在翻譯過程中顯然理解錯了原文的意思,將“ger”與“ger_e”相混淆。“ger”是房、舍、氈包。而“ger_e”為契約、合同。


(1)趙景陽譯本:“到了四月峽谷內不會有浮物了”[5]152。
(2)那日薩譯本:“進入四月,帽纓不再吹飛”[1]257。



(1)趙景陽譯本:“三年進行一次人口登記,把各戶的男人都寫在盟的專用冊子上。”[5]17
(2)那日薩譯本:“自古蒙古部落每三年將家庭男子人口數及名字錄入比丁會盟衙門檔冊之上,稱其為‘填丁’。”[1]36
趙景陽譯本中,與清朝戶籍制度相關的“比丁會盟”“填丁”等詞語未進行翻譯。將“比丁冊”籠統得譯為“專用冊子”,導致未能正確傳達作者的原意。


(1)趙景陽譯本:“在翻譯詩詞時,要對好蒙文的字頭”。[5]73
(2)那日薩譯本:“單就詩句翻譯而言,以蒙古文字母押頭韻的規則來翻譯”[1]135。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丹碧批注本第157~159頁的6首詩趙景陽譯本全部漏譯(該6首詩的翻譯見那日薩譯本第135~136頁),這是趙景陽譯本的重大失誤。趙景陽在對其他篇章進行翻譯時也出現了許多文字信息的遺漏,在此不一一指出。


(1)趙景陽譯本:“佛,(譯者注:此佛指釋伽牟尼)出生在印度皇帝之家,是索瓦達尼之子。因而,那里僧侶特多,廣建了寺廟。”[5]73
(2)那日薩譯本:“佛陀本為印度地區首圖馱那國王之子,他大力發展佛教事業,創建眾多塔寺。”[1]137
趙景陽譯本將釋伽牟尼的父親名字“首圖馱那”錯譯為“索瓦達尼”,“大力發展佛教事業”錯譯為“那里僧侶眾多”。
綜上所述,趙景陽譯本對細節的處理、歷史知識的掌握和運用方面較欠缺,甚至對于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地名等需采用通用名稱的地方出現了誤譯或不譯,嚴重影響了譯文讀者對《蒙古風俗鑒》內容的認知。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蒙古風俗鑒》涉及的知識面廣泛,翻譯難度較高。那日薩譯本基于大連圖書館藏羅卜藏全丹蒙古文原稿本進行翻譯,所以避免了翻譯抄本所帶來的錯訛。其次,那日薩譯本在歷史知識的把握上很到位。對此,北京大學陳崗龍教授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蒙古風俗鑒〉新譯詳注》直接根據大連圖書館藏羅卜藏全丹《蒙古風俗鑒》原稿為底本,忠實準確翻譯并作了大量的學術注釋,因此具有很高的翻譯價值、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是羅卜藏全丹研究和《蒙古風俗鑒》研究中的一個新的里程碑。《〈蒙古風俗鑒〉新譯詳注》翻譯文字精準流暢,是一部花了很大功夫并見深厚功底的譯著。是非蒙古語的讀者和學者研究和理解《蒙古風俗鑒》的可靠的科學翻譯本。同時,本書第一次公布了羅卜藏全丹的珍貴照片,讓我們第一次親眼目睹一百年前撰寫《蒙古風俗鑒》為啟蒙蒙古民族而苦苦奮斗的思想家羅卜藏全丹的風貌。”[6]此外,那日薩譯本中有三處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進行了大量的學術注釋,其中不乏多處對原稿內容錯誤之處的更正;二是第一次向世人公開了原稿作者羅卜藏全丹的照片;三是“羅卜藏全丹”名字的漢文寫法歷來不統一,那日薩譯本根據在日本找到的羅卜藏全丹照片上的署名及羅卜藏全丹在日履歷表上的署名,確定了其正確的寫法。
注釋:
①羅卜藏全丹名字的漢文寫法歷來不統一,有“羅卜桑愨丹”“羅布桑卻丹”等寫法。那日薩譯本根據在日本找到的羅卜藏全丹照片上的署名及羅卜藏全丹在日履歷表上的署名,確定了其正確的寫法。
②表1中羅卜藏全丹蒙古文、漢文原稿本目錄由那日薩教授提供。
③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大連理工大學那日薩教授的幫助和指導,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