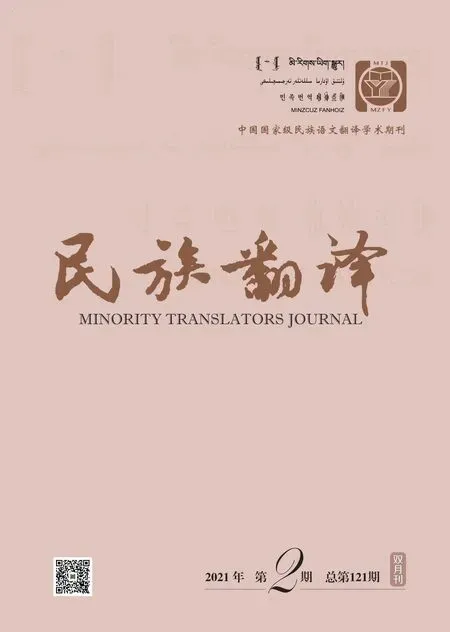從“VP了的時候”管窺《清文指要》中的直譯現象*
⊙ 王曉艷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北京 100089)
一般認為,元代的翻譯文獻中存在直譯體。亦鄰真、祖生利等把出現于元廷廟議記錄、圣旨、文件、令旨等公牘中的詞句奇特、句法乖戾的文體稱為“硬譯文體”,這種文體語言不符合漢語中的語法規律和用語習慣,翻譯比較機械。[1-2]因此前人的研究多將目光聚焦于元代的翻譯文獻中,實際上隨后清代出現的滿漢合璧文獻中也出現了直譯體翻譯方式。竹越孝梳理了蒙漢、滿漢對譯文獻中的部分直譯現象,認為元、明、清三代的直譯體體現了原文(蒙文或滿文)的優越性。[3]該文雖論及清代滿漢合璧文獻材料,但主要是強調滿語教材的價值,對于直譯現象的舉例較少。
基于以上語言事實,本文選用滿漢合璧《清文指要》為研究語料,通過對“VP了的時候”結構的考察探討以下問題:
1.翔實分析《清文指要》中“VP了的時候”結構,并進行量化處理。采用滿漢對勘方式,明確滿語文與漢語文的對應關系,直觀呈現文獻的直譯性特征。
2.試圖從語言本體、譯者和譯策三個角度分析《清文指要》出現直譯現象的原因,以期從翻譯學的角度,豐富歷時維度直譯體翻譯表現的材料,并推動滿漢語言接觸及旗人漢語的研究。
一、“VP了的時候”直譯表現
清定鼎中原之后,尤其是乾隆時期,滿族逐漸漢化,出現了復合雙語現象,滿人母語水平逐漸磨蝕,漢語逐漸成為其日常生活中的第一語言。清政府為了鼓勵滿洲旗人積極學習滿族文化和滿語,開始倡導“國語騎射”運動(乾隆十八年),并將其視為“滿洲根本”“旗人要務”。為順應學習要求,出現了一批滿漢合璧教科書,《清文指要》就是其一。該書反映了清代雙語教學的真實情況,明確闡述了編纂的目的及重要性:“今敘明初學清文少年,應知數語,以便講習”“清話呀,是咱們頭等頭要緊的事,就像漢人們各處的鄉談一樣”②,即教授母語生疏的旗人學習滿語及滿漢翻譯。《清文指要》漢語部分口語化程度較高、影響范圍廣,之后被外國人編寫的北京話教材引用、改編。張美蘭、綦晉比較了不同時期的修訂版,強調三槐堂版本的《清文指要》漢語部分比較忠實滿語原文,帶有“硬譯”的痕跡。[4]
《清文指要》中“VP了的時候”共出現28例,大多數例句不符合現代漢語的語法語用規范,顯得佶屈聱牙。如:
(1)俊俏年青的人,系上一副俏皮撒袋馬騎上了的時候,才能出眾的年輕人,少年仰著臉兒就像鶯一樣的呀。(96-2-1)③
(2)把這話就通知咱們來的太太們,瞧了姑娘的時候,把阿哥也叫進去,給這里的太太們瞧瞧。(68-3-2)③
(3)這一次饒過了的時候,就說是改了嗎?也不過減等著喝一兩日罷咧,過去了又是照舊的喝啊。(60-3-6)③
(4)多咱你遇見一個狠刻薄的人,磞了丁子了的時候,你才說:哎喲,原來這樣的利害呀啊。(96-2-1)③
以上例句中“VP了的時候”主要表示時間性用法(例1、2)和假設性用法(例3、4),時間性用法表示“的時候”“之后”,假設性用法可替換為“(要是)……的話”。以上例句中“VP了的時候”,尤其是“了”的使用看起來顯得生硬,經過對滿語文本的逐一分析,總結“了的時候”滿語對應成分如表1。從表1可以看出,“了的時候”與滿語成分的對應具有高度一致性與對等性。

表1 “了的時候”滿語對應成分匯總表
(一)“VP了的時候”中“了”與滿語對譯分析
從“了”對譯滿語成分來看,主要為副動詞詞綴及時體標記。副動詞是由動詞詞干加上詞綴構成,“了”緊跟動詞之后,主要對應順序副動詞詞綴-fi和直至副動詞詞綴-tolo,用來表示行為動作的終結或持續,如下例(5)表示“遇見”的完成義,例(6)中“了”輔助“到”表示“直至、盡”之意。時體標記主要用來說明動作行為發生的時間,如例(7)(8)表示動作“過去”“悮”引導的事件分別發生在過去和將來。
(5)遇見了各樣的事情了的時候,斟酌了又斟酌,得了主意了,再說人的不是,人也服啊。(66-2-4)③(“了”對應順序副動詞詞綴)


(6)后來客們將散了,我就放了一個枕頭,穿著衣裳,把頭一倒竟自睡熟了,到了第二更的時候才醒了。③(87-2-3)(“了”對應直至副動詞詞綴)


(7)過去了的時候,又想著可怎么樣呢?實在的殺他嗎?③(84-3-2)(“了”對應一般過去時)


(8)要是拘擬舊規矩,“旗桿底下悮了操”,睜著眼睛至于悮了的時候,什么趣兒呢?③(64-3-3)(“了”對應現在將來時)


《清文指要》中用時態助詞“了”對譯特定的滿語成分來表明情狀發生的時間和情態,這些“了”與“VP”結合,形成復雜的長定語結構“V了”。祖生利提出,滿語中過去式形動詞和動名詞基本用旗人漢語“V了的”來對應,這種語言對譯模式在蒙式漢語中早已出現,元代的直譯體文獻中“了”是重要的時體標記,常用來對譯蒙古語動詞、助動詞過去時的后綴成分,如-ba、-be、-bai、-bei等。[5]“了”還可以與時標記“有、來、也”組合表示完成,如“了有、了來、了也”等。[6-7]曹廣順、祖生利認為導致蒙古語出現直譯方式的原因,主要是受到蒙古語和漢語的雙重影響,譯者傾向于將雙語中語法功能、句法位置及語音相似的語法語素直接匹配,以求語法成分在功能、語義等方面的對等。[7-8]
(二)“VP了的時候”中“的時候”滿語對譯分析
“VP了的時候”結構中表示“的時候”對應位格de及后置詞manggi、jakade。de是滿語位格標記之一,可譯為“的時候”用來指示時間,如例(9)。后置詞manggi表示“已然”,用在一般過去時的形動詞之后,表示事件發生的非同時性,如例(10)表示“翻過來了之后”。后置詞jakade“較de字詞義實在”[9]238,用法同manggi,也表示“……之后”,如例(11)。
(9)把緣故從頭至尾分晰明白了的時候,怕把你怎么樣嗎?③(97-1-5)


(10)合上了里面續上了棉花,翻過來了的時候,你縫大襟,我就行。③(64-1-5)


(11)我說這想必是存住食了罷,吃了一服打藥的時候,把好歹的東西全打下來了。③(87-3-5)



漢語屬于漢藏語系,主要利用虛詞和語序作為表達手段,大多一個詞為一個語素;滿語屬于阿爾泰語系,主要通過添加后綴成分派生詞和變化詞性,多個黏合附加成分表示多重語法意義。在滿漢直譯過程中,滿語中多個語素通常對應漢語的幾個詞,這種翻譯方式增加了“VP了的時候”結構的使用頻率。雖然直譯能幫助習得者盡快熟悉滿語語義與語法結構,但是這種機械的雙語對應形式,造成了翻譯文體用清代漢語口語詞匯套用滿語的語法現象。因此出現了不做變通、拘泥于滿語語法格式的不符合漢語語法規范的用法,造成了語義的模糊,反映了直譯的局限性。
二、直譯體原因探究
學術界一般將滿漢對勘文獻中的特殊語法現象歸因于滿語的干擾。張美蘭、綦晉指出,《清文指要》所處乾隆時期是滿漢語言接觸的加深階段,因此《清文指要》中的語言接觸特征更為凸顯,隨著滿語文的逐漸衰落,這些顯著的滿語干擾特征也就逐漸減少至殆盡。[4]不可否認,滿語干擾是形成滿漢文獻文本特殊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編寫教材中,譯者所處的社會因素的影響、譯者對翻譯的考量以及對教科書翻譯策略的選擇也應被考慮在內。
(一)語言分析:滿語干擾及規約化翻譯
《清文指要》中“VP(了)的時候”在語言接觸過程中受到滿語干擾因素的影響。劉曼、張美蘭、祖生利在探究滿語干擾影響時指出,“的時候”表示假設性的特殊用法是帶有滿語特征的漢語表達。[5,10]王曉艷《在從滿漢對勘看〈清文指要〉中“VP(了)的時候”的句法語義特征》一文詳細分析了“VP(了)的時候”滿語成分,認為其句法語義特殊性與滿語成分具有一致性。[11]經過滿漢對勘,我們發現,“VP了的時候”與滿語語素大體呈一一對應的關系,這是典型的經由翻譯所導致的語言接觸現象。其原因主要源于早期京旗滿人對漢語的不完全習得,其后學習者將二語學習中習得的“暫時的”錯誤或者干擾特征引入目的語中,經過頻繁的使用,逐漸規約化(conventional)、固化(stabilization)成為二語習得甚至民族方言變體的一部分,并傳給八旗子弟。規約化翻譯現象在滿語語法書中也有體現,例如《清文啟蒙·清文助語虛字》中對manggi(了的時候、了之后)有如下釋義:
oho manggi 了之后。作了之后。
bihe manggi 有來著之后。在來著之后。
sehe manggi 說了之后。
ki sehe manggi 欲要之后。
oso manggi 既而。既令作之后。
se manggi 既說教令之后。[9]275
以上“了之后”“來著之后”“說了之后”等句的性質與《元朝秘史》旁譯相同,是滿語的直譯形式。祖生利認為,這種受到滿語干擾的直譯形式不僅體現在文獻中,還很有可能是對當時漢語實際情形的反映,像“(的)上/上頭”“有”“來著”的使用亦如此。[5]祖生利[5]、王繼紅⑥稱這種從滿語原文機械翻譯而來、不符合漢語固有的語法規范和用語習慣的“滿漢混合式”語言為旗人漢語,類同于元代的漢兒言語。
(二)譯者分析:直譯思維的固化
筆帖式(滿文為bithesi)是清代特有的官職設置,源于清入關前的“巴克什”或“巴可克什”,天聰五年金設六部將其改稱為“筆帖式”[12]。滿文稱筆帖式為“筆特赫式(或筆特和式)”,意為“文書、士人”。清入關后,政務、文書急劇增加,因此亟需通曉滿漢雙語者翻譯奏章文籍。筆帖式職掌事務繁多,因朝廷公務的需要逐漸主職滿蒙漢文的互譯,謄寫奏章文書。《清朝通志》提到“凡翻譯繕寫奏章,……俱筆帖式執掌”⑤。
清初官職各部門以滿人為正職,漢人為副職。且清代權貴雖為滿族,但是漢人官員較多,在頒布詔令制敕、題本等文件時多采用滿漢合璧形式,其余文書單用滿文或漢文,因此筆帖式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譯漢文或者滿文公文,服務于統治階級和貴族。公文文體較為規范,一般傳達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旨意或重要信息,為了防止誤譯或者改變原意,筆帖式傾向于盡量保持公文的原貌,采取直譯的方式將改動降到最低。長此以往,筆帖式形成一套規律性的翻譯方式,可以迅速、圓滑地行移公文。除了公文外,筆帖式還為上層統治階級翻譯漢文書籍、編寫滿語教科書以推動滿族政治軍事發展及“清語”的學習。受到翻譯公文潛移默化的影響,筆帖式在翻譯此類文體文獻時,也會利用直譯方式幫助讀者理解原文結構與意義。
(三)譯策分析:教科書翻譯的要求
《清文指要》是滿清統治者和一些滿族有識之士為加強滿語教育和提高滿漢翻譯水平而刊行的滿漢對勘教科書。對于教科書而言,翻譯方式的選擇尤為重要。一般教科書的翻譯通常利用意譯和直譯兩種方式,這兩種方式沒有高低優劣之分,“直譯以達意,意譯以求直”[13]。
意譯的翻譯方式有助于習得者對原文信息的理解,但其語言形式與原文迥異,拉大了句子結構與原文的差別,過度的闡釋也會使譯文失去原文的韻味,不利于習得者理解滿語的語法成分。因此用意譯對教科書釋義是有局限性的。對于二語習得者來說,“形”與“意”同樣重要,雖然大規模的直譯看起來較為笨拙,但是它“盡可能地貼近了原文的內容與形式”[14],還原了民族的語言、文化,保留原文特殊語法現象,降低學習難度,是教科書翻譯的不二選擇。
《清文指要》選用平行雙語教學,將原文與譯文置于同一層面,凸顯不同語言思維之間的聯系。直譯的翻譯方式使得漢語文嚴格遵循滿語語法語素形式的對應,保留了滿語原文的規范性,表現原文的意義,可以幫助二語習得者充分理解滿文結構與語法意義。筆帖式研習且深諳二語習得者的學者慣習及關照旗人滿語學習、忠實于原作的譯者慣習,靈活采取直譯的翻譯策略,有效地幫助了旗人的漢語學習并發揮了教科書的引導作用。
三、結語
翻譯界和史學史以往主要注重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以及清末民初的西學翻譯,但是低估了民族翻譯的價值。[15-16]清代滿漢合璧會話教材《清文指要》反映的滿漢互譯現象,在翻譯史中具有重要意義。
通常情況下,翻譯一般很少采用單一直譯的方式,因為直譯一般等同于逐字硬譯,被認為是缺乏技巧的表現。《清文指要》中出現的“VP了的時候”多為筆帖式直譯滿語的結果,從該結構語義與句法表達的特殊性也可以看出直譯的局限性:僅僅移植滿語語法結構而不加以調整,會導致漢語部分語句的不通順及文字的不洗練。但是直譯的翻譯方式并非反映了筆帖式翻譯水平的下降或者翻譯策略處理的失誤,而是筆帖式根據當時旗人漢語特點以及具有教學特殊性質的教科書有意識、有目的地選擇的結果。直譯避免了間接轉譯或者意譯造成的語言二次變形和語言信息量的增刪,保持了原文翻譯的清晰和豐富性,使讀者能夠準確地理解原文的意義和語法成分。這一認識可以使我們更接近于旗人漢語的本質。
注釋:
①本文使用《清文指要》三槐堂重刻本(1890年)。
②參見三槐堂重刻本《清文指要·序》(1890年)。
③本文語料來自王繼紅、李聰聰、彭江江、房旭、馬楷惠、王曉艷等人整理并完成的滿蒙漢合璧文獻《一百條》系列語料庫。文中選用的滿語拉丁字母轉寫為穆麟德夫(1892)AManchuGrammerwithAnalysedTexts一書的轉寫法,引用例句的所屬章回段落序數以語料庫編排順序為準。
④參見(清)福格《聽雨叢談(卷八)》:“巴克什(baksi):亦作榜式,亦作把什,乃清語文儒諳悉事體之稱。”
⑤參見《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匯編·官常典》第264卷,陳夢雷(編)、蔣廷錫(校)。
⑥參見王繼紅于2018年“語言互動史研究——近代東西語言接觸研究學術會議”宣讀的《清代旗人漢語的內部差異——以滿漢合璧文獻為中心》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