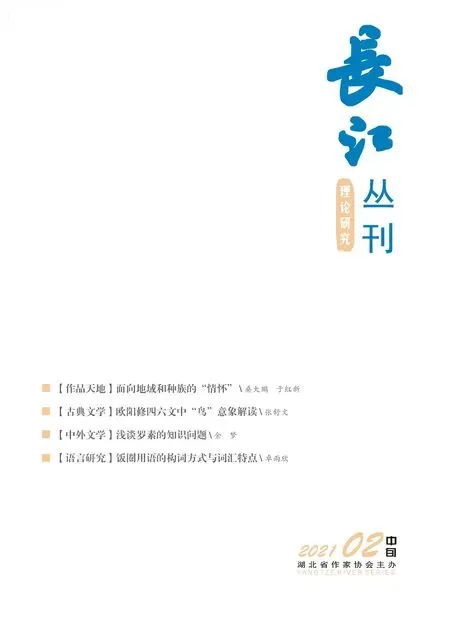“嘴皮子上的后大套”王占昕“呱嘴”藝術研究
■
河套學院

圖1
王占新又名王占昕(圖中右一王占昕,左一其子王舜,圖片來源于其演出宣傳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人,1986年入臨河曲藝團,師從相聲大師候寶林的師弟王世臣,師妹張松青(藝名小明星)學習相聲,隨從天津曲藝團趙學禮學習快板書、數來寶,后又拜西安曲藝團相聲演員鄭平安為師,1995年進入臨河歌舞團,在繼續表演曲藝的同時,轉攻二人臺。這一時期開始與民間藝人王云亮老人學習“數板”(呱嘴的前身),1998年相聲《飯盒小姐》獲全區環保調演二等獎;2001年12月,在廣州舉辦的全國第十二屆“群星獎”大賽中,相聲《夸河套》獲優秀獎,二人臺數板《王婆賣瓜》獲銀獎。2004年二人臺《王婆罵雞》在內蒙古首屆二人臺電視大賽職業組和晉、蒙、陜、冀二人臺藝術電視大獎賽總決賽中均獲二等獎。2004年10月,自治區專業團體文藝調演呱嘴《王婆罵假》榮獲銀獎。2006年8月,二人臺抹帽戲《王婆罵假》榮獲全區二人臺調演一等獎。2006年9月23日,呱嘴“王婆系列”獲第四屆曲藝節最高獎“牡丹獎。”2007年,同謝峰、郭文華、張金龍等共同拜中國二人臺表演藝術家武利平為師。
王占昕現在是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二人臺藝術團國家一級演員、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二人臺代表性傳承人。中國文聯文藝志愿者協會會員,中國曲藝家協會會員,內蒙古曲藝家協會副主席,內蒙古文藝家志愿者協會副主席。內蒙古文聯文藝工作者職業道德建設委員會委員。結合二人臺藝術中彩婆子風趣幽默的表演,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把二人臺呱嘴藝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呱嘴藝術特色、和自己的表演風格。呱嘴“王婆系列”在社會上產生深遠的影響。代表作品有呱嘴《王婆罵雞》《王婆罵假》《二人臺唱成萬人臺》二人臺傳統小戲《補鞋》《借冠子》《探病》多次應中國曲藝家協會的邀請赴日本、韓國、西班牙、英國、愛爾蘭、盧森堡、德國、法國進行藝術交流演出把二人臺、呱嘴藝術帶出國門走向世界。多次獲國家及區內外大獎、榮獲巴黎中國曲藝節“盧浮”特別獎、烏蘭夫基金民族文化藝術杰出貢獻獎。評選為第三屆內蒙古自治區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為弘揚發展傳承二人臺藝術做出巨大貢獻。
王占昕本人是從快板學習入門的曲藝行當,后又系統的學習了二人臺唱腔藝術,這些“啟蒙式”的學習都為他將呱嘴藝術和其他種類的藝術融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說唱式”曲調源流
現在流行在后套地區乃至整個內蒙古西部地區的呱嘴藝術是屬于曲藝范疇之內的一門民間傳統藝術,具有“說唱”性質。對王占昕本人采訪而得知呱嘴藝術在其之前是只有說腔而沒有唱腔的融入的,王占昕本人是相聲行家出身,精通快板的說唱腔韻,所以將之前的只說不唱與快板的說唱腔融為一體形成了現在的呱嘴藝術的“說唱體”。因此,他的呱嘴藝術特色具有了濃郁的唱腔特色,更加能鮮活的表現其藝術內容及形象。這種說唱不是真正的類似蒙古族說唱音樂“烏力格爾”“好來寶”的那樣的說唱形式,這種快板說唱腔基本具有“公式化”的特點,固定的腔調基礎上添加不同的說詞。伴奏樂器也是無音高的噪音樂器,而蒙古族的說唱是樂音樂器大四胡作為伴奏樂器,所以“呱嘴”的這種說唱只具備腔韻而不是真正的說唱,因此也只能說具備“說唱”的性質。
通過訪談得知,他偶然在一次喪宴之上,聽到當地老藝人王云亮的“數板”表演(后套地區稱“呱嘴”的前身稱為“數板”,土默特地區稱為“干磕兒”,于2004年晉蒙陜冀二人臺大賽之后統一將該民間藝術冠名為“呱嘴”。)激發了其濃郁的學習欲望,但是這一時期的“數板”只有說腔而無唱腔的,其類似于“串話”的集成,王占昕在數十年的“數板”學習之后,在經典曲目《王婆罵雞》中融入快板藝術的唱腔,進一步使這門語言藝術具有了一定的旋律感,不再是純粹的、單純的語言表演,從而形成了現在的“說唱”性質的民間傳統藝術。
二、節奏靈活多變
傳統的呱嘴藝術是“一板一眼”的兩拍子式的節拍單位,多以“正拍式”的起句為其節奏特點。在王占昕演繹的一大批呱嘴曲目中,如:《王婆罵雞》《王婆罵假》《王婆說風》《懶大嫂》等等中,其突出的節奏特點是“后半拍”與“搶拍子”式的起句法,這樣就有別于傳統式的正拍起句法。見例1《懶大嫂》的傳統與現在的節奏對比(圖2)。

圖2
通過上例的比較,首先是速度上有所不同,后者比前者略微的快了一些,其次是節奏上后者變化更為豐富些,起句多為“后半拍”的起法,實際在表演中后半拍起句時還有些“搶拍”的感覺,這樣靈活的語言節奏與人物角色更加生動貼切的融為一體,能夠很好的調動觀眾賞聽的積極性。另有,王占昕的表演在原有作品的基礎上加入了大量的方言“襯詞”,這也促使語言的節奏發生了改變。
三、伴奏樂器的豐富性
起初的“數板”表演中并沒有伴奏樂器的出現,只有表演藝人主觀能動性的去把握節奏,后來藝人們將梆子這一敲擊性樂器引入,幫助表演者固定節拍節奏,從而形成節奏特點上的一板一眼的節奏節拍特點。王占昕的呱嘴藝術表演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之上又將鼓、四塊板、手輪、小鑔加入伴奏樂器行列,從而形成“五件套式”的伴奏樂器規模,形成“立體化”的伴奏模式,使節奏的聲響效果得到極大的豐富,也使得這一藝術形式的表演更具感染力。

圖3
四、帶妝“角色化”表演
在傳統的呱嘴藝術表演中受到時間、場地等因素的影響(時間的不確定性——有時說演就演;場地靈活性——并不都是具有舞臺才進行演出),從而具有隨時隨地的演出特性,其演出的也多為舊時婚喪嫁娶等民間宴會場所。因而傳統的民間藝人往往進行的是沒有化妝沒有角色裝扮的表演,這種形式不具備舞臺化的演出形式,也是大眾化演出的需求所致。王占昕的表演從傳統曲目《王婆罵雞》中的王婆這一角色入手,形成了帶妝、帶裝扮的舞臺化表演形式,大多數情況下是“丑角”化的扮相,男性演員裝扮成農村老婆兒(后套地區老太太的方言稱謂)扮相,其本身就是一種幽默滑稽的藝術行為。此類扮相使藝術形象更加具體化、生動化。這種化妝式造型對藝術表演大致可以起到三方面的促進作用:(1)塑造準確地人物形象有幫助;(2)化妝與人物角色相融合;(3)提升演員與觀眾的互動性有幫助。王占昕的這一突破將傳統的民間藝術推向舞臺專業化表演,為民間藝術的傳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五、遵循師傳原則
王占昕本人承接了后套地區“呱嘴”藝術的“手藝”,并且也將其提升到了相當高的藝術境界,從他開始再往下傳給弟子也是有他自己的原則——“學我者生、像我這死”,他不贊成他的弟子再模仿他,“復制”他的藝術形象及相關方面,相反,他鼓勵弟子們要對陳出新不斷的去創造新的藝術表現形式、新的藝術形象。筆者在對“呱嘴”藝術做田野調查時發現,雖然王占昕本人積極鼓勵弟子們去走創新的道路,但在表演時弟子們的模仿“痕跡”還是很明顯的,有的甚至是“復制”師父的藝術表演風格;與此同時,在民間也有大量的喜愛“呱嘴”藝術的人們在模仿王占昕的扮相及其表演風格,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王占昕的“呱嘴”藝術表演影響力之廣、之大,但是,從一門藝術發展的角度來看,還應該遵循“學我者生、像我者死”的規則,不可去“復制”前人的藝術風格,這也正是藝術的魅力其根源所在是也。
綜上所述,王占昕從偶然間接觸到“呱嘴”再到將其發揚光大,這其中也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也是在不斷的磨練與思考中前行,將其他藝術形式與“呱嘴”藝術相融合,形成了當今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新“呱嘴”藝術形式,這也印證了藝術發展的道路肯定是融合的道路,孤立的、“復制”化的藝術思維其結局肯定是窮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