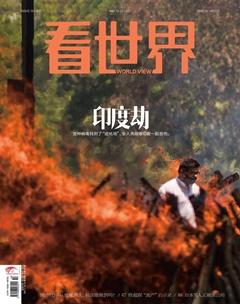“新婚貸”與“天使計劃”:鼓勵生育的社會
丁海笑

2019年4月13日,伊朗伊瑪目廣場,外出參觀的女學生
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都一直存在對繁殖的干預。在食物豐富的尼羅河一側,母象每4年生一胎,而在食物貧瘠的另一側,母象每9年才產一胎。蜂王不僅可以根據巢房的大小及花源的多少來確定產卵的數量,還可以按需要來決定性別。
馬爾薩斯于1798年發表《人口論》,他主張對人口增長采取積極的限制。除中國外,亞洲的伊朗與日本是兩個將人口控制理論付諸實踐的典型國家,不過兩國都有過數次調整人口政策的舉措。因為數據的盲區,我們無法得知哪些人口的改變是人為干預造成的,哪些人口的變化是隨著自然條件、歷史、社會、經濟背景的變化而自然發生的;我們只能羅列每一次調整背后的原因,且分析這些調整的啟示。
被戰爭扭轉的計劃生育
伊朗是近現代歷史上唯一實施計劃生育的伊斯蘭國家。其人口控制政策始于巴列維王朝時期,背景是伊朗在現代化過程中工業基礎薄弱、人口急劇增長、食物短缺。巴列維國王深受馬爾薩斯主義和“人種優越論”的影響,開展一系列“增強人民體質、促進智力發展、塑造優秀雅利安民族”的社會運動。
在巴列維國王的授意下,伊朗設立家庭計劃生育委員會,將計劃生育作為國策推行。計劃生育使伊朗的人口出生率陡然下降,至1973年,伊朗年人口增長率為2.7%,比前十年降低了3.1%,與之相應的是伊朗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切似乎正按巴列維國王所設想的發展,再造波斯帝國的輝煌指日可待。
從1975年開始,伊朗經濟下滑,通貨膨脹嚴重,民間與政府的矛盾激化。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伊朗人民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1980年,兩伊戰爭打響,深陷戰爭泥淖的伊朗需要大量的軍事人口。領導人霍梅尼一上任就鼓勵生育,戰爭期間伊朗的人口反而出現了大幅增長,從1976年的3400萬到了1989年的5000萬。當時的伊朗婦女平均會生7個小孩,遠超當時的世界平均生育率。

2020年9月6日,伊朗德黑蘭一所兒童醫院內,3個月大的嬰兒
鼓勵生育政策在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出現了翻轉,新上任的領袖認為戰爭已經結束,過高的人口增長超過了伊朗的負擔能力,出現了嚴重的糧食危機與住宅問題,于是轉而規劃節育政策。從1988年開始,伊朗重啟了生育控制計劃,向偏遠農村投放了大量計劃生育的醫生和官員。
自1989年11月開始實施的全國家庭計劃生育項目包括:鼓勵婦女把生育間隔延長3至4年;勸阻18歲以下和35歲以上的女性不要生育;縮小家庭人口規模,鼓勵兩孩家庭。
1993年,伊朗議會通過了《人口與安排家庭法》,規定三孩以內的家庭可以享受免費醫療保險和免費教育,按人頭可優惠購買生活必需品,超標出生的孩子不能享受福利,家長也不能享受帶薪產假。一些伊朗男子接受了由政府提供的輸精管結扎手術,來降低伊朗的嬰兒出生率。項目實施后,伊朗的年生育率跌到了3%以內。此舉曾被聯合國贊許為伊斯蘭國家典范。
伊朗生育率雖然下降,但多年的經濟衰退、高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并未得到緩解。而且,人口控制政策只是讓波斯婦女的生育數下降,而諸多的少數族裔生育數并未明顯下降,伊朗的內部矛盾加劇。
/伊朗是近現代歷史上唯一實施計劃生育的伊斯蘭國家。/
代孕合法化
2006年,伊朗總統內賈德認為,增加人口可以使伊朗取得相較西方國家的勞動力優勢,因此又開始鼓勵生育。
伊朗的國家立法機關開始配合發布早婚早育、多生多育的政策。2009年,伊朗提出了一個鼓勵生養的計劃,即為每名新生兒建立新生兒鼓勵賬戶,提供從出生至18歲的補貼。

1970年代,伊斯蘭革命爆發前的伊朗女性
/伊朗人的結婚率在近十年下降了40%,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齡為29歲。/
2012年,伊朗解除了長達24年的人口控制政策。從2014年開始,伊朗甚至采取了一系列強硬手段,通過法案來禁止人民進行絕育手術,禁止一切避孕用品的商業廣告,禁止無理由墮胎,還建議企業優先雇用有孩子的婦女。
內賈德的鼓勵生養計劃收效甚微,原因在于結婚的人變少了。伊朗人的結婚率在近十年下降了40%,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齡為29歲。伊朗女性的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學歷低的女生幾乎進不了社交圈子。受西方思想影響,高等教育成為逃避婚姻的一種方式。由于受西方國家制裁,伊朗國內的經濟問題也讓結婚生子變得困難,2016—2017年,伊朗的失業率達到11.4%以上。
2020年,伊朗人口增長率首次降至1%以下,平均每位婦女生育1.7個孩子,低于整個中東(含北非)地區每位婦女生育2.8個孩子。德黑蘭大學人口統計學教授沙拉·卡澤米普爾指出,城市化、高識字率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是伊朗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到2050年,伊朗可能成為中東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
2021年3月,伊朗衛生部宣布代孕合法,引起一片嘩然。新婚貸與早婚貸的補助,也隨之大幅提高。伊朗衛生部副部長阿里里扎·萊西甚至認為,墮胎等同于“殺人重罪”,他呼吁司法部門和網警配合打擊網上銷售打胎藥的行為。
伊朗的最近一次人口政策調整,是在21世紀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做出的。祭出一系列的舉措背后,伊朗似乎無力扭轉生育率下降的趨勢:經濟與國際環境每況愈下,加上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單單“催生”也無濟于事。

1973年,伊朗國王巴列維二世與其妻子、兒女
日本少子化危機
亞洲另一端的日本,早在江戶時期便有因生活所迫而限制人口的舉措。明治維新之后,隨著民眾生活條件提高,醫療衛生狀況得到改善,政府為了增加人口,立法對墮胎定罪,從而刺激了人們的生育熱情,日本人口迅速增加。
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國土面積狹小的日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人們大規模向海外移民。今天巴西仍留有不少當時的日本移民后裔。人口增加也促使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人口擴張政策隨之出臺。1939年的“結婚十訓”,就是鼓勵生育、增加人口的政策。1941年,“人口政策確立要綱”提出20年內日本人口達到1億的目標,為此提倡早婚早育,每對夫婦要生5個孩子。
二戰后日本經濟大衰退,龐大的人口造成糧食供應不足。1949年,政府成立了家庭計劃普及會,通過派發避孕套試圖控制人口增長。1959年時,日本家庭的人口出生數被掌控。
到了1970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達到最高值,隨后開始急劇下降,來到了人口少、出生率低的時代。政府又開始重新鼓勵生育。

越來越多的日本女性選擇放棄結婚生育
21世紀的日本進入了“低欲望社會”,經濟不景氣,消費力不足。日本如今是全球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截至2020年6月1日,日本總人口約為1.25億,其中15歲以下人口約為1500萬,為歷史最低值,65歲以上人口為3600萬,為歷史最高值。日本是個長壽國,年輕人欲望縮減的同時,許多老年人卻工作在第一線。
日本的少子化跟年輕人不愿結婚息息相關,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不想有責任,不想承擔責任,不想擴大自己的責任。家庭女性要承擔育兒養老的傳統責任,越來越多的日本女性選擇放棄結婚生育。而日本又不像法國或者北歐國家那樣開放,法國、北歐國家幾十年前就已經認可了事實婚姻,非婚生子超過半數。日本未婚女性一旦懷孕,將面臨奉子成婚或墮胎的選擇,這也對生育率存在束縛。
/改變生育率不僅要順應歷史時空背景,更重要的是人們婚戀觀念的改變。/
在對付人口減少的各國政策實踐中,現金補貼政策是一種直接、簡單的方法。現金補貼包括生育津貼、育兒補貼、家庭補貼等,通過補貼減輕培養孩子的經濟壓力,有助于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
日本鼓勵生育的政策,主要涵蓋經濟補貼、保障休假、托幼服務、女性就業支持等領域。日本生育女性可獲得42萬日元的一次性生育臨時金。日本還設立了14周產假、10個月育兒假以及8周男性育兒假。日本于1994年、1999年和2004年三次升級“天使計劃”以擴大托幼服務。
2020年5月29日,日本內閣確定了第四次《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大綱首次提出減輕3個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負擔、為年輕人結婚提供支援等具體措施。除了無償提供幼兒教育和保育服務等措施,大綱還加入了對不孕不育治療的支持和擴大兒童津貼等內容。
同伊朗一樣,進入21世紀的日本面臨著更嚴峻的少子化危機。日本新生兒數量自2016年跌破100萬大關后逐年下降,2020年日本新生人口數量為87萬多,同比減少2.9%,出生數量創下百年新低。
日本學者大前研一認為,困擾日本的最大問題在于人口減少,而日本已錯過調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時機,即使再過三四十年,日本的勞動力人口也不會增加,高齡化將會持續加劇,只能通過移民來填補日本的人口缺口。
伊朗已率先宣布了代孕合法,且不論道德因素,這是一場觀念的革命。而日本至今仍對墮胎、事實婚姻態度保守。日本與伊朗的例子或許能夠說明,改變生育率不僅要順應歷史時空背景,更重要的是人們婚戀觀念的改變,頻繁的人為干預有時候效果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