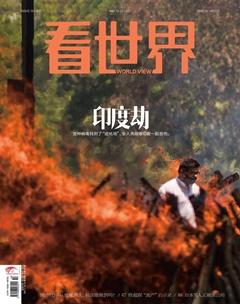高福利北歐國家:無須養兒防老
江穎斐

瑞典,遛狗的老年人
根據最新的聯合國人口報告,2020年,全球60歲以上人口占比13.5%,65歲以上人口占比9.3%。而歐洲的老齡人口占比,幾乎是全球平均比例的兩倍。按照老齡化社會的國際標準(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7%),整個歐洲已經深陷老齡化泥潭。北歐福利國家也不能幸免,其中尤以芬蘭的情況最為嚴重:60歲以上人口占比29%,65歲以上人口占比22.6%,老齡化問題嚴峻。

非營利組織“薩爾瓦迪翁救助軍”提供的長者午餐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北歐國家的老年服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屬于私人領域,是家庭和當地社區的責任。但是,隨著福利制度的引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政府開始負擔社會的養老需求,建立養老保險制度和公共照顧體系。至20世紀末,所有北歐國家都形成了以養老院和家庭護理為基石的公共護理體系。各市政府承擔了其轄域內市民的大部分公共服務。
當前,北歐國家社會已經在觀念和制度上,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養老問題是政府公共部門的責任,盡管很多子女在積極地照顧他們年邁的父母,但贍養老人并不被視為是個人的法定義務。養兒防老,無論在制度上、倫理觀念上,還是實際操作層面,都被宣告無效。養老問題被拋入社會,家庭照顧并不能作為社會老齡化問題的可持續解決方案。
/在挪威,有相當于10萬名全職員工的老年護理志愿者。/
北歐福利國家,曾經在高漲的社會主義思潮中快速發展工業化,走出了一條全新的資本主義道路,又避開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建立了一套成熟的高福利經濟制度。如今,當整個歐洲陷入生育率低谷與老齡化社會,這些高福利國家,是否以其雄厚的經濟基礎與獨特的社會制度,開辟了一條可供借鑒的老齡化問題解決之道?
養老金與退休制度
北歐福利國家雖然各自的養老金制度不盡相同,但依然有著一些共同點:都是一個多支柱體系,其中包括最低養老金、收入相關養老金以及個人儲蓄,三者之間互為補充。最低養老金由政府向全體居民發放,無論居民是否具有公民身份、是否繳費,只要在境內居住滿一定年限,到退休年齡就有資格領取養老金。

芬蘭Kauklahti老年公寓
另一部分是與收入掛鉤的養老金。在芬蘭,這部分養老金覆蓋所有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只是不同經濟部門的計劃有所差異。養老金是基于終身收入的,但隨著勞動年齡的增長,后期的收入比重更大。比如,從2005年起,18~25歲人口的養老金收入增長率為1.5%,53~62歲為1.9%,63~67歲為4.5%。這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中老年人延遲退休、繼續工作,以緩解芬蘭勞動力人口的下降。
2020年,芬蘭人的平均退休年齡為61.9歲。21世紀初以來,芬蘭平均退休年齡已經增加了3年,目標是在2025年達到62.4歲。芬蘭養老金中心官網2月25日發布的統計報告顯示,在2020年這個遭遇疫情沖擊的年份,退休人群繼續工作的熱情前所未有地高漲。在無法享受業余愛好和旅行的特殊時期,退休后的休閑時間似乎也變得不那么誘人。
在北歐國家中,芬蘭的養老金更大程度上與收入掛鉤,和歐洲大陸國家較為相似,丹麥、冰島則是對無收入或幾乎無收入居民頗為慷慨,而挪威和瑞典則介于兩者之間。
總的來說,北歐國家強勁的經濟后盾以及在養老金制度上的前瞻性改革,使其已經具備充足的養老金儲備。當歐洲一度陷入主權債務危機時,除冰島以外的所有北歐福利國家都沒有任何凈國家債務。
多元主體的引入
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政治家的影響下,養老事務也從國家公共部門一手包辦,轉變到政府、私營公司及社會非營利組織多方主體共同參與協作的局面。政府企圖通過引入市場機制、鼓勵社會參與,獲得更好、更高效的服務。
芬蘭在2000年引入營利性機構參與市場公共服務。市場化最為集中的領域,是為弱勢群體(包括老年人口)設計和提供相關服務。
參與公共養老護理的主要非營利組織,包括薩爾瓦迪翁救助軍(Salvation Army)、教堂城市使命(the Church City Mission)、紅十字會等。這些組織會提供一些免費培訓,以便義工們能勝任他們的工作。但是,許多人并不愿意成為上述機構中的一員,也不愿意將其作為自己的—項長期職責,而只希望零散地做一些志愿工作。為了充分吸收這部分資源,由不同群體和機構組織的志愿中心成立起來,以招募這部分志愿者,開展一些照護活動,包括拜訪老人、幫助老人前往醫院、幫忙購物等。志愿中心也可以由公共組織運營,從而獲得更多的公共支持。
在北歐,盡管家庭沒有贍養老人的正式義務,仍有很多人以志愿工作的形式參與其中。志愿活動是他們在社會互動和人際關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挪威,有相當于10萬名全職員工的老年護理志愿者。如果這些志愿者全部放棄他們的職責,北歐國家的老年服務體系將立即崩潰。
居家養老的回歸
在芬蘭有句諺語:“無論什么年紀,家對每個人

改裝的老人居室

為老年人配備的緊急求助項鏈

Viarama的VR產品向長者提供虛擬的世界旅行服務而言都是最好的。”
20年前的芬蘭,老年人流行住養老院,為此各地興建了很多養老機構。如今,機構養老的弊端日益顯現,比如“住進去容易搬出來難”“服務重心從護理患者轉向康養地產”。而且,芬蘭隨著老齡化問題的進一步加重,至2030年,國家難以全額支付各大養老院的服務,傳統的養老模式再難維系。今天的芬蘭,必須積極尋找可行的在線和居家醫養保健服務。芬蘭社會衛生部制定的最新目標是:超過90%的75歲以上老人能獨立地在自己家中養老。
如今,芬蘭正致力于建設一張覆蓋全國的居家養老服務網絡。服務通常由具有專業資格的家庭護理團隊完成。以赫爾辛基市政府為例,赫爾辛基全市共劃分為73個服務區,每個服務區都有2~3個護理團隊,每個團隊約有15名專業人員。護理團隊工作強度很大,平均每人每天上門服務十多次,每次服務10分鐘到半小時不等。
老人的居室也經過改裝,臥室、衛生間和廚房的門檻都被移去,浴室淋浴噴頭下安放了座椅,墻壁上安裝了扶手,以防止洗澡時滑倒。室內改裝的費用大部分由赫爾辛基市政府支付,本人只需要負擔其中的一小部分。
/芬蘭社會衛生部制定的最新目標是:超過90%的75歲以上老人能獨立地在自己家中養老。/

北歐福利國家中,芬蘭的老齡化問題最為嚴重:60歲以上人口占比29%,65歲以上人口占比b22.6%。圖為芬蘭赫爾辛基街頭
為了解決退休老人的社交需求,老年人與青年學生共同居住的試點項目——合住計劃(公寓業主共享公共空間)陸續開展。2015年“活躍的老年人”協會合住項目二期在赫爾辛基落成,名為“家園港灣”。建筑是完全無障礙的,輪椅可暢行無阻。“家園港灣”不是一座普通的養老院,而是一種新型的自助式居住方式。老人除了要打掃自己的公寓房間,還要組成家務組,輪流打掃社區公共空間,并在雙休日的晚上,為愿意一起聚餐的老年人做晚飯。這種生活方式,適合那些希望生活自己做主,同時又喜歡社區氛圍的老年人。
先進科技的助力
隨著居家養老模式的回歸,芬蘭入戶護理人員短缺問題也顯現出來,而利用前沿科技提供遠程護理服務,則被作為居家養老的輔助手段。
芬蘭赫爾辛基市政府主導的“家庭護理項目”,為約4000名有需求的居家老人配備了安全小設備:GPS手環、摔倒檢測器、報警按鈕、護理人員電話專線。護理人員可以遠程監控這些設備。傳感器在探測到異動時,會向護理小組發送警報。
無論是依靠護理人員還是電子設備,盡早發現問題是老年健康生活的保障。芬蘭的一些城鎮,已經在測試能實時追蹤獨居老人日常活動的技術。MariCare Oy和Benete等科技公司,已經開發出利用運動傳感器收集數據的網絡系統,可以顯示出老人在家中的活動軌跡,以及上廁所、打開冰箱的頻率。護理人員通過匯總這些數據,來確定優先家訪的對象和需要檢查的事項。例如,上廁所次數明顯增加,可能因為尿路感染;打開冰箱的次數減少,可能顯示患者記憶力衰退問題加重。
除了疾病困擾,“孤獨感”也是獨居老人們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赫爾辛基市政府為不便出門的老人舉辦虛擬聚會,其中包含益智問答、椅子康養課、唱歌活動、讀書會,以及由牧師主持的宗教討論會等。Viarama公司的VR產品,通過為老人提供虛擬的世界旅行,幫他們回憶過去的美好時光。越來越多的老人可以通過社交媒體與朋友和家人互動。
無論是養老模式的轉變,還是科技手段的引入,上述一系列的芬蘭養老舉措,都依然處于探索和完善之中。而且,富裕的福利國家在以社會力量解決養老問題時,于國家經濟實力、社會制度、公眾意識方面,都有著其先天的優勢。然而,每個國家有著本國的特殊國情,其中的經驗也不能被盡數復制,但福利國家的開創性有效嘗試,至少已經向我們證明:老齡化問題有解決之道,而且“養兒防老”并不會成為其中的必備選項;在社會層面上來統籌安排個人養老,給予每個人更多元、更自由的人生路徑,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