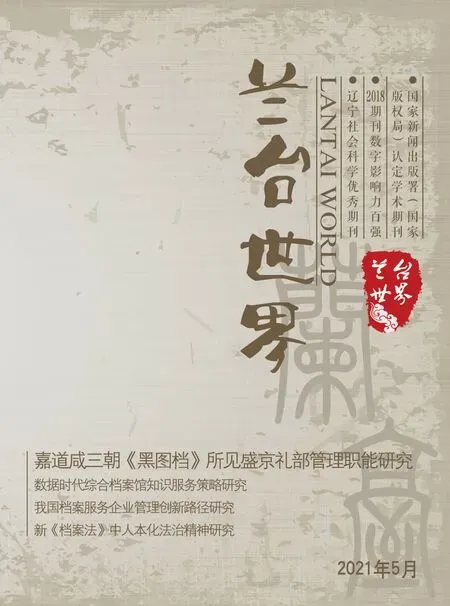荷蘭面向GLAM的數字人文教育培訓項目研究
嚴 棟
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一種數字技術與人文學科交叉而形成的新興研究領域,始于20世紀40年代,現在已經受到國內外的普遍關注。歐美不僅是數字人文的發源地,也是數字人文教育的發源地和主要的實踐地。數字人文教育對于推進數字人文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隨著數字人文的發展,業界有些學者認為數字人文已經慢慢成為一個獨立學科[1]。國內知名學者馬費成先生認為,數字人文在人文研究和數字技術中大有作為:解決傳統人文學科無法解決的難題;發現并研究新技術帶來的新的人文問題;數字信息工具及平臺對人文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教育的影響等[1][2]。為了更好地推進數字人文工作,世界上許多高校已經開始進行數字人文教育,包括本科、碩士和博士等不同層次的教育。同時,為了做好有關數字人文的服務工作,荷蘭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the Netherlands)、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圖書館(Vrije University Amsterdam library)和萊頓大學圖書館(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聯合成立的數字人文培訓(以下簡稱DH clinics)[3],為推動荷蘭數字人文知識普及作出了重要貢獻。數字人文培訓有別于高校數字人文教育,對我國非高校機構進行數字人文專業教育實踐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國內外數字人文教育發展回顧
數字人文教育對數字人文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歐美作為數字人文的起源地,也非常積極推動數字人文教育工作。2015年,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協會(ACRL)通過了《高等教育信息素養框架》(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以下簡稱《框架》)。《框架》提出權威的構建性與情境性等6個“閾概念”[4-5],也是數字學術迫切需要學習的信息素養能力。2019年,國際知名的iShcools聯盟已經專門成立了數字人文課程設計委員會(Curriculum Design Committee for Digital Humanities),我國武漢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曉光教授是該委員會的委員之一。迄今為止,國內外有不少高校紛紛設置了數字人文教育,其中歐洲有32所高校、北美有9所高校在開展不同層次的數字人文教育項目[1]。學者張璇和孟祥保對開展數字人文教育的高校進行調研,發現數據素養可分為基礎能力、核心能力和高級能力等3個級別:其中基礎能力包括數據認知、數據工具、數據文化和數據倫理;核心能力包括數據發現、數據評估、數據分析、數據管理和數據可視化;高級能力包括數據監護、數據共享、數據保存、數據轉換和元數據創建等[6]。我國學者加小雙和馮惠玲在數字人文教育方面提出SCP2的教育體系,該體系由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ered)、以協作(Collaboration-based)和平臺(Platform-based)為基礎、以課程培養(Curriculum training)和項目實踐(Project practice)為核心[1]。該體系強調數字人文教育的參與性、協作性、平等性與創新性,打破專業局限和學科局限,體現出數字人文的“破壞性創新”特點。學者肖平和樊振佳等人對美國圖書館如何服務大學生創新創業進行了研究,提出素養教育、協調創新及數字人文創客空間等教育形式為大學生提供服務[7]。
以上數字人文的相關教育都是基于國內外高校而進行的精英教育,而對于非高校圖書館如何進行數字人文教育的研究及實踐卻未有提及。但數字人文研究并不僅僅存在于高校,整個社會人員都可能是數字人文的研究者,非高校圖書館如何更好地做好數字人文服務工作顯得非常重要。DH clinics雖然主要進行的是非高校專業教育,但其發起成員中有兩個高校圖書館,對于高校圖書館如何面向GLAM(美術館、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下同)提供教育培訓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二、荷蘭DH clinics項目的緣起、階段管理及其影響
1.項目緣起。隨著荷蘭越來越多人對數字人文感興趣,有關這方面的需求隨之增多。荷蘭國家圖書館是整個荷蘭處理最多數字人文需求的圖書館。但在2015年之前,整個荷蘭都沒有有關數字人文的交流平臺,對數字人文交流與教育形成一定的阻礙。受大英圖書館數字人文學術Library Carpentry項目成功的啟發,也為了促進荷蘭數字人文的交流,荷蘭國家圖書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圖書館、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協會數字人文興趣組等多個團隊于2015年同意組建一個有關數字人文的Google交流群,分享在數字人文服務方面的經驗。但由于種種原因,Google交流群僅在2016年發起過,且很少涉及數字人文,所以Google交流群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擁有豐富數字人文服務經驗的荷蘭國家圖書館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圖書館聯合提議成立能為整個荷蘭的大學、科研及公共圖書館數字人文服務的交流機制。該機制最后得到了萊頓大學圖書館的支持,最后形成了荷蘭數字人文培訓(以下簡稱DH clinics)。該項目面向整個荷蘭的GLAM團體及荷蘭大學與國家圖書館聯盟的會員,覆蓋面很廣。
DH clinics有3個目標,分別是幫助學員掌握基本的數字人文知識和技能、加強與數字人文科研人員的聯系及建立荷蘭的數字人文知識社區。(1)基本的數字人文知識和技能包括:明確衡量學者數字人文目前的知識技能與目標之間的差距;能明確理解數字人文科研人員的信息需求,并通過掌握的各種技能進行滿足。DH clinics并不是要將每個數字人文的館員都變成高水平的程序編輯員,但必須能掌握相關的服務技能。(2)加強與數字人文科研人員的聯系,邀請他們參與到DH clinics的培訓中來,將他們所擅長的技能在這里分享給大家,了解他們的真實需求,并讓數字人文館員參與到科研項目中去。(3)建立數字人文知識社區,希望借助DH clinics平臺通過線上和線下的方式形成跨機構、跨部門、跨學科的數字人文項目合作機制,并形成一定的知識成果。所以,DH clinics的目標不僅是為荷蘭GLAM群體提供數字人文交流及知識傳授的平臺,而且是成為荷蘭數字人文項目協作的一個平臺,促進整個荷蘭數字人文向前發展。
2.項目各個階段的管理。
(1)主題獲取。DH clinics為學員們提供了為期5天的培訓安排,包括專業課程及研討會。但專業課程和研討會主題應該是什么則值得慎重選擇,關系到整個項目質量。在主題獲取方面,DH clinics主要通過3個途徑進行:頭腦風暴法、文獻回顧和崗位需求描述等。
頭腦風暴法。DH clinics會為邀請荷蘭的數字人文館員提出該崗位或者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應該具備哪些知識與技能,他們會列出一系列的知識、技能和軟件等。DH clinics將數字人文館員列出的清單交給國內知名的數字人文的項目人員,讓他們確認是否需要這些知識或技能,及是否有所遺漏。通過這種方式,DH clinics能獲得一份與數字人文工作相關的且比較契合實際的培訓主題。
文獻回顧。為了與世界數字人文發展同步,DH clinics在主題篩選時還參考了美國和英國兩份有關數字人文館員能力要求方面的報告。這兩個報告中提到,數字人文館員應具備可視化(visualization)、文本分析與支持(text analysis and support)、數據分析(statistical analysis)、軟件開發(developing software)、編程(programming)、知識庫(knowledge base)、交流能力(communication skills)、領導能力(leadership skills)和科研能力(research skills)。可見,從歐美的調研結果來看,數字人文館員不僅要有一定的技術知識,還應掌握交流、領導等社交方面的能力。
崗位需求描述。DH clinics在網上收集了15個數字人文館員的崗位需求描述,發現可將數字人文需要具備的能力分為軟技能和硬技能:其中軟技能主要包括團隊合作、交流、戰略思考等;硬技能主要包括DH知識庫、教育、培訓、DH經驗等。對于一個數字人文館員來說,軟技能和硬技能都是不可或缺的。
(2)主題篩選。經過以上3個途徑,DH clinics獲得了許多的數字人文培訓的主題,但在這5天的時間內如何合理有效地傳授給學員們是值得商榷的。DH clinics首先根據數字研究活動中的人文分類系統(Taxonomy of Digital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Humanities,簡稱TaDiRAH)對獲得的主題進行歸類匯總,并按次分法(subdivision)分成與文本有關、結構化數據及視頻可視材料等。最后,根據荷蘭數字人文的實際發展情況,DH clinics將培訓主題分成四個階段:獲取(capture)、創造(creation)、擴充(enrichment)和分析(analysis)等,并通過文本及視頻教學等多種形式來實現。
為了讓DH clinics的項目內容能更契合實際,DH clinics將篩選出的培訓主題通過Twitter和GLAM網站的形式展現問卷調查。最后,DH clinics收到了來自14個機構的40份有效問卷。
(3)培訓內容及安排。經過培訓主題獲取、篩選及信息反饋等環節,DH clinics制定了為期5天的培訓計劃,如表1所示。雖然是為期5天的培訓,但學員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有選擇性地聽其中某些課程,也可參與全部的課程。DH clinics為每個課程和研討會分別安排30—40人和15—20人參與。由于空間有限,DH clinics限制每個機構每次最多2人參與該項目。從表1中可知,DH clinics的課程全部都是硬能力,即全部都是與數字人文技術相關的內容,且與時俱進。研討會與當天的課程內容息息相關。

表1 DH clinics培訓內容及安排表[3][8]
第一天主要了解數字化工藝流程、著作權、技術技巧、不同類型數據庫等與數字化和數據庫相關的知識。第二天主要培養學員的計算思維,即將現實問題轉換成用軟件完成的思維,及給學員講授常用的編程語言python。第三天主要培養學員自然語言處理、關系型數據處理和通過OpenRefine進行數據清洗。第四天主要培養學生通過Eventbrite使用歷史數據和原始數字數據進行文本分析。第五天主要培養學生通過Eventbrite處理視聽資料和地理信息分析。
DH clinics主要是幫助學員回答數字人文對于圖書館意味著什么,如何支持數字人文科研及教育等問題,將數字人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DH clinics的課程及研討會的老師均有著豐富的數字人文工作經驗,研討會也通過實際操作的形式替代傳統的討論或展示的形式。
(4)培訓費用。DH clinics無固定的經費支持來進行項目的開展。雖然課程和研討會老師免費為學員講解,但其午餐和路費應由DH clinics負責。為了解決課程和研討會老師的午餐和路費,DH clinics要求報名的機構及贊助商提供不低于500歐元的費用。作為回報,DH clinics在每期培訓期間給贊助商5分鐘的時間做廣告,并在DH clinics的官網展示其LOGO。但DH clinics對贊助商的回報僅是贊助商贊助的那天。從DH clinics的歷史發展來看,其贊助商主要是荷蘭國家圖書館、烏得勒支大學圖書館(Utrecht University Library)、萊頓大學圖書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圖書館、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埃姆蘭檔案館(Archief Eemland)等。荷蘭國家圖書館、萊頓大學圖書館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圖書館等不僅是DH clinics的發起者,也是最主要的贊助者。
3.影響。DH clinics于2017年正式成立并對外提供培訓,到2019年底已經提供了許多場培訓活動。2019年7月8日于荷蘭海牙召開的“圖書館作為數字人文的研究伙伴”的會議上,DH clinics介紹了其發展現狀[9]。DH clinics在原來的3個目標的基礎上新增了1個目標,即通過向館員介紹新技術來減輕他們的工作負擔。DH clinics每期培訓的容納能力從30—40人增加到75—80人。DH clinics的學員以圖書館館員為主,也有少部分為檔案館員和博物館館員。學員在培訓后普遍反映對其數字人文服務工作有積極的作用,但希望有更多有關圖書館提供數字人文服務的真實案例,這也是DH clinics的未來發展方向。DH clinics的成功運行讓更多荷蘭科研人員了解數字人文,特別是提升了荷蘭科研圖書館館員的數字人文服務能力。
三、DH clinics對我國面向GLAM的數字人文教育發展的啟示
我國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汕頭大學等均有設置數字人文教育的相關專業或課程。但除了高校,我國尚未有專門的機構從事數字人文培訓工作。我國數字人文從理論研究到教育實踐都取得了快速的發展。荷蘭DH clinics項目的成功為我國非高校的數字人文教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其以學生為中心、跨機構協作等都值得我們學習。
1.集中精英機構組建數字人文培訓中心。DH clinics的3個發起單位是荷蘭頂級的數字人文研究機構,他們有豐富的經驗和過硬的技術,他們的水平代表著整個荷蘭數字人文發展水平,所以DH clinics是荷蘭數字人文領域強強聯合的結果。我國雖然有高校開設數字人文的相關專業或課程教育,也有不少高校提供了數字人文服務,但對于我國龐大的數字人文需求卻沒有專門的培訓教育機構。所以,我國非常有必要成立專門的DH培訓中心,面向全國的GLAM工作人員和感興趣的數字人文研究人員提供專業的培訓服務。目前,我國武漢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在數字人文教育及項目實踐方面都有成功的嘗試,可由這些機構聯合成立我國的DH培訓中心。這些機構有數字人文中心或數字人文實驗室以及影響較大的數字人文項目成果,這些為我國數字人文培訓提供了良好的設備及經驗。
2.做好培訓主題篩選工作。DH clinics成功的部分原因來自于非常謹慎認真的主題篩選工作。DH clinics主題獲取通過3個途徑進行,幾乎囊括了全部數字人文可能涉及的知識與技能。在獲取主題之后,DH clinics還將這些主題進行分類,并對潛在的機構進行問卷調查,在獲得反饋之后制定了最后的數字人文培訓主題。所以,我國在進行數字人文培訓時也應對主題進行精細篩選,不應僅僅根據自身實力或喜好,而應考慮到數字人文崗位技能需求和潛在客戶的真實需求。數字人文的技能包括軟技能和硬技能,但從DH clinics的實踐和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也應以硬技能培訓為主。只有為學員提供真實有用的知識與技能,才能將數字人文培訓長期舉辦下去。我國雖然有不少機構舉辦過數字人文相關的論壇,但這些一般是數字人文研究前沿的主題,與GLAM數字人文實際工作關系不大。如北京大學已經連續舉辦了4屆數字人文論壇,主題非常前沿,與時俱進,但落實到具體GLAM如何提供數字人文服務較難。以DH clinics學員反饋的建議為例,希望DH clinics能介紹更多GLAM有關成功數字人文服務的案例。這不僅是DH clinics的未來發展方向,也是我國數字人文教育中應重點關注的主題。
3.以學生為中心,提供靈活多樣的學習方式。DH clinics為學員提供的學習方式不僅有專業課程,還有研討會。研討會除了在培訓期的晚上線下舉行,也有通過線上在其他時間舉行的。DH clinics允許不同知識背景和興趣的學員選擇不同的學習課程。學員可選擇五天課程中的特定課程,也可以選擇全部課程。學員可以只選擇專業課程,也可以選專業課程加研討會。這種靈活多樣的學習方式完全體現了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以學生為中心不僅在DH clinics得到體現,也在我國學者加小雙和馮惠玲的SCP2的數字人文教育體系中得到系統論述。所以,我國在開展面向全國GLAM工作人員及數字人文科研人員的培訓時也應以學生為中心,不僅在課程設置上要考慮學員的自身需求,而且要在課程安排和展現方式上考慮到學員的特殊性。
4.制定合理的收費制度和贊助制度。目前,我國無論是高校還是學會舉辦的培訓一般都要收費,這是因為培訓場地和師資都需要相應的支出。所以,我國在舉辦數字人文相關培訓時收取學員一定的費用是能夠理解的,且我國各個機構都有一定額度的培訓費用。DH clinics邀請的老師除了午餐費和來回路費外,其他都是不收費的。但盡管如此,由于DH clinics沒有經費支持,還是需要學員提供一定的報名費用或者收取一定的贊助費。鑒于此,我國高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及協會等舉辦的數字人文培訓不應以營利為目的,但為了支付相應的費用可適度向學員收取一定的報名費,但報名費不宜過高。在報名費不足以支撐培訓費時,舉辦方可邀請相關機構進行贊助,從而減輕學員的報名費負擔。合理的收費制度和贊助制度有利于我國數字人文培訓健康發展。
5.建立國內數字人文交流機制。DH clinics已經成為荷蘭數字人文交流的重要平臺,建成了國內跨學科、跨部門、跨機構的數字人文經驗交流和項目合作的重要平臺。學者加小雙和馮惠玲在SCP2的數字人文教育體系中指出,數字人文教育要以協助和平臺為基礎,并提到紐約城市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數字人文機構均建立了數字人文教育平臺。學者加小雙和馮惠玲認為,平臺和學術團隊是數字人文教育的兩大基礎設施。所以,我國應在數字人文精英研究機構聯合下建立數字人文交流機制,定期就高校數字人文教育、GLAM涉及數字人文服務方面的教育等進行討論,并積極開展跨機構、跨學科的項目合作。目前,我國數字人文研究機構之間的聯系并不緊密,無論是數字人文項目合作還是聯合舉辦會議,次數都很少。所以,我國非常有必要搭建包含高校和GLAM在內的數字人文交流機制。
四、結束語
我國數字人文的需求越來越多,但面向非高校人員的數字人文培訓很缺乏。雖然有些高校已經開展了數字人文相關的教育,但畢竟受到相關教育的人數不多。所以,我國推進高校數字人文教育的同時也應高度重視GLAM對數字人文培訓的需求。本文通過對荷蘭DH clinics成功的運作經驗進行深入研究,發現非高校也是能夠很好地提供數字人文教育的。在借鑒DH clinics的經驗及評估我國的實際情況后,為我國GLAM的數字人文教育尋找新的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