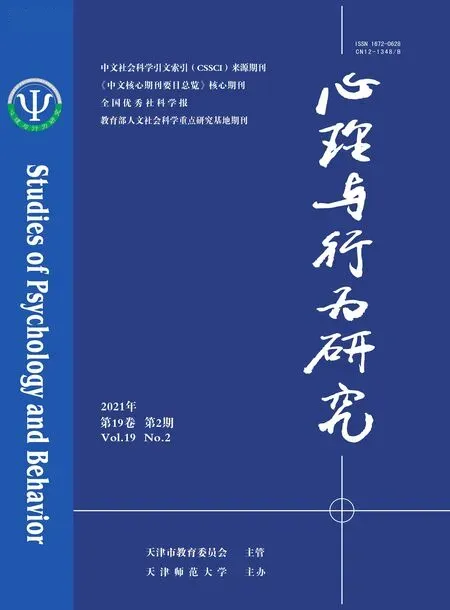幼兒在不同規范標準下的意圖判斷:“副作用”效應
劉希平 云薏霏 柴凱軒 李 楠 唐衛海
(1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天津師范大學心理與行為研究院,天津 300387) (2 天津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天津 300387) (3 學生心理發展與學習天津市高校社會科學實驗室,天津 300387) (4 廣東培正學院,廣州 510830)
1 引言
行為“副作用”(即行為導致的附加結果)的效價會影響個體對行為意圖的判斷。即使行為者先前已知曉并表示不關注“副作用”的發生,個體也傾向于認為伴有消極“副作用”行為的執行者是有意導致消極“副作用”發生的;而并不傾向于認為伴有積極“副作用”行為的執行者是有意帶來積極“副作用”的。也就是說,個體對伴有不同“副作用”效價的行為意圖判斷有著不對稱的判斷傾向,這種現象被稱作意圖判斷的“副作用”效應(the side-effect effect, SEE)(Knobe, 2003)。
SEE 說明個體的道德判斷會影響意圖判斷。因此,國內外發展性研究考察了SEE 產生的基礎。有研究者認為,SEE 體現了個體早期的道德感知或“道德能力”;也有研究者認為,SEE 反映出個體社會化過程中的個體差異。國內對于SEE 的研究比較有限,有兩項研究分別考察了成年人(張靖昊, 2017)以及初中生(陳友慶, 陶君,2016)的SEE,并且都發現積極和消極的道德效價影響被試的意圖判斷,并表現出不對稱的判斷模式。而國外研究者則更早關注了幼兒意圖判斷的SEE。Leslie,Knobe 和Cohen(2006)發現,3 歲幼兒能夠理解“事先知曉”的概念,但不能夠理解“不關心”的概念,因此,3 歲幼兒沒有表現出SEE,而4 歲幼兒出現了SEE。Pellizzoni,Siegal和Surian(2009)的研究也發現了4~5 歲幼兒表現出了SEE。但該研究也發現,即使在4~5 歲幼兒中,仍然有不少幼兒沒有表現出SEE。那么,什么因素影響了幼兒SEE 的發展表現?Michelin,Pellizzoni,Tallandini 和Siegal(2010)控制了幼兒意圖判斷發展過程中的個體差異,考察了故事呈現形式與雙語經驗對3~5 歲幼兒意圖判斷的影響。結果發現,即使是3 歲幼兒,也表現出了SEE現象,同時具有雙語經驗的被試的SEE 表現傾向性更明顯。上述研究說明,幼兒早期已經具有道德意識,并且會受到社會化過程導致的個體差異的影響。
上述研究考察了道德規范標準下幼兒的SEE,但在不同的規范標準下,幼兒的SEE 是否會表現出不同的發展規律?Uttich 和Lombrozo(2010)將“禁止性規范”分為“道德規范”和“約定規范”。禁止性規范(prescriptive norm/injunction norm)是對人們在某種情境下“應該做什么”(Lapinski &Rimal, 2005),或者“怎樣做才是正確的”所做出的規定(Lindstr?m, Jangard, Selbing, & Olsson,2018)。個體在該規范下的行為受到避免社會制裁的動機驅使,并會感受到違背規范帶來的壓力(Kallgren, Reno, & Cialdini, 2000)。道德規范(moral norm)是指約束人們尊重和維護他人固有利益、公平和權利的規范,例如,“不能偷竊”。約定規范(conventional norm)是指確保群體成員按照相同的方式言行所做出的規定,例如,“把黃色的玩具放進黃色的盒子里”(Heiphetz & Young,2017; Mammen, K?ymen, & Tomasello, 2018; Yucel,Hepach, & Vaish, 2020)。
幼兒從3 歲開始就能夠理解道德規范與約定規范的本質。幼兒能夠認識到這兩種規范最大的區別在于適用性不同:不論是何種社會環境背景下,幼兒總是認為違背道德規范的行為是錯誤的,不被允許的,而且后果更加嚴重,理應得到更多懲罰;而違反約定規范僅僅是違背了某個社會組織的規則(Lahat, Helwig, & Zelazo, 2013;Mammen et al., 2018)。此外,當幼兒意識到違背規范的行為引起了受害者情緒化的反應,幼兒就將該行為知覺為違背了道德規范;而當違背規范的行為并沒有導致情緒化的反應,幼兒就認為這是違背了約定規范(Nichols, 2002)。那么,在心理理論領域,幼兒對兩種規范標準的認知是否會影響對他人的意圖判斷?Rakoczy 等人(2015)首次考察了幼兒在道德和約定規范標準中的SEE,并發現,4~5 歲幼兒在兩種規范標準下的意圖判斷是一致的,表現出了穩定的SEE。
但Rakoczy 等人(2015)的研究范式仍存在不足。即在道德規范標準和約定規范標準下的故事情境設置并不完全對等。具體來說,在道德規范標準的故事情境中,遵守/違背規范的行為帶來的“副作用”使行為對象受到了情緒上的影響,由此產生了與道德相關的“副作用”。這很容易讓被試理解行為與結果的關系。然而,在約定規范標準的故事情境中,對“副作用”的操作僅僅描述了動物的位置狀態。因此,被試對行為與結果關系的解讀是不清楚的。
那么,在意圖判斷中,為什么會出現SEE 現象?研究者提出了兩種觀點來解釋SEE 產生的機制。第一,理性推理(rationality accounts)。人們之所以對違背與遵守規范的行為做出不同的意圖判斷,是因為違背規范的行為給推斷行為者的心理狀態和特質提供了認知基礎,但遵守規范的行為并不能提供類似的認知基礎。具體來說,人們在對行為者的心理狀態進行推斷時,使用了理性策略。這種理性策略是考慮行為者的行為與規范的關系,即行為者的行為是否有意違背或者有意遵守了規范。而且這種推斷受到行為者“知識”(行為者事先知道自己遵守/違背規范的行為會引起積極/消極“副作用”)的指導,“知識”的作用在積極和消極情境中的不對稱性(Holton, 2010),導致了人們對行為者心理狀態推斷的不對稱性。即如果個體認為行為者事先知道違背規范的行為會引起消極“副作用”,但選擇忽視這種可能性,并仍然執行了該行為,則個體表現出SEE 的傾向就更加明顯。第二,道德效價推理(morality account)。道德錯誤的行為會自發引起人們對于該行為的負性反應,進而導致對行為者的責任歸因。為了使責任歸因合理化,人們就強調行為者是有意做出該行為的。而道德正確的行為并不會引發需要被合理化的負性反應,因此,道德正確的行為就不太可能被判斷為有意做出的(Alicke, 2000)。
這兩種觀點的區別是,理性推理強調,個體在進行行為意圖判斷時采取了理性策略,或者說會將故事情境中的相關信息作為其推斷行為者心理狀態的證據。而道德效價推理認為,個體會根據行為者引起的道德結果直接做出意圖推斷。本研究推測:(1)如果SEE 不僅在道德規范標準下存在,而且在與道德無關的純粹人為制定的約定規范標準上也能夠表現出來,那么,理性推理觀點就是正確的;(2)如果以幼兒給主人公分配星星的數量作為考察指標,幼兒表現出了不對稱的獎懲行為,也能為驗證理性推理觀點提供證據。
總體來看,本研究嘗試考察兩個問題。第一,使道德規范標準與約定規范標準下的故事情境相匹配,并使用不同的指標來探討幼兒SEE 產生的原因與發展趨勢。第二,考察是“理性推理”還是“道德效價推理”更能解釋幼兒的SEE。除了通過幼兒在道德規范和約定規范標準上的意圖判斷表現來揭示該問題,本研究在意圖判斷任務后額外設計了獎懲任務,嘗試探討幼兒是否會采用理性策略推測主人公的心理狀態。
具體來說,根據理性推理的認知加工過程,個體對行為者的意圖判斷分為兩個階段。階段一,個體利用對表征積極/消極情境,或者“診斷”行為者心理狀態有關鍵作用的信息,并將其整合為理性策略推斷行為者的行為表現;階段二,個體在上述推斷的基礎上判斷行為者是否有意執行該行為(Feltz, 2007; Leslie et al., 2006)。以此為基礎,獎懲任務通過提示幼兒主人公引起“副作用”的遵守/違背規范的行為,并要求幼兒對主人公的行為表現進行評估,進而給予主人公獎勵/懲罰(分配星星),來直接分析幼兒如何表征積極/消極情境。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相比于意圖“有無”判斷任務,利用分配星星任務,考察幼兒對伴隨不同效價“副作用”的主人公行為的偏愛程度,可以更敏感地考察幼兒SEE 的推理過程。
假設2:如果在道德規范標準和約定規范標準中,幼兒都表現出對行為者心理狀態推斷的不對稱性,則說明幼兒在兩種規范中都能理性地使用分析策略進行推斷,理性推理觀點成立;如果幼兒只在道德規范標準下表現出對行為者心理推斷的不對稱性,則說明幼兒只能夠根據道德結果進行非理性的推斷,道德效價推理觀點成立。
2 研究方法
2.1 實驗設計
采用2(“副作用”效價:積極、消極)×3(年齡:4 歲、5 歲、6 歲)×2(規范標準:道德規范、約定規范)的被試間設計。因變量為意圖“有無”判斷得分和星星分配數量。
2.2 被試
被試來自天津市四所幼兒園。主試從小、中、大班中隨機選取了532 名幼兒(男孩265 名,女孩267 名),年齡在38~81 個月之間,并按年齡大小進行了分組:4 歲(38~54 個月)、5 歲(55~66 個月)和6 歲(67~81 個月)。完成正式實驗后,保留了3 個控制問題都通過的被試,最終獲得491 名有效被試。4 歲組161 人,5 歲組170 人,6 歲組160 人。每名被試隨機接受四種故事情境中的一種。
2.3 實驗材料和工具
2.3.1 實驗材料
虛擬故事。為了避免被試對故事中主人公的性別偏好(Susskind & Hodges, 2007; Xiao, Cook,Martin, Nielson, & Field, 2019),實驗編制了兩個版本的故事材料,每個版本包括四種故事情境。兩個版本唯一的區別是故事主人公的性別不同,一個版本的主人公是男孩,另一個版本的主人公是女孩。一部分男孩觀看男主人公版本的故事,而另一部分男孩觀看女主人公版本的故事。女孩也是如此。在道德規范標準下,主人公的行為會導致積極的結果(如,引起弟弟的愉悅感),或者消極的結果(如,引起弟弟的恐懼感);在約定規范標準下,主人公的行為也會引起積極的結果(如,人們想和小老鼠做好朋友,會跟它友好相處),或者消極的結果(如,小老鼠會偷吃糧食,人們把小老鼠抓起來)。四種故事情境的共同點是,主人公知曉行為會引起“副作用”,但表示不關心“副作用”的產生。本研究采用的故事情境的優勢是:(1)設置了主人公為男孩和女孩兩個版本的故事,嚴格控制無關變量,即幼兒對主人公的性別偏好;(2)更明確地闡述約定規范標準故事中的“副作用”,使幼兒能清楚理解故事情境。
控制問題。故事敘述過程中穿插了3 個控制問題,以確保幼兒理解故事的主要內容,同時保證幼兒的注意力維持在實驗上。控制問題分別測查了幼兒是否知曉行為結果、是否知曉行為“副作用”以及是否知曉主人公不關心“副作用”的發生。
測試問題。意圖“有無”判斷任務的測試問題是:“小明(小紅)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獎懲任務的測試問題要求幼兒評價主人公遵守/違背規范的行為表現,以及分配星星(如,“你認為小明這樣的表現好嗎?你認為老師會分給小明幾顆小星星?”)。
問題得分。(1)對控制問題的記錄。對于每一個控制問題,幼兒可能一次性通過問題,也可能第一次沒有通過問題,這需要主試回到有關該問題的情境,再次給幼兒講述相關內容。最多有兩次提示,經過三次詢問后幼兒仍無法通過,就讓該幼兒停止實驗。(2)對意圖“有無”判斷得分的記錄。如果幼兒的回答是“故意的”,就表明幼兒將主人公的行為判斷為“有意”,計1 分;如果幼兒的回答是“無意的”,就表明幼兒將主人公的行為判斷為“無意”,計0 分。(3)對星星分配數量的記錄。幼兒以第三方身份判斷教師分配給故事主人公的星星數量,數量為1~5 顆,分配得越多表明幼兒認為主人公的行為表現越好。
2.3.2 實驗儀器
筆記本電腦,記錄表,筆。
2.4 實驗步驟
實驗是個別進行的。所有數據由兩位主試搜集完成。一名主試搜集了154 個數據,分布在3 個年齡段的不同任務中。剩余數據由另一名主試搜集。第一步,幼兒完成練習任務,完成后進行30 s 的無關活動,之后進行正式實驗。第二步,觀看故事。主試邀請幼兒觀看PPT,并向幼兒演示、講述故事。第三步,控制問題問答。主試對幼兒進行控制提問,記錄幼兒的回答。第四步,完成意圖判斷任務。請幼兒回答意圖“有無”判斷問題,記錄幼兒的回答。第五步,完成獎懲任務。主試首先提示幼兒故事主人公引起“副作用”的遵守/違背規范的行為,之后請幼兒回答測試問題,記錄幼兒的回答。
3 結果
使用SPSS22.0 進行數據分析。
正式實驗之前,通過讓幼兒對小老鼠(小兔子)的喜好程度進行評分,考察了幼兒對兩種動物的態度。3(年齡:4 歲、5 歲、6 歲)×2(性別:男孩、女孩)×2(動物類型:老鼠、兔子)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年齡、性別與動物類型的交互作用均不顯著,ps>0.05。這表明,故事情境中的小動物類型不會對4~6 歲幼兒的意圖判斷產生影響。
3.1 意圖“有無”判斷中“副作用”效應的發展
對幼兒意圖“有無”判斷中回答“是”的人次進行統計,得到不同條件下4~6 歲幼兒的判斷結果。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表 1 幼兒在意圖判斷任務中回答“是”的人次
采用χ2檢驗對幼兒在不同規范標準和“副作用”效價條件下的意圖“有無”判斷人數進行分析。
第一,考察“副作用”效價在幼兒意圖“有無”判斷上是否存在差異。結果發現,“副作用”效價在意圖“有無”判斷上差異不顯著,χ2=0.54,p=0.465。結果表明:“副作用”效價與幼兒的意圖“有無”判斷無關,幼兒總體并沒有表現出SEE。
第二,不同年齡段幼兒的SEE 表現差異是否導致“副作用”效價主效應不顯著?分別考察對于4、5、6 歲三個年齡段幼兒,“副作用”效價在意圖“有無”判斷上是否存在差異。結果發現,對于4、5、6 歲幼兒來說,“副作用”效價在意圖“有無”判斷上的差異均不顯著,χ24歲=1.49,p4歲=0.222;χ25歲=0.01,p5歲=0.928;χ26歲=0.06,p6歲=0.811。結果表明,在4~6 歲不同年齡段幼兒中,SEE 都沒有發生。
第三,SEE 在不同年齡段幼兒中沒有表現出來,是否是不同規范標準下的SEE 表現趨勢差異導致的?分別考察在道德規范標準和約定規范標準下,對于4、5、6 歲三個年齡段幼兒,“副作用”效價在意圖“有無”判斷上是否存在差異。結果發現,對于4、5、6 歲幼兒來說,不同規范標準下的意圖“有無”判斷差異均不顯著,χ2道德規范×4歲=0.60,p道德規范×4歲=0.439;χ2道德規范×5歲=0.63,p道德規范×5歲=0.427;χ2道德規范×6歲=0.64,p道德規范×6歲=0.423;χ2約定規范×4歲=0.95,p約定規范×4歲=0.329;χ2約定規范×5歲=0.73,p約定規范×5歲=0.394;χ2約定規范×6歲=1.27,p約定規范×6歲=0.260。結果表明,在意圖“有無”判斷中,無論是在道德規范還是在約定規范標準下,4~6 歲幼兒都沒有表現出SEE。
3.2 星星分配任務中“副作用”效應的發展
對幼兒判斷教師分配給故事主人公的星星數量進行統計,得到不同條件下4~6 歲幼兒的判斷結果,描述性統計值見表2。

表 2 幼兒星星分配任務得分
2(“副作用”效價:積極、消極)×3(年齡:4 歲、5 歲、6 歲)×2(規范標準:道德規范、約定規范)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第一,“副作用”效價的主效應顯著,F(1, 479)=結果表明:幼兒在積極“副作用”條件下分配的星星數量顯著多于消極“副作用”條件。幼兒認為,老師會認為帶來積極“副作用”的主人公表現更好,并對伴有積極“副作用”的行為進行獎勵。第二,為了分析幼兒的SEE 是否具有發展趨勢,考察了“副作用”效價和年齡的交互作用,并發現交互作用不顯著,F(2, 479)=0.36,p=0.696。這說明,4 歲、5 歲、6 歲幼兒都會對消極“副作用”給予較少的獎勵,而對積極“副作用”給予更多的獎勵。第三,為了分析幼兒的SEE 在不同規范標準下是否有不同的發展趨勢,考察了“副作用”效價、年齡和規范標準的交互作用,發現交互作用不顯著,F(2, 479)=1.03,p=0.359。這表明,4~6 歲幼兒表現出了對故事主人公心理狀態推斷的不對稱性,但在4~6 歲期間沒有發展變化的趨勢,同時,在不同規范條件下,這種表現完全一致。
4 討論
4.1 4~6 歲幼兒“副作用”效應的發展
本研究首先對Rakoczy 等人(2015)的范式進行了調整。在約定規范標準的故事情境中,使行為者遵守/違背約定規范標準而帶來的“副作用”與規范標準本身有更明顯的區分,并且能夠清晰地體現出故事主人公遵守/違背約定規范標準是引起“副作用”的原因。這樣就能夠使幼兒充分理解主人公的行為會引起怎樣的“副作用”,而不會存在規范標準與行為結果模糊不清的情況。以此保證幼兒在道德規范標準和約定規范標準下的意圖判斷表現是可以比較的。
基于更加合理的范式,本研究考察了幼兒的意圖判斷是否存在SEE 現象。結果發現,利用意圖“有無”判斷,并沒有發現幼兒的SEE;但利用幼兒對教師給故事主人公分配星星數量的判斷,表明相比于消極“副作用”,4~6 歲幼兒傾向于給帶來積極“副作用”的行為者分配更多的星星進行獎勵。這說明,與意圖“有無”判斷任務相比,星星分配任務可以更敏感地考察幼兒SEE 的推理過程。研究還發現,4~6 歲幼兒對故事主人公心理狀態推斷不對稱現象的表現并沒有隨著年齡而變化。這說明,即使是4 歲幼兒,只要條件合適,指標足夠敏感,其意圖判斷的認知加工過程可能與較高年齡段的幼兒相仿。
4.2 意圖判斷中的理性推理觀點
本研究還揭示了,不論是在道德規范標準還是在約定規范標準下,相比于消極“副作用”,幼兒都會給帶來積極“副作用”的行為者分配更多的星星。這一結果符合理性推理的觀點。幼兒在評價主人公是否有意帶來了“副作用”時,會考慮行為與規范標準的關系,而不僅僅是行為的結果。在理性推理的認知加工過程中,相比于遵守規范的行為,違背規范的行為在對行為者及其動機、特質的推斷上更具有“診斷性”或借鑒性。也就是說,幼兒認為違背規范的行為一定是存在原因的。即在消極“副作用”的情境中,主人公事先知曉行為會帶來“副作用”的認知基礎足以讓幼兒推斷出主人公有意違背了規范;但在積極“副作用”的情境下,“事先知曉”的信息就不足以幫助幼兒推斷行為的原因,即主人公是由于動機驅使,還是僅因為規則限制而遵守規范,幼兒是不理解的。
Nichols 和Ulatowski(2007)指出,意圖判斷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事先知曉”。如果個體在理解了行為者事先知曉自己的行為會引起“副作用”,并基于此對行為者“不關心”的態度進行解釋,那么,就會形成一種理性的分析。行為者“不關心副作用”本來是一種中性的態度(Leslie et al., 2006),表面上看,行為者并不是有意帶來了某種特定的“副作用”。但是,在消極情境中,幼兒考慮到行為者事先知曉消極“副作用”會發生,為了避免消極結果,他本來不應該去執行行為,但行為者卻選擇忽視這種可能性。因此,幼兒會傾向于認為主人公有意違背了規范。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在幼兒完成“獎懲”任務后,詢問幼兒“你為什么覺得小明的表現好/不好?”幼兒陳述的理由基本上與上述心理狀態的推斷一致。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對幼兒進行認知引導之前,幼兒對意圖“有無”直接進行判斷,其SEE 并沒有發生;但通過提示幼兒主人公遵守/違背規范的行為,并要求幼兒對主人公的行為表現進行評估后,幼兒對伴隨不同“副作用”的行為卻做出了不同的獎勵預期。這說明,認知推理在幼兒的意圖判斷中起到了作用。然而,在本研究中,幼兒為什么不是完全主動自發地去評價主人公的行為表現,而是需要經過一次提示呢?研究者猜測,有可能是因為幼兒的理性推理能力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因此,不足以讓幼兒獨立完成這個認知加工過程。或許前人研究的數據可以間接為這個猜測提供一些證據。在Leslie 等人(2006)的研究中,并不是所有幼兒都表現出了SEE 現象,仍然有30%~40%的幼兒并沒有將消極“副作用”判斷為主人公有意帶來的。在Rakoczy等人(2015)的研究中,也有50%的幼兒沒有將消極條件下的行為判斷為有意。這或許表明,幼兒的理性推理能力還沒有完全達到與成年人一樣的水平。這可能使幼兒不能自主地表現出SEE。而通過適當的提示來彌補幼兒推理水平上的不足,起到了“觸發”幼兒去推斷行為者心理狀態的作用。
本研究雖然初步證明4~6 歲幼兒行為意圖判斷存在理性成分,但考慮到研究者對影響道德判斷的認知和情緒因素的爭論(Danovitch & Keil,2008; Greene & Haidt, 2002; Haidt, 2001; Nichols &Mallon, 2006; Pizarro & Bloom, 2003),未來可以采用更直接有效的方法探討SEE 是由理性推理導致的,還是由“副作用”效價引發的責任歸因或者道德情緒所帶來的意圖判斷偏差導致的。前人研究將“副作用”效價和規范標準兩個因素混淆起來,即積極情境對應遵守規范,同時,消極情境對應違背規范。這樣就不能探討幼兒SEE 形成的原因(Uttich & Lombrozo, 2010)。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行為者是否違背規范標準與“副作用”效價是相互獨立的因素,這就會形成不同于傳統SEE 案例的其他類型案例。例如,行為者違背了一項法律,但帶來了積極“副作用”,這個“副作用”在大多數被試看來是好的結果,這個行為會被判斷為有意的;如果行為者因為遵守法律帶來了消極“副作用”,這個行為就會被判斷為無意的(Knobe, 2006, 2007)。
5 結論
(1)使用星星分配數量作為指標考察幼兒的意圖判斷更敏感。(2)幼兒會把違背規范的行為推斷為有意的,遵守規范的行為推斷為無意的,且這種表現在4~6 歲之間具有穩定性。不同規范標準下,幼兒的這一表現沒有差異。(3)研究結果支持了SEE 理性推理觀點。
致謝誠摯地感謝馬麗老師在本研究數據采集過程中給予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