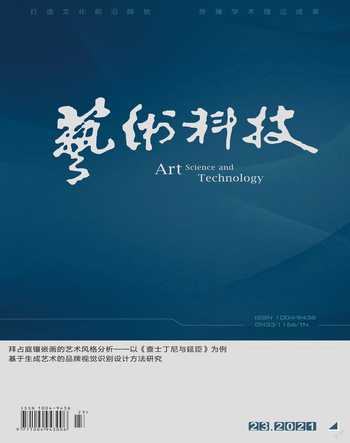拜占庭鑲嵌畫的藝術風格分析
李宇涵,李芃


摘要:拜占庭的繪畫藝術在中世紀歐洲藝術中有很高的地位。文章從拜占庭鑲嵌畫的發展歷史和風格出發,分析《查士丁尼與延臣》鑲嵌畫的創作背景及內容,從構圖、顏色、材質等方面分析作品的藝術表現,從而思考并總結拜占庭藝術對現代藝術設計的參考意義,以及鑲嵌畫藝術表現形式的變化與展示方式。
關鍵詞:拜占庭;鑲嵌畫;藝術風格
中圖分類號:J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23-0-03
1 拜占庭鑲嵌畫的發展歷史及風格
拜占庭帝國其實是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后的東羅馬帝國,它信奉東正教,承襲了希臘語,因地處東、西文明的交匯點,在繼承羅馬藝術,注入基督教文化特色的基礎上,又吸收了東方的繪畫藝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藝術風格,并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藝術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它的繪畫藝術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發展階段:早期、中期和晚期[1],不同時期的鑲嵌畫受社會發展的影響,在內容、主題、風格的選擇和體現上各有不同。早期的發展時間為公元4世紀中期到6世紀末,這一時期拜占庭帝國正在轉型,所以鑲嵌畫具有多元性,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羅馬繪畫的古典與傳統,透露出自然主義的精神,東方藝術中重色彩而不注重造型的描繪在畫中也有體現,其人物形象較為呆板,身長比例不做細節處理,主要以圖示化的方式強調鑲嵌畫的教化功能。中期的發展時間為公元7世紀到11世紀[1],這個時期是拜占庭鑲嵌畫發展的黃金期,主題多為宗教事件、圣經故事或宗教人物等,色彩艷麗,造型概括,個體鮮明而突出,較少有背景,更趨向于扁平化,給信徒一種崇高和神圣的感受。晚期的發展時間為公元11世紀后半期至15世紀中期[1],國家衰敗導致藝術發展緩慢,鑲嵌畫失去了原有的統一性和整體感,在繼承西歐和東歐國家藝術形式的過程中發展形成了新的風格,題材選擇更加自由,人物形象有了性格特征的表現,動作由靜態轉為動態,體現出寫實的傾向,畫面注重敘事性和聯系性,也開始講究新的色彩組合或采用具有地方文化特點的色彩[2],催生了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
2 《查士丁尼與延臣》鑲嵌畫的產生背景及內容闡述
《查士丁尼與延臣》鑲嵌畫(見圖1)的創作時間為公元547年,尺寸為264cm×365cm,鑲嵌在圣維塔爾教堂的拱形墻壁中。這個教堂呈八角形,屬于集中式建筑結構,內部鑲有華麗的大理石浮雕和鑲嵌畫,雖外表樸素但內部精美絢麗,是查士丁尼皇帝為紀念臘文納城市光復而建造的。《查士丁尼與延臣》鑲嵌畫是當時的工匠們為了紀念和頌揚查士丁尼的偉大和他為國家帶來的勝利而鑲嵌于墻壁上的。
畫面主要展現的是查士丁尼皇帝和他的侍從手捧圣經、圣器獻祭的場景,畫中共有13個人,查士丁尼皇帝位于中心,他頭戴珠玉帽,身穿紫紅色長袍,手拿盛裝圣水的器物。他的右側是拉文納大主教,身穿白色和黃色衣服,手持鑲嵌綠寶石的黃色十字架,二人之間只露出上半部分身體的人據推測是阿爾罕塔利亞,畫面最右側兩位為助祭者,分別手拿圣經和油燈。查士丁尼皇帝的左側有2名穿紫紅色和白色衣服的貴族及5名拿著盾牌和矛的侍衛,他們筆直且踮腳站立,表情呆板嚴肅,凝視前方,好似在舉行某個儀式。畫面中12名延臣與基督的十二門徒的數量正好一致,而查士丁尼皇帝頭上的光芒也寓意著政權與神性的融合,他好似擁有了神的地位,整幅畫展現出濃厚的宗教色彩。
3 《查士丁尼與延臣》的藝術表現與風格
3.1 藝術風格的體現
《查士丁尼與延臣》鑲嵌畫主要采用了寫實、抽象的表現手法,在融合多國藝術的基礎上自成一派,現在來看它更像是馬賽克風格的一種具體體現。這種風格最初用于建筑室內裝飾,隨著時代的發展,在服裝、游戲、工藝品中廣泛體現,它的特點在于材料和色彩的豐富性以及塊料的拼貼方式或小色塊的排列組合。在《查士丁尼與延臣》鑲嵌畫中,作品更多體現出神權與皇權的交融,以及宗教的神圣和嚴謹[3],其中的盾牌、經書、矛等物件,以及人物形象的面部表情和發型樣式等都以較寫實的方式展現出來,服飾的精細程度也根據權力和職能的不同有所區分。查士丁尼皇帝位于中心處,兩側為貴族和大主教,神職人員及侍衛在外側,編排上有著與事實相通的考量。在人物的身高比例上,采用了抽象的表現手法,將身體的比例拉長,頭身比例接近為1∶9,顯得高大和莊嚴,給人以壓抑感,體現出秩序和冷靜,強調權力的至高無上和不可褻瀆。這是拜占庭藝術風格的體現,這些表現手法讓人物成為了一種抽象符號[4],用以傳達蘊含的文化、知識和思想。
3.2 材質的選擇與肌理的運用
鑲嵌畫興起于公元2世紀,它是一種肌理的表現形式,常使用小色塊且形狀不規則的材料,如玻璃、玉石、陶瓷、大理石等,將其混合鑲嵌在墻壁和平面上,起到裝飾的作用[5]。拜占庭鑲嵌畫主要以彩色玻璃片和大理石子為材料,其堅硬、耐腐蝕,在陽光的照射下,玻璃片可以折射出彩色的光,營造出熠熠生輝、神秘和夢幻的視覺感受,解決了教堂內部光線不足的問題。因教堂墻壁有拱形、半球形等多種形狀,拜占庭藝術家在鑲嵌時結合空間、教徒觀察藝術作品的距離和從下往上仰視的習慣,改變了人物的大小比例,從而達到較為平衡和真實的視覺效果。
鑲嵌畫的工藝從涂上一層細膩的灰泥開始,這層灰泥用石灰和磚塊粉末混合制成,涂好后再用尖銳的利器在灰泥層上刻畫出輪廓線,然后用不同的顏色標示出作品的圖案和背景,根據顏色放置合適的石塊(見圖2)。如采用玻璃材質,則會在玻璃鑲嵌片的后面先鋪上一層底色,金色和銀色用金箔和銀箔做底。此外,根據鑲嵌面的弧度以不平行的方式做拼貼粘黏,使其相互擠壓而更加牢靠[6]。拜占庭鑲嵌畫經過細密的拼貼,利用自然材料的屬性體現出不平整的視覺形式[7],利用肌理的屬性給平面視覺上的“面”帶來了平滑和粗糙感,與直接以繪圖形式呈現的壁畫相比,更具生動性,其裝飾性也在空間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延伸,從而有了動態的美,視覺體驗進一步得到了滿足。
3.3 色彩運用分析
從整體來看,《查士丁尼與延臣》的鑲嵌畫顏色純度和明度較高,畫面氛圍和諧、典雅,充滿秩序和理性,色彩感受豐富而熱烈。背景采用金色,除了體現出高貴、華麗的視覺感受以及永恒不變、真誠的基督教寓意外,也代表著光芒,即查士丁尼皇帝的神性光輝,結合自然光所帶來的金光閃閃的視覺效果,更容易使教徒產生身處天堂的幸福、虔誠和滿足感。在基督教題材的眾多繪畫作品中,顏色與人物常有一定的聯系或象征含義,如圣母瑪利亞常穿藍色的衣服,是神圣的象征,君王、富家子弟常穿紫紅色衣服,象征高貴和威嚴,圣徒穿著黃色或淺藍色[6],代表著神圣或不潔,此外白色象征著純潔、生命,綠色象征著和平、安寧[8]。在《查士丁尼與延臣》這幅鑲嵌畫中,君王穿著紫紅色,拉文納大主教穿著黃色和白色,其余助祭者的衣服為白色和少量的紫紅色,與君王相呼應,有眾星捧月的隱喻。左側侍衛的衣服顏色較為豐富,裝飾性強。由此可以看出,這幅鑲嵌畫沒有完全古板地遵循基督教色彩的規律,當時可能受東方藝術的影響,更關注畫面明快的視覺效果及宗教傳播教義、凝聚人心的意義。
此外,該鑲嵌畫四周裝飾物的顏色皆與主畫面人物中的顏色有所呼應,整體色調上達到了視覺的統一與和諧,又在和諧中存有塊面的對比色與鄰近色變化。
3.4 畫面構圖與線條表現
《查士丁尼與延臣》鑲嵌畫為橫式和中心對稱構圖,其對稱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畫面構圖的對稱,另一個是圖案的對稱。對稱并非以絕對對稱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強調在視覺上,物體的重量分布、描繪程度,視覺中心的左右兩部分都體現出一種均衡和穩定的感覺,從而展現出對稱的美感[9]。畫面中人物腳呈外八狀,由中心向兩側并排分開站立,具有穩定性。人物的位置安排上強調層次感和前后的空間感,在有限的平面中也注重三維效果的體現,寫實感強[10]。以查士丁尼君王為中心,右側人物較為稀疏,左側人物較為緊密,畫面富有節奏感且主次分明,查士丁尼君王頭上有光圈,在視覺上略高于眾人,突出了他的崇高地位及權力。從圖案角度來看,畫面中物件的裝飾元素,如經書上的綠葉與花紋、十字架上的鑲嵌、盾牌上的字母符號都以左右或上下對稱的形式來表現,鑲嵌畫四周的裝飾柱及頂部裝飾除了左右對稱外,還有疏密之分,左右兩側元素小,排列密集,頂部元素少,整齊而均衡。這些裝飾在豐富畫面的同時也增強了色彩的豐富性和畫面的可視性,起到了調節的作用,并將人物歸納在一個秩序的塊面中,人物形象統一且觀者視覺注意力集中。
“點線面”在畫面中同樣有所體現,鑲嵌畫由形狀不一的點經過排列和粘黏之后組合而成,也就是一個面,其中點根據建筑物的表面結構不同而有了多種路線走勢,在顏色的輔助下能更易清晰地看見由點緊密排列而形成的直線或曲線,線的方向和軌跡為觀者圈出了形狀各異的大小塊面,而點的排布經過并置、重疊、穿插、擴散等手法具有了豐富的變化[7]。從《查士丁尼與延臣》鑲嵌畫中可以看出點線面的具體表現,如盾牌上的基督教符號“Χρ”即是線與點的組合,寓意天定的勝利,選用藍綠色的圓點沿其字母的筆畫進行裝飾,為冷硬的盾牌增添了一絲美感。而查士丁尼的服飾和帽子,通過點的并置、排列、旋轉及形狀大小變化,如圓形、水滴形,加上互補色、同類色的搭配有了律動感,其鑲滿了五彩珠玉的帽子也突出了君王的高貴,強化了主體人物的視覺美感。
與中國白描畫中講究線條的粗細變化,運用線條構造服飾的疏密層次或人物的形態、突出柔和與意境的方式不同,在《查士丁尼與延臣》鑲嵌畫中,可以看到線條前后兩端及中間均無粗細的變化,線條鑲嵌粗獷、厚實和嚴謹,運用十分節儉、可靠,與西方的實用性文化相契合,突出了西方追求理性與寫實的態度。
4 結語
拜占庭鑲嵌畫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雖然作品一直以基督教題材為主,但始終追求畫面元素與主體的真實形態,從而進行抽象及高度概括性的表達,通過構圖、色彩和材質的選擇使畫面裝飾性得到進一步增強,并突破了平面的限制轉而在空間中營造氛圍美。拜占庭鑲嵌畫的藝術特點為現代設計創作提供了參考。首先,鑲嵌畫中的點在排列方式和布局上可以有所突破,通過不同大小點的分散或緊湊排列打造遞進、擴散等效果,或直接使用點元素創作圖形,雖然圖形沒有明確的邊界線但依然具有識別度。其次,可采用鑲嵌畫的創作形式,但改變材料和主題的選擇,運用多種綜合媒材創造多種肌理質感,探索平面外的視覺呈現效果。最后,鑲嵌畫的視覺展示方式不必拘泥于建筑載體,可以采用雕塑、AR、動態、物件等多種形式。
參考文獻:
[1] 胡長江.拜占庭帝國的繪畫藝術及其多樣性特征初探[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6(1):55-60.
[2] 梅穎瑩.拜占庭鑲嵌畫初探[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0.
[3] 沙美,徐雷.圖像學角度下拜占庭風格的地域性研究[J].大眾文藝,2019(21):120-121.
[4] 邵天澤.拜占庭藝術初探[J].黑龍江教育(理論與實踐),2018(4):91-92.
[5] 荊銀萊.淺析綜合材料在西方綜合繪畫中的演進[J].明日風尚,2017(3):123.
[6] 趙亮.拜占庭教堂鑲嵌壁畫藝術特色探析[D].南京:南京藝術學院,2010.
[7] 李蘭婷.拜占庭風格鑲嵌畫的視覺藝術特征[J].芒種,2014(23):263-264.
[8] 楊健吾.基督教的色彩觀念和習俗[J].文史雜志,2003(4):30-32.
[9] 郭喜邦.中國畫與西洋畫的構圖差異思考[J].美與時代,2019(11):22-23.
[10] 董婷,劉虹.談構圖在繪畫創作中的意義[J].美術教育研究,2021(7):92-93.
作者簡介:李宇涵(1997—),女,湖北松滋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視覺傳達。
李芃(1963—),男,湖北武漢人,碩士,教授,研究方向:視覺傳達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