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克·福爾摩斯:世界上最著名的偵探
〔英國〕約翰·薩瑟蘭

“我考慮殺掉福爾摩斯……把他干掉,一了百了。福爾摩斯占據了我太多的時間。”阿瑟·柯南·道爾1891年11月在一封給母親的信中抱怨說。母親堅決不同意他的這種念頭。母親告訴他,除了寫好福爾摩斯,別的他什么也干不好。后世的讀者十分同意柯南·道爾母親的看法。夏洛克·福爾摩斯不僅是柯南·道爾這位作家最好的成果,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位作家所能創造的最佳成果之一。私家偵探福爾摩斯住在貝克街221號B,哈德孫夫人是女房東,華生醫生沒有結婚之前也住在這里,但就在這個毫不起眼的地方,走出了一個可以和哈姆雷特、堂吉訶德、匹克威克、斯文加利(英國小說家喬治 · 杜 · 莫里耶于1894年出版的經典小說《特麗爾比》中的音樂家,他使用催眠術控制女主人公特麗爾比,使其唯命是從,成為他牟利的工具。后人用斯文加利來形容那些對他人具有極大影響力和控制力的人。——譯注)、哈利·波特比肩的文學人物,名氣突破了文學圈。
福爾摩斯帝國的版圖從《血字的研究》開始。這本小書為貧困的作者(當時他還是一名苦苦掙扎的醫生)帶來了25英鎊的收入;現在,“夏洛克”已經成為電視劇和電影行業的品牌,在全世界產生了數千萬英鎊的利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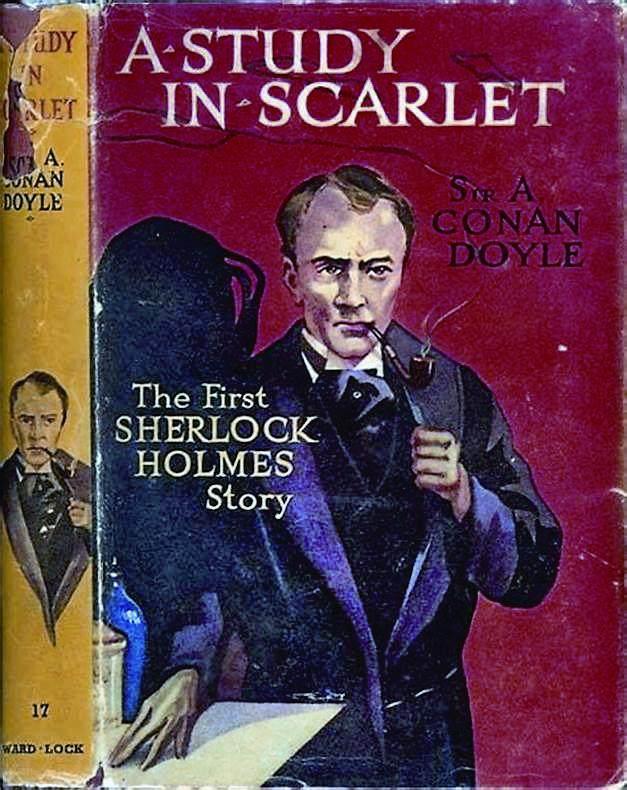
這是怎么發生的?維多利亞時代眾多偵探小說中的主角紛紛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夏洛克·福爾摩斯何以繼續收獲一代又一代讀者的青睞?我們可以條分縷析,在眾多因素中找到答案。但首先還是來看一下福爾摩斯創造者的生平吧。

道爾1859年生于愛丁堡,父親是愛爾蘭人,酒鬼,晚年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柯南·道爾在斯托尼赫斯特的天主教耶穌會大學接受教育,16歲時在奧地利待了一年,回國后進入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學習。1880年,道爾作為一條捕鯨船的隨船醫生,在北極地區待了七個月。1881年,他順利畢業,隨后去了非洲。1882年,在樸茨茅斯開了一家診所。1885年底,他的年收入已經達到了300英鎊。他和他的一位病人的妹妹結了婚。道爾在行醫時已經開始寫作,1886年,他開始寫一些以“業余私家偵探J.謝林福特”為主角的小說,結果就誕生了夏洛克·福爾摩斯系列故事里的中篇小說《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但沒有任何一家好出版社愿意出版這篇小說。它最終的出路是先在一本雜志上作為“圣誕節贈品”連載刊登,然后被當作廉價小說(當時叫“一先令驚險小說”)推向大眾。
《血字的研究》中有發生在美國猶他州和英國倫敦的兩起謀殺案,這吸引了普通讀者的興趣。道爾緊隨其后又發表了一篇福爾摩斯探案故事——《四簽名》(The Sign of Four)也受到了讀者的歡迎,但是直到1891年初,道爾將六則短篇小說投給《河濱雜志》(Strand Magazine)之后,“福爾摩斯熱”才真正開始。看到投稿后,《河濱雜志》的編輯意識到“他是埃德加·愛倫·坡之后最偉大的短篇小說家”。道爾寫這些小說的真正目的是糾正當時偵探小說中的“重大缺陷”——缺乏邏輯。《河濱雜志》所刊登的短篇小說由優秀的插畫師西德尼·佩吉特配圖,他給福爾摩斯配上了標志性的獵鹿帽和鷹鉤鼻造型。
道爾的心從來沒有真正放在偵探小說上,但是這些小說在英國和美國深受歡迎,和它們相比,道爾的其他作品就遜色多了。1893年,他在《最后一案》中讓福爾摩斯死于萊辛巴赫瀑布(Reichenbach Falls),結果,《河濱雜志》一夜之間就丟失了兩萬名訂戶。這件事甚至驚動了英國高層,許多人對此表示不滿。
盡管道爾逐漸討厭福爾摩斯,但不可否認的是,讓他成為有錢人的正是福爾摩斯——道爾是19世紀末英國最富有的作家之一。
偵探小說的發展
在19世紀,偵探小說已經演變成一種暢銷文學類型。偵探小說得以發展的歷史條件是1878年倫敦刑事調查處等諸如此類的犯罪調查部門的建立,發揮相同作用的還有埃德加·愛倫·坡所寫的那些具有開拓意義的短篇小說,其中最著名的“密室類”經典當屬1841年出版的《莫格街謀殺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和福爾摩斯一樣,小說中的偵探奧古斯特·杜平完全依靠“推理”來破案。這也是福爾摩斯破案的不二法則。在《四簽名》中,他兩次明確地表達了這一理念:“我曾經和你說過多少次,當你把絕不可能的因素都除出去以后,不管剩下的是多么難以相信的事,那一定就是實情。”對道爾產生影響的還有偵探小說界先驅人物、法國作家埃米爾·加伯利奧(Emile Gaboriau,1832—1873)以及他筆下系列小說的主角勒考克。
廉價小說的市場
一個渴望廉價小說的大眾閱讀市場,對偵探小說的發展也很重要。1870年,英國頒布了《初等教育法》,大批年輕、受過教育的讀者群應運而生,但他們手頭拮據,而福爾摩斯探案的故事就在這時閃亮登場。更重要的是,道爾的第一篇故事屬于廉價小說,刊登該篇小說的《河濱雜志》當時售價為6便士(相當于現在的2.5便士)。窮孩子也能享受得起福爾摩斯探案故事帶來的刺激。
道爾給偵探小說這種文學類型帶來了一些革新。從整體上看,這類小說贊揚了英國人的“業余主義”(amateurism)文化(比如,道爾喜愛板球運動,但只在業余時間玩玩而已)。福爾摩斯非常出色,但他沒有專門的職業。雖然他比那些教授聰明,但他一直懶得去拿醫學學位。
正如《血字的研究》第一章中所說,福爾摩斯是一位“私家偵探”。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的偵探則是官方的。1852年,狄更斯在《荒涼山莊》(Bleak House)中首次推出了蘇格蘭場的偵探貝克特。私家偵探的從業人員因為1857年《婚姻訴訟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的頒布迅速壯大。但福爾摩斯是一位“有紳士風度”的偵探,絕不會通過偷窺去調查出軌,因為那“不是紳士所為”。他渾身洋溢著上層社會的騎士風度和英式禮儀。在《波希米亞丑聞》(A Scandal in Bohemia)中,福爾摩斯與罪犯艾琳·艾德勒發生了一次戀愛事件,但他的表現無可挑剔,有著真正的英國范。
愚蠢的朋友,高明的罪犯和法醫學
道爾將三項創新引入了偵探小說的敘事,它們已經成為這種文學類型不可或缺的規范。他的第一個創新是所謂的“愚蠢的朋友”,你一定要將所有的事情都解釋給他聽(實際上就是講給讀者聽)。在福爾摩斯探案故事中,華生醫生就是這樣的伙伴。這位善良的人有許多近親,例如阿加莎·克里斯蒂偵探小說中波洛偵探的“笨伙伴”黑斯廷斯少校,另外還有其他小說中的此類人物。

道爾的另一個創新是“高明的罪犯”或“犯罪界的拿破侖”(Napoleon of Crime),這些人比行事魯莽的警察要聰明不知道多少倍。在福爾摩斯探案故事中,莫里亞蒂教授就是此類罪犯。
莫里亞蒂出身名門,受過極好的教育,在數學方面天賦異稟,二十一歲時寫了一篇關于二項式定理的論文。他憑著這篇論文在一所大學謀到了數學老師的教職。在所有人看來,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此人繼承了家族的兇殘。他天生就是罪犯。他是犯罪界的拿破侖,華生。倫敦城中一半的犯罪活動、幾乎所有未被偵破的犯罪活動都是他組織的……
[《最后一案》
(The Final Problem),1893]
第三項創新是用“法醫學”來破案。我們在《血字的研究》第一章中首次遇到福爾摩斯時,他正在貝克街的實驗室中研究血紅蛋白。他對心懷疑慮的華生說:
“這是法醫學數年來最為實用的發現。難道你還不明白,它可以幫助我們精確地鑒別血跡嗎?”
在第二篇福爾摩斯探案故事《四簽名》中,道爾說指紋是偵探破案的重要方法。
匪夷所思和邏輯混亂
道爾認為偵探小說并不屬于文學。他覺得自己經過周密研究之后寫的歷史小說才是后人最珍視的作品。他錯了。他根據自己心中的高低之分,在寫福爾摩斯故事時就不那么用心了。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一些匪夷所思、邏輯混亂之處,有時甚至是荒誕不經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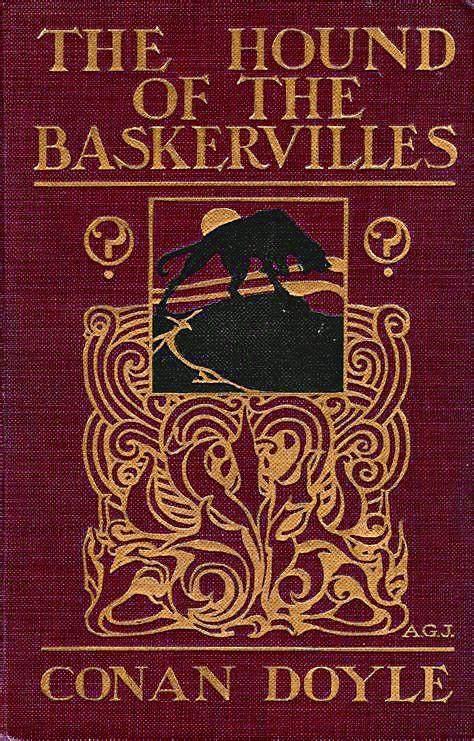
比如,《巴斯克維爾的獵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1902)里有位貴族被“魔鬼般的獵犬”嚇死了,后來才發現那不過是條從富勒姆路上的狗販子那里買來的雜交犬。這條可憐的狗眼睛被涂了發光材料,以制造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效果。任何一位愛狗人士都可以站出來說這太難了。如果可以利用格林彭沼澤的流沙來殺人,有什么樣的罪犯還會大費周章地用那種毫無必要、極其復雜的方法去作案呢?
在福爾摩斯探案故事中,道爾的最愛是《帶斑點的帶子》(The Speckled Band)。小說講的是一樁密室謎案:一條訓練過的蛇(印度沼澤地蝰蛇,但這一物種并不存在)能夠按照口哨的命令,沿著房間內的鈴索爬動。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因為蛇不會聽從命令。那些喜歡挑錯的讀者很容易在福爾摩斯探案故事中找到破綻。
但時間和讀者的喜愛都已經證明這些漏洞并不重要。在數百萬讀者當中,大部分人都會毫無障礙地接受這五十六篇小說在邏輯、時間和細節方面的瑕疵。這些故事太好看了。
與醫學的聯系
文學史家注意到,現實或小說中的“偵探學”都與醫學在19世紀取得的進步緊密相關,觀察犯罪線索和解釋病癥之間的關系亦然。“你看了,但你沒有觀察。”福爾摩斯在《波希米亞丑聞》中這樣批評華生。現實中的大部分醫生也是這樣。1854年,約翰·斯諾發現倫敦傳播霍亂的不是有毒的空氣,而是被污染了的水。和福爾摩斯一樣,斯諾做到了“抓住線索”。
福爾摩斯是學醫出身,而道爾本人也是歐洲頂尖醫學院的畢業生,受過專門訓練且有行醫執照。在愛丁堡大學求學期間,道爾深受導師約瑟夫·貝爾教授“演繹推理法”的影響。道爾曾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
(約瑟夫 · 貝爾)對病人說:“嗯,伙計,你當過兵。”
“是的,先生。”
“剛退伍不久?”
“是的,先生。”
“是皇家蘇格蘭高地團?”
“是的,先生。”
“非戰斗軍官?”
“是的,先生。”
“駐扎在巴巴多斯?”
“是的,先生。”
“大家看看,”(貝爾)解釋道,“這位先生彬彬有禮,卻沒有脫帽致意,因為他們在軍隊中不這樣做,但如果他已經退伍很久的話,應該已經學會了平民社會里的禮節。他不怒自威,一看就知道是蘇格蘭人。至于巴巴多斯,他來看病是因為得了象皮病(Elephantiasis),這病發生在西印度群島,不在英國。”
比較一下《血字的研究》第一章中福爾摩斯和華生初次見面時的場景:
“你好。”他熱情地打招呼,和我握手,我簡直不敢相信他竟有那么大的力氣。“我想,你去過阿富汗。”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我驚訝地問。
頹廢
和奧斯卡·王爾德一樣,福爾摩斯的名望在1890年代達到頂峰,那時的文學界盛行“頹廢風”。例如《四簽名》的開頭:
“今天用的是什么?”我問他,“是嗎啡,還是可卡因?”他懶懶地從剛打開的一本舊書上抬起頭,“是可卡因,溶液濃度百分之七。想不想試試?”
華生醫生是愚蠢朋友中最不頹廢的,他拒絕了福爾摩斯的邀請。如果有大膽的讀者和批評家想在這兩位同居一室的男性之間找出一絲曖昧意味,對此的回答只可能有一種:“當你把絕不可能的因素都除出去以后,不管剩下的是多么難以相信的事,那一定就是實情。”
不,或許也不一定吧。
(錢云華: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郵編:214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