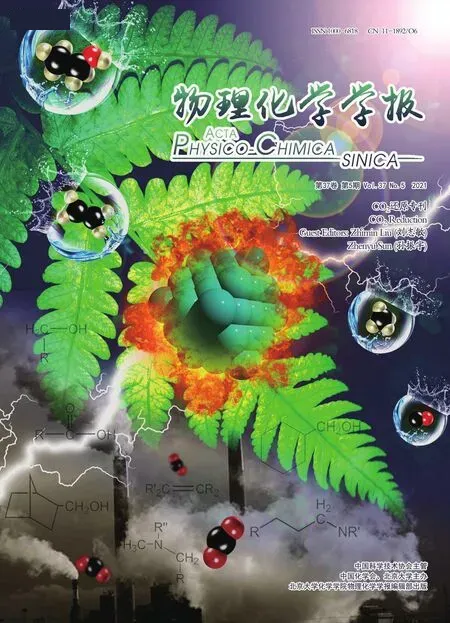鈷(II)基分子配合物用于光催化二氧化碳還原
張繼宏,鐘地長,魯統部
天津理工大學新能源材料與低碳技術研究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天津 300384
1 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和能源需求提升,尋找經濟和可再生能源是人類21世紀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1,2。目前的能源結構中,85%能源由化石燃料提供。由于化石燃料的不可再生性,將使得其變得更加昂貴且難以獲取;另外,化石燃料的使用,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CO2)等溫室氣體,對全球氣候產生嚴重影響,威脅著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尋找可替代化石燃料的能源載體非常重要3,4。
受自然界綠色植物光合作用的啟發,研究者考慮利用太陽光將CO2轉化為燃料或高附加值化學品,這不僅可以降低大氣中CO2濃度,緩解環境問題,還可以將太陽能轉化成化學能,實現太陽能的存儲,解決能源危機5-11。然而,由于CO2的惰性,直接用一個電子將CO2轉化為CO2·-非常困難,需要非常負的氧化還原電勢(見式(1))12-14;另一種相對有利的途徑是通過質子輔助的多電子轉移來還原CO2,使CO2可以在相對較正的氧化還原電勢下還原為一氧化碳(CO),甲酸(HCOOH),甲醇(CH3OH),甲醛(HCHO),甲烷(CH4)或乙酸(H2C2O4)等(見式(2)-(7))15-18。從熱力學上,多質子多電子轉移反應有利于CO2還原形成HCHO、CH3OH、CH4等還原產物,但隨著質子和電子的增加,動力學勢壘通常也將增加,所以將CO2還原成HCHO/CH3OH/CH4等比CO/HCOOH更難19。同時,熱力學有利的質子還原反應(-0.41 V vs NHE)還將與CO2還原競爭20,21。因此,開發高效、高選擇性的廉價催化劑是實現CO2還原的關鍵。

光催化CO2還原體系主要分為均相和非均相光催化體系。非均相體系主要是利用具有納米結構的半導體材料或者金屬/半導體復合材料等為催化劑,通過光照,利用價帶躍遷到導帶的電子直接實現CO2還原。非均相催化劑一般具有穩定的催化性能,也能較好循環利用,但其復雜結構導致催化機理難以揭示。均相光催化CO2還原體系是通過吸光基團吸光和一系列質子和電子轉移來實現CO2還原22-27。體系中一般包含分子催化劑(CAT),電子犧牲劑(SD)和光敏劑(PS)。催化反應的第一步是在光照下將PS激發到激發態PS (PS*),被激發后的PS*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發生猝滅:氧化猝滅和還原猝滅(圖1)。在氧化猝滅中,電子從PS*轉移到CAT,生成PS+和CAT·-,隨后PS+與SD反應,而CAT·-進一步向結合的CO2提供電子實現CO2的還原;在還原猝滅中,激發態的PS*獲得SD中的電子,生成強還原劑PS·-和SD+,PS·-將電子轉移到CAT形成CAT·-,產生的CAT·-進一步還原結合的CO2分子。雖然反應路徑不同,但在這兩種途徑中都必須要形成CAT·-,因此CAT·-對CO2結合和轉化是非常重要的活性中間體。相對于非均相催化劑而言,均相催化劑具有確定的空間結構,有利于結構設計和優化,也有利于研究催化機理和建立構效關系,因而在催化CO2還原方面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28。

圖1 分子催化劑在光催化CO2還原過程中的兩種途徑Fig. 1 Two reaction paths of photochemical CO2 reduction in homogeneous catalytic systems.
在均相催化劑中,貴金屬Re、Ru、Ir等的配合物均具有較為優異的光催化CO2還原活性,但由于其昂貴的成本將限制其大規模應用,非貴金屬Fe、Co、Ni、Mn、Cu等的配合物因而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29。Co作為VIII族非貴金屬,由于其廉價、儲量豐富和多樣的氧化態,在非貴金屬催化劑用于光催化CO2還原的研究中尤其受到關注30,31。1984年,荷蘭烏得勒支大學Tinnemans等人以Co(II)大環配合物作為催化劑32,構建了第一個基于非貴金屬催化劑的均相光催化CO2還原體系。隨后研究者開展了大量基于不同配體的Co(II)配合物用于光催化CO2還原方面的研究。
本論文主要從配體設計角度出發,介紹Co(II)配合物分子催化劑在光催化CO2還原方面的最新研究進展,重點討論配體設計和修飾對催化劑效率,選擇性和穩定性的影響,總結構效關系。為了更好地分析配體結構對催化效果的影響,我們根據配體類型將鈷分子催化劑分為:(1) 基于大環配體鈷分子催化劑;(2) 基于吡啶類配體鈷分子催化劑;(3) 基于卟啉或卟啉衍生物配體鈷分子催化劑;(4) 基于非平面N4配體鈷分子催化劑。
2 具有光催化CO2還原活性的鈷分子催化劑
2.1 基于大環配體的鈷分子催化劑
許多配體被用來構建金屬配合物并用于催化CO2還原,其中大環配體能夠穩定催化循環中形成的中間體,從而提高催化活性。1984年,荷蘭烏得勒支大學Tinnemans等人使用三種四氮雜大環配體合成系列Co(II)配合物(C1-C3;圖2),它們可作為分子催化劑在水溶液(pH 4.0)中實現光催化CO2還原。以[Ru(bpy)3]2+作為光敏劑和抗壞血酸鹽(HA-)作為電子犧牲劑,C1和C2光催化CO2還原成CO的選擇性分別為22%和32%,C3對CO選擇性低于1% (表1,Entries 1-3)32。在光照18 h后,C1和C2的TONCO分別為22和9.6。作者提出的催化機理是:抗壞血酸鹽使激發態的*[Ru(bpy)3]2+發生還原猝滅生成還原性更強的[Ru(bpy)3]+(圖3,步驟1和2),然后[Ru(bpy)3]+將[CoIIL] (L代表C1-C3的配體)還原成[CoIL] (圖3,步驟3)。在質子溶劑中,[CoIL]與質子結合生成[CoIIILH]-(圖3,步驟4),接下來可能經歷兩種不同的途徑:一種是[CoIIILH]-與另一質子反應生成H2(途徑a),另一種是CO2插入Co―H鍵形成[CoIIILCOOH],然后結合一個質子釋放出CO和H2O(途徑b)。最后[CoIIIL]與抗壞血酸鹽反應,被還原成[CoIIL] (圖3,步驟5),完成一個催化循環。美國Fujita教授等人隨后用瞬態光譜證明了光催化反應中中間體[CoIL]和相應的[CoL(CO2)S] (S = 溶劑)的形成33-36,說明在CO2存在的情況下,途徑b是形成CO的有效路徑。

圖2 基于大環配體的鈷分子催化劑Fig. 2 Chemical structures of Co molecular complexes based on macrocyclic ligands.

圖3 Tinnemans等人提出的CoIIL配合物光催化還原CO2為CO機理Fig. 3 Proposed mechanism of photochemical reduction of CO2 to CO by Tinnemans et al.
1995年,美國Yanagida和Fujita等報道了另一Co(II)大環催化劑(C4;圖2)34,以三聯苯(pterphenyl)作為光敏劑,三乙醇胺(TEOA)作為電子犧牲劑,C4在CH3CN/MeOH混合溶劑體系中可以光催化還原CO2為CO和甲酸,C4表現出良好的選擇性和高量子產率(表1,Entry 4)。當用吩嗪(phenazine)作為光敏劑和三乙胺(TEA)作為電子犧牲劑時,CO2還原成甲酸的選擇性明顯提高(>90%),量子效率為0.07 (表1,Entry 5)35。此外,他們進一步探究了C4催化劑中大環配體的結構對催化活性的影響(表1,Entries 6-10)36,37。他們發現:在相同條件下,帶有更多甲基取代基的C6光催化CO2還原的活性明顯比C5的低(表1,Entries 6和7);將C4中四氮雜大環配體中N-甲基化后形成的C7不能實現對CO2的還原(表1,Entries 8和9)。這些實驗結果表明,太多甲基取代基可能會導致位阻太大,阻礙催化中心與CO2結合,從而影響CO2還原催化活性。他們還發現沒有N―H鍵的四氮雜大環Co(II)配合物(C9;圖2)光催化CO2還原活性比C8更低(表1,Entry 10)。除N4大環外,研究者還設計合成了基于N5大環的鈷分子配合物(C10;圖2),發現以fac-Ir(ppy)3為光敏劑和TEA為電子犧牲劑時,它能光催化還原CO2為CO,TON達到270,對CO的選擇性達到97% (表1,Entry 11)38。有意思的是,當催化中心換成Fe后,在相同條件下,CO2的還原產物為甲酸鹽。
2.2 基于吡啶基配體的鈷分子催化劑
吡啶類化合物是合成鈷分子催化劑的常用配體,將Co(II)與聯吡啶(bpy)配位形成的[Co(bpy)3]2+(C11;圖4)和雙金屬配合物C12和C13 (圖4),在光照條件下能將CO2還原為CO,但它們的TON和選擇性都較低(表1,Entries 12-14)39,40。2016年香港城市大學Lau和法國Robert等人報道了鈷與四聯吡啶形成的催化劑C14 (圖4),在[Ru(bpy)3]2+和1,3-二甲基-2-苯基-2,3-二氫-1H-苯并[d]咪唑(BIH)的CH3CN/TEOA體系中,光催化CO2還原成CO的TON高達2660,選擇性為98%,量子效率(ΦCO)達6.74% (表1,Entry 15)41。用吡啉(purpurin)替換[Ru(bpy)3]2+作為光敏劑,該催化劑仍表現出較高的活性,TON達790 (表1,Entry 16)。隨后Chen, Lau和Robert等人進一步合成了一種基于四聯吡啶雙核鈷催化劑(C15;圖4)42,他們發現C15在不同pH值溶液中能將CO2選擇性的還原成HCOO-或CO。在弱堿性乙腈溶液中,CO2的還原產物為甲酸,TON達到821,選擇性為97% (表1,Entry 17);在弱酸條件下,CO2的還原產物為CO,TON達到829,選擇性達99% (表1,Entry 18)。機理研究表明催化過程由兩個Co(II)協同作用完成。2018年,Fujita課題組合成了兩個具有五齒聚吡啶配體的Co(II)配合物(C16和C17;圖4)43。當用C16作為催化劑,[Ru(bpy)3]2+作為光敏劑,TEA作為電子犧牲劑(表1,Entry 19),在可見光照射下,CO2可被還原成CO和HCOOH。有趣的是,在配體的末端吡啶上接上甲氧基后(C17;圖4),CO2還原產物只有CO (表1,Entry 20)。

圖4 基于吡啶基配體的鈷分子配合物Fig. 4 Chemical structures of Co molecular complexes based on polypyridyl ligands.
2.3 基于卟啉或卟啉衍生物配體的鈷分子催化劑
卟啉及其卟啉衍生物具有良好的吸光性能,基于卟啉及其卟啉衍生物配體的金屬配合物被廣泛用于光催化反應。1998年,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eta等人發現用三乙胺作為電子犧牲劑,在紫外可見光(λ > 320 nm)照射下,鈷卟啉(C18;圖5)在乙腈溶劑中能將CO2還原成CO和甲酸44。光照200 h后,產生CO和甲酸的總TON超過300 (表1,Entry 21)。作者通過電化學和光譜分析捕捉到了反應的活性中間體[Co0P] (P = 卟啉)。此外,Neta等人進一步研究發現將三聯苯作為光敏劑和三乙胺作為電子犧牲劑時,在紫外可見光的照射下,卟啉鈷衍生物(C19和C21;圖5)和酞菁鈷(C20;圖5)也能將CO2還原成CO或者甲酸(表1,Entries 22-24)40,45,46。
2019年,日本九州大學Sakai課題組合成了兩種水溶性的鈷卟啉(C22和C23;圖5)。在可見光下,它們能夠高效還原CO2為CO,當以[Ru(bpy)3]2+為光敏劑和抗壞血酸鹽為電子犧牲劑時,C22能在水溶液中將CO2還原成CO,TON高達926,選擇性大于82% (表1,Entry 25)47。當作者用廉價的Cu(I)配合物(CuPS)48替代[Ru(bpy)3]2+作為光敏劑時,在純水體系中,C22也具有優異的光催化還原CO2為CO性能,TONCO達到1085,選擇性達到90% (表1,Entry 26)49。在同樣的條件下,C23表現出更為優異的催化性能,將CO2還原成CO的TON高達2680,TOF達到2600 h-1(表1,Entry 27)49。

圖5 基于卟啉或卟啉衍生物配體的鈷分子配合物Fig. 5 Chemical structures of Co molecular complexes based on porphyrin and porphyrin-like ligands.
2.4 基于非平面N4配體的鈷分子催化劑
除平面結構的Co(II)配合物外,研究者還探究了基于非平面N4配體Co(II)配合物光催化CO2還原性能。2015年,香港理工大學Chan等人報道了一種含有四齒三腳架配體的Co(II)配合物[Co(TPA)Cl] (TPA = 三(2-吡啶基甲基)胺) (C24;圖6)50-52。使用Ir(ppy)3作為光敏劑和TEA作為電子犧牲劑,C24在乙腈中能夠催化CO2轉化為CO,選擇性達到85%,TONCO達953 (表1,Entry 28)。隨后,華中科技大學王峰等人將TPA配體進行修飾,合成了一種順式雙核Co(II)配合物(C25;圖6)53。光催化CO2還原結果顯示C25能將CO2還原成CO和HCOOH (表1,Entry 29)。DFT計算結果表明:活性中心配位點上的氧原子在CO2轉化為CO和HCOOH都起著重要作用。

圖6 基于非平面N4配體的鈷分子配合物Fig. 6 Chemical structures of Co molecular complexes based on nonplanar N4 ligands.
2016年,香港大學支志明課題組合成了一系列新型的順式[Co(N4)Cl2]配合物(C26-C29;圖6),用于光催化CO2還原54。在這些配合物中,活性中心Co(II)與配體上四個氮原子和兩個氯離子配位,形成六配位八面體構型。光催化實驗結果表明:配合物中N4配體的不同結構極大地影響了它們的光催化CO2還原活性(表1,Entries 30-33)。其中,以Ir(ppy)3作為光敏劑和TEA作為電子犧牲劑,C26表現出最高的光催化CO2還原活性和選擇性,可見光照射60 h,TONCO達到368,選擇性為95% (表1,Entry 30)54,但在C26的配體吡啶環上修飾上甲基,形成的配合物C27卻不能實現對CO2的光還原(表1,Entry 31)。作者還合成了兩個類似配體的Co(II)配合物C28和C29,實驗結果表明:C28能將CO2還原成CO,但TONCO只有13,而C29對CO2還原卻沒有活性(表1,Entries 32-33)。由此可見配體中部分基團的空間位阻效應對催化活性具有重要影響。電化學和光譜研究表明,激發態Ir(ppy)3的電子轉移到C26所產生的CoI是CO2結合的活性物種。DFT計算表明,配位的Cl-對催化活性也有顯著影響,與不存在Cl-的相比,[Co(CO2)LCl]0質子化得到[Co(COOH)LCl]+是放熱的過程,有助于CO2催化還原過程的進行。此外,華中科技大學王峰等人系統研究了不同鹵素離子對催化活性的影響,他們合成了兩個結構相似的Co(II)配合物(C30和C31)55,56。如圖6所示,這兩個配合物具有相同的N4配體和金屬中心,但配位的鹵素離子不同,與C30催化中心配位的是Cl-,而C31的是Br-,在相同的條件下,它們表現出不同的催化CO2還原活性(表1,Entries 34-37)。在光照12 h內,C31(TONCO= 102)的CO生成速率比C30 (TONCO= 56)更快,說明鹵素對CO的形成有影響。但是光照48 h之后,由于C30穩定性更高,C30的TON(TONCO= 470)高于C31 (TONCO= 403)55。電化學和光譜研究表明,C31光生電子轉移(PET)過程的速率常數和自由能變化比C30更大,與催化實驗結果一致。
四齒三腳架配體通常與金屬結合形成五配位的單核金屬配合物57-59。在催化過程中,軸向位置的溶劑分子可以解離,暴露出空位點鍵合底物分子。因此,基于四齒三腳架配體的金屬配合物也可能具有光催化CO2還原的能力。最近我們組通過配體修飾合成了一系列基于四齒三腳架配體的Co(II)配合物分子催化劑,并構建了穩定高效的光催化CO2還原體系。最初,我們采用具有富電子的苯并咪唑基團的四齒三腳架配體NTB (NTB = 三-(苯并咪唑基-2-甲基)胺)與Co配位形成單核Co(II)配合物(C32;圖7)58,使用[Ru(phen)3](PF6)2作為光敏劑和TEOA為電子犧牲劑,在含水溶劑(CH3CN/H2O,v/v = 4 : 1)中,C32光催化CO2還原成CO的TON達到1179,選擇性為97% (表1,Entry 38)58。隨后,我們研究了空間位阻對光催化CO2還原活性的影響,設計了兩個基于三腳架配體結構相似的配合物C33和C3460,如圖7所示,C33中催化中心Co(II)周圍的是三個異丙基;C34中的是苯甲基,光催化實驗結果表明:C33光催化CO2還原的催化效率是C34的7倍(表1,Entries 39和40),這可能是由于C33中異丙基比C34的苯甲基空間位阻更小,有利于CO2與C33中的催化中心CoII結合以及激發態的光敏劑與催化劑C33之間的電子轉移33,34,61。我們進一步研究了共軛效應對光催化CO2還原活性的影響,設計合成了三種具有不同共軛基團的三腳架配體及其相應的Co(II)配合物(C35-C37;圖7)62,實驗結果表明含有蒽甲基的C35和含有萘甲基的C36光催化CO2還原成CO的活性和選擇性都比C37高(表1,Entries 41-43)。對照實驗和DFT計算表明,C35和C36具有更優異的催化性能是由于配體中的共軛取代基使得催化中心CoII具有更正的還原電勢,同時,共軛基團也促進了激發態光敏劑分子上的電子往催化劑分子上轉移,從而顯著提高了CO2還原成CO的效率。此外,我們還研究了催化中心Co(II)的配位環境對光催化CO2還原活性的影響(C38-C41;圖7)63,發現隨著喹啉基團數量的逐個增加,配合物的光催化活性逐步提升,最高TON達到10650,選擇性也接近100%。C41催化活性略低,可能原因是喹啉基團的增加,導致催化中心周圍空間位阻增大,不利于Co(II)與底物CO2作用(表1,Entries 44-47)。

圖7 基于非平面N4配體的鈷分子配合物Fig. 7 Chemical structures of Co(II) molecular complexes based on nonplanar N4 ligands.
在研究單核Co(II)配合物光催化CO2還原為CO時,我們發現中間體[O=C―OH]中C―O鍵的斷裂是反應的速控步,需要較高的反應能壘,含有雙中心的雙核金屬配合物可能有助于中間體中C―O鍵的斷裂,加快催化反應的進行,提升催化效率。根據這個設想,最近我們合成了一個基于氮雜穴醚大環配體雙核Co(II)配合物(C42)64,65。光催化實驗結果表明:C42光催化還原CO2為CO的TONCO高達16896,選擇性也達到98%(表1,Entry 48),催化活性遠遠高于相應的單核Co(II)配合物(C34;表1,Entry 40),從實驗上證明了兩個Co(II)金屬中心協同催化作用的存在。接著我們進一步通過理論計算提出了雙核金屬協同催化機理:一個Co(II)作為催化活性中心結合和還原CO2,另一個Co(II)作為輔助催化位點促使中間體[O=C―OH]中C―O的斷裂和―OH的離去,協同促進了CO2向CO迅速轉化,并由此提出了雙核金屬協同催化CO2轉化為CO的反應路徑(圖8)。首先,C42快速結合CO2形成碳酸根橋聯的雙核Co(II)配合物C42a,然后進行質子耦合電子轉移反應生成C42b,C42b結合一個質子并脫去一分子H2O得到C42c。C42c通過過渡態TS1-1轉化為C42d,C42d經歷第二次質子耦合電子轉移反應得到C42e,C42e經過TS2-1形成C42f,在這一步中間體[O=C―OH]中C―O通過兩個Co(II)協同作用發生斷裂,最后釋放出CO完成催化循環66。這是首次利用雙核金屬協同催化實現光催化CO2還原。我們進一步研究發現,在電催化條件下雙核金屬分子催化劑也存在協同催化作用,極大地提升了CO2還原活性67。隨后葡萄牙里斯本大學Martinho等人對C42進行修飾,合成了三種苯環上具有不同取代基的雙核Co(II)配合物C43-C4568,實驗結果表明催化劑在低濃度和較短照射時間下,帶有給電子基團炔基的配合物C45表現出最高的催化活性,TONCO達到14210 (表1,Entries 49-51)。隨著反應時間的延長,生成的CO會進一步反應生成CH4,其中帶有―Br取代基的配合物C43產甲烷的活性最高(表1,Entries 52-54),理論計算結果表明C43能改變鍵能,以及使反應中間產物HCO3-更牢固地與催化劑結合,從而表現出較高的活性。

圖8 C42可見光驅動CO2還原為CO的催化機理Fig. 8 Catalytic mechanism of C42 for the visible-light driven reduction of CO2 to CO.
為了進一步驗證和利用雙金屬協同催化,我們將C42中的一個CoII換成ZnII合成了一種雙核異金屬配合物C4669,通過光催化CO2還原實驗我們發現,在相同條件下,雙核異金屬配合物C46的TONCO達到65000 (表1,Entry 55),遠遠高于C42(表1,Entry 48),是C42的4倍,選擇性也達到98%。C46催化活性的增強歸因于CoII與ZnII之間增強的協同催化效應,因為Zn(II)對OH-具有更強的結合力,更有助于反應中間體[O=C―OH]的C―O的斷裂,極大地促進了CO2向CO的轉化。除此之外,我們還設計合成了另一種穴醚配體,希望通過調節兩個金屬中心之間的距離從而進一步研究雙核金屬協同催化CO2還原,遺憾的是我們只得到了單核Co(II)配合物C4770。為了研究穴醚配體的限域作用,我們還合成了另一個相應的三腳架配合物C48。實驗結果發現,C47比C48具有更高的光催化還原CO2為CO的活性(表1,Entries 56和58)。即使在模擬煙道氣氛圍中CO2/Ar = 1/9 (v/v),C47光催化CO2還原為CO仍表現出高活性和選擇性(表1,Entry 57)。對照實驗和DFT計算結果表明C44更高活性歸因于穴醚配體的限域作用,這使活性中心CoII擁有更正的還原電位和更低的過渡態能壘。除雙核Co(II)配合物,最近日本大阪大學Masaoka等人合成了一個五核Co(II)配合物(C49)71,用Ir(ppy)3作為光敏劑,BIH作為電子犧牲劑,在DMA和TFE混合溶劑中,光催化CO2還原成CO和甲酸的TON為58.4和55.7 (表1,Entry 59)。

表1 Co(II)配合物分子催化劑光催化CO2還原Table 1 Co(II) complexes as molecular catalysts for photocatalytic CO2 reduction.

continued Table 1

continued Table 1
3 具有光催化CO2還原活性鈷分子催化劑的異相化
為了提高分子催化劑的穩定性,以及減少對貴金屬光敏劑的依賴,研究者也開展了許多將分子催化劑與無機半導體材料如氮化碳、石墨烯、二氧化鈦和硅等結合起來制備光催化CO2還原異相催化劑的工作。2014年印度石油研究所Jain等人合成一個卟啉鈷分子催化劑C50(圖9)72,C50上氨基與氧化石墨烯(GO)上的羧基通過席夫堿反應形成C50-GO催化劑,實驗結果表明以TEA作為電子犧牲劑,光照48 h,C50-GO能將CO2還原成甲醇,反應速率達到78.8 μmol·g-1·h-1,遠遠高于單純的GO或GO與C50物理混合作為催化劑的催化活性。2016年日本大阪大學Fukuzumi等人利用π-π堆積作用將C51 (圖9)與碳納米管(CNTs)復合形成C51-CNTs催化劑。以[Ru(Me2phen)3]2+作為光敏劑,TEA作為電子犧牲劑,在CH3CN和H2O溶液中,C51-CNTs能高效光催化CO2還原成CO,TONCO達到50173。2017年天津大學葉金花教授將帶有羧基的卟啉鈷(C52;圖9)通過共價鍵連接的形式與g-C3N4形成C52-g-C3N4復合催化劑74,用TEOA作為電子犧牲劑,在乙腈溶液中不添加其他光敏劑的條件下,CO的生成速率達到17 μmol·g-1·h-1。后續研究者報道了一系列鈷分子配合物(C53-C56;圖9)通過共價鍵或超分子作用與g-C3N4連接起來,并用于光催化CO2還原的研究工作75-78。其中C53和C54分別與g-C3N4形成的復合催化劑光催化CO2還原成CO的TON分別達到90和128,C55-g-C3N4光催化成CO的生成速率達到8.1 μmol·h-1。而C56-g-C3N4能將光催化CO2還原成甲醇,產率最高可達538.7 μmol·g-1·h-1(以C56的量計算)。最近我們組將帶負電的CdS量子點和帶正電的雙核鈷分子配合物(C57;圖9),通過靜電作用組裝成C57-CdS79,用TEOA作為電子犧牲劑,在NaHCO3水溶液中,光催化CO2還原成CO的TON達到1380。這些異相化后的鈷基催化劑,均能表現出良好的循環穩定性。

圖9 用于異相化的鈷分子配合物Fig. 9 Chemical structures of Co(II) molecular complexes used for heterogeneity.
4 總結和展望
在本文中,我們主要從配體角度綜述和討論了非貴金屬鈷分子催化劑在光催化CO2還原方面的最新研究進展。從總結的研究工作可以發現,配體結構對鈷分子催化劑催化CO2還原性能具有重要影響,配體修飾能明顯改善催化劑的催化活性。但是,目前均相光催化CO2還原離實際應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存在一些關鍵問題沒有解決。首先,當前報道的光催化CO2還原分子催化體系,除了我們課題組發現的一個普適性含水催化體系外18,58,80,其它幾乎都需要在無水體系中進行。因為在含水體系中,水的質子還原競爭反應將極大降低CO2還原的選擇性。因此,要實現真正人工光合作用,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開發在含水或全水體系中高效高選擇性的CO2還原分子催化劑。其次,最理想的人工光合作用是在太陽光和催化劑作用下,CO2還原反應與水氧化反應相耦合,實現真正的人工光合作用。然而,已報道的分子催化劑在光催化CO2還原時需要加入電子犧牲劑,而大部分電子犧牲劑的成本比CO2的還原產物如CO、CH4、CH3OH等還高,從而無法在實際中得到應用。因此,開發新的分子催化體系,利用水氧化產生的電子還原CO2,實現真正的人工光合作用,是光催化CO2還原分子催化劑的一個極其重要而又富有挑戰的發展方向。
盡管目前報道的包括Co(II)配合物在內的分子催化劑,均需要在使用電子犧牲劑的情況下才表現出光催化CO2還原活性,而且大多數催化劑反應活性、產物選擇性和穩定性仍然不夠理想,但是,這種模擬光合作用半反應的催化體系,對篩選催化劑,分析和總結催化劑的構效關系,以及揭示催化反應機理,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只有對催化劑的構效關系和催化機理有深入的認識,才有可能指導設計出更加優異光催化性能的CO2還原分子催化劑。為了獲得理想的光催化CO2還原分子催化劑,我們認為在設計催化劑時,以下幾個方面值得考慮:(1) 構建雙核或多核Co(II)配合物催化劑,利用雙核金屬間的協同催化作用,提高催化劑對光催化CO2還原的活性和選擇性。(2) 配位原子合適的Lewis堿性。理論上,配位原子的弱Lewis堿性會使Co(II)更容易被還原,獲得更正的氧化還原電勢,但弱Lewis堿性也可能使配體與Co(II)結合不牢固,導致Co(II)基分子催化劑不穩定。(3) 配體上修飾有效的功能基團。這些功能基團最好能一方面富集CO2分子,使Co(II)催化中心周圍具有高濃度的CO2,從而加強Co(II)與CO2分子的接觸,提高催化效率。另一方面可以與催化中心結合的反應中間體產生超分子作用,對反應中間體有一定的穩定作用,使其沿著預期的反應方向進行。有機功能基團―OH,―NH2等既能作為氫鍵給體和受體與反應中間體形成氫鍵作用,又能與CO2分子作用富集CO2,因此,在催化劑設計中,可以考慮在配體的合適位置修飾―OH,―NH2等功能基團,提高光催化CO2還原效率。總之,Co(II)分子配合物在光催化CO2還原方面展現了潛在的應用前景,也取得了較大進展,雖然目前還存在活性、穩定性和量子效率普遍比較低、多碳產物少等一些問題,但通過對催化機理的深入理解和揭示,進一步總結和積累構效關系,可以指導設計出具有優異光催化CO2還原性能的Co(II)基分子催化劑。
- 物理化學學報的其它文章
-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u/ZnO lnteraction in CO2 Hydrogenation to Methanol
- Electrocatalytic CO2 Reduction to Ethylene over CeO2-Supported Cu Nanoparticles: Effect of Exposed Facets of CeO2
- Controlling the Global Mean Temperature by Decarbonization
- Cu@UiO-66 Derived Cu+-ZrO2 Interfacial Sites for Efficient CO2 Hydrogenation to Methanol
- 二氧化碳電還原反應的理論研究
- 離子液體介導CO2化學轉化研究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