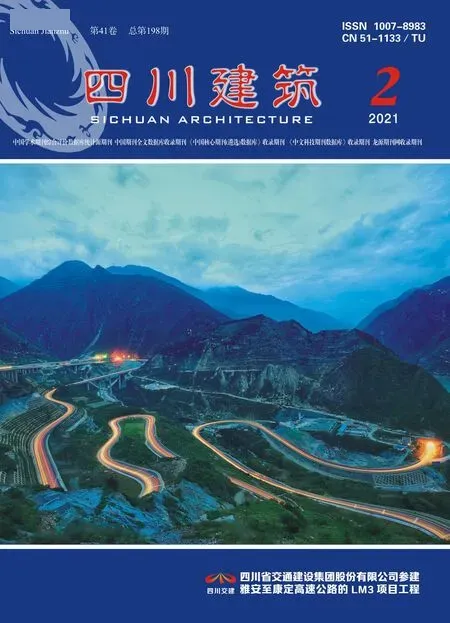深切峽谷相鄰橋址區風速相關性研究
余佳昕,張明金,李永樂
(西南交通大學橋梁工程系,四川成都 610031)
近年來我國為了發展西部經濟進行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其中不乏位于高山峽谷間的超大跨橋梁,但由于山區復雜的風場分布特性,存在湍流強度大和風切變強烈的特點[1],在設計山區橋梁時,為了確定橋梁的設計基準風速,通常采用數值模擬的方法模擬風環境,無需花費大量成本測量現場風速。
數值模擬是目前主要的風特性分析方法,數值模擬主要通過計算流體力學為基礎,可以以極低的成本模擬山區風環境,另外兩種方法為:風洞試驗和現場實測[2]。目前數值模擬主要針對,湍流模型,邊界條件,和特殊風場分析。對于湍流模型,主要針對不同地形條件下不同的湍流模型的適用性研究。Uchida和Ohya[3]研究了大渦模擬在風特性模擬中的應用,并取得復雜地形的風特性數據。Xiao[4]等將多種不同的湍流模型應用于一個范圍10.1 km×6.9 km的小島區域,分析不同湍流模型下的小島的風場分布。
對于邊界條件近年來主要針對于入口風速模擬。研究多尺度分析的耦合是模擬邊界層的高雷洛數和復雜流動現象的潛在方法[5]。沈煉[6]等結合WRF中尺度氣向分析為小尺度的CFD分析模擬邊界湍流入口,這種耦合方式能較好的模擬風場內的湍流強度。
復雜風場分析現被用于為復雜地區橋址區選址和設計風速確定提供參考。李永樂[7]等基于Y型河口研究了其風特性分布情況,研究了不同于普通深切峽谷的風特性。張玥[8]等基于一斜拉橋實際工程,利用多年的現場實測和數值模擬相結合的方式驗證橋址區風環境,并應用于橋梁風振研究中。遆子龍[9]等基于FLUENT研究了不同地表粗糙度對橋址區風環境的影響,研究發現增加地表粗糙度可能使主梁處風速增加。王云飛[10]等通過數值模擬研究了山區大壩對風環境的影響,發現大壩削弱了橋址區的風速和正攻角效應。
以上研究重點針對于模擬方法和特定地形條件下的風場模擬,對于兩橋之間的風速相關性研究較為缺乏。本研究基于西南山區大渡河上兩座距離僅4.88 km的千米級大跨橋梁,且橋軸線基本平行,相差不超過2 °。一座為川藏公路大渡河大橋,另一座為川藏鐵路大渡河大橋,研究系統研究了兩橋在不用入口風向下的風速相關性。
1 數值分析模型
1.1 工程概況
兩橋位于西南山區的深切峽谷之中,分別位于瀘定縣城上下游。兩橋址區峽谷高差達5 000 m,地形和地表狀態復雜,是典型的青藏高原深切峽谷,受南亞季風和青藏高原的雙重影響,可能存在較強的局地風場。兩座千米級大跨橋梁相距僅4.88 km,均為川藏線控制工程。公路橋東南側存在一條海拔約2 000 m的高聳山脊,鐵路橋西側有一突出山體,高程約為2 320 m。兩橋軸線基本保持平行,橋位設定角差不超過2 °。橋位布置見圖1,立面布置見圖2。

圖1 橋位布置平面


圖2 橋位布置立面(單位:m)
1.2 模型建立
根據該地的地貌特征地形范圍取為20 km×20 km,以此保證風場的充分發展,地形模型的下表面為山體與河流,頂部高程取為10 000 m。采用6面體網格對計算區域進行離散劃分,為了能在保證計算效率的前提下增加橋址區模擬精度,網格采取了從兩側向橋址區處逐漸加密網格,形成兩側網格較為稀疏,中間網格劃分較密的網格計算區域。底層壁面網格高度為2 m,并采用較低的網格增長率,充分模擬橋址區域的風場,最終形成了網格數量為380萬的計算區域。網格劃分見圖3。

圖3 三維地形模型及網格劃分
計算湍流模型使用SST k-ε模型,壓力與速度耦合采用SIMPLEC算法,離散格式選用二階精度格式。模型的底部邊界為WALL邊界,頂部邊界為對稱邊界,前后左右四個邊界根據工況的不同,選為壓力出口或速度入口。
風場計算中入口處來流風速分布偏安全地采用氣象觀測站標準場地對應的風剖面,邊界層高度取為1 640 m,邊界層的海拔高度為3 000 m。計算入口風速通過用戶自定義函數(UDF)進行設置,高程3 000 m以上部分風速取為50 m/s,高程3 000 m以下部分按B類地表(標準場地)風速隨高度變化的指數規律進行設置,高程1 360 m處為入口處谷底,其中梯度風速取為50 m/s,梯度風高度取為1 640 m。入口處風速可用下式表示,風速分布如圖4所示。

圖4 入口邊界風速剖面
1.3 計算工況與觀測點設置
瀘定縣50 a歷史風向資料表明橋址區風向主要為南北向。為考察不同方向來流對橋位風場的影響,計算中入口來流取24個方向(如圖5所示),圖中數字代表計算工況號,其中以南偏西15.9 °方向(工況13)為來流垂直于橋位橋軸線的入口風,其余工況以南偏西35.9 °方向(工況11)為始,逆時針每10 °一個工況,共11個工況。同樣在橋軸線的對應側也有相應的11個工況,此外設置兩個與河道走向基本垂直的工況(工況10與工況22)。為了方便討論以風向與南北軸線的夾角代替各工況的名稱,其中由南向北逆時針為正,順時針為負,風攻角以向上為正,向下為負。

圖5 風向工況示意
為獲取橋位關鍵點的風速情況,在兩橋塔間每1/8跨布置一個檢測點,橋軸向上共設置九個監測點,為了更好地捕捉橋位處的風速剖面情況,在近橋面高度附近進行了加密。在鐵路橋址區橋面下布置15個檢測點,橋面以上布置10個檢測點,共25個檢測點。在公路橋址區,以同樣的布置原則,在橋面以下布置12個檢測點,橋面以上布置13個檢測點,共25個監測點。故兩橋址區總共設置66個監測點(圖6)。

圖6 兩個橋位觀測點位置示意
2 計算結果與分析
2.1 跨中和橋塔風速
圖7(a)和圖7(b)為不同入口風向下公路橋和鐵路橋的橋面跨中和橋塔處的橫橋向風速。從圖中可以看出,橋面跨中和橋塔處風速展現出了高度相似的變化規律,這表明跨中處的風速和橋塔跨中處的風速存在較強的相關性,整體上看公路橋風速由于東側山脊線的影響風速在一定范圍內呈現出較大起伏,但橋塔和跨中處風速依然保持一致性良好的風速變化規律。由于鐵路橋位于峽谷中段,風環境相對穩定,從圖上表現出比公路橋更好的擬合性。

(a)公路橋風速

(b)鐵路橋風速圖7 跨中風速與橋塔風速
圖8(a)和圖8(b)為兩橋跨中和橋塔處橫橋向風速線性回歸擬合。將從圖8上可以看出,兩橋的橋塔和跨中風速均表現出了較好的風速線性相關性,其中公路橋的擬合風速的截距為0,斜率為0.96。鐵路橋的截距為0,斜率為0.99。可以看出風環境相對穩定的鐵路橋比公路橋風速更接近1。主要是由于公路橋的橋址區相比鐵路橋明顯復雜,四周存在多座高聳山體的影響,使公路橋的風速較為發散。
2.2 兩橋位跨中風速相關性
下圖9為兩橋跨中橫橋向風速,從圖9可以看出,兩橋在不同入口風向下跨中橫橋向風速變化規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這說明兩橋的橫橋向風速存在著一定的相關性。但從圖上也能發現,在個別工況下,兩橋的橫橋向風速存在較大差異,這來源于公路橋四周的高聳山脊線和山體對風場的影響,且差異風向主要為風偏角較大工況21和工況22。從圖9可以看出,西側來流作用下,兩橋的橫橋向風速一致性較好,東側來流時,由于高聳山體的影響,兩橋的風速出現了較大的差異。由此可以看出,在沒有特殊山體的影響下,由于峽谷河道對氣流導向作用使得同一河道緊鄰的上下游橋梁的跨中橫橋向風速存在這較強的風速相關性。

(a)公路橋風速擬合

(b)鐵路橋風速擬合圖8 同一座大橋跨中和橋塔處風速線性擬合

圖9 兩橋位跨中橫橋向風速
為了更好地研究兩橋橫橋向風速的相關性,將兩橋不同工況下的橋面的橫橋向風速進行線性擬合,如圖10所示,其中不考慮個別受山體遮擋的工況,從圖上可以看出,在不考慮個別特殊工況的情況下,兩橋的橫橋向風速具有較好的線性相關性,在截距為0的情況下擬合風速斜線的斜率為0.823。表明緊鄰的上下游橋梁的橫橋向風速有較好的線性相關性。

圖10 兩橋位跨中橫橋向風速相關性
2.3 兩橋位橋塔風速相關性
為了研究兩橋的橋塔處的風速相關性,下圖11給出了兩橋的西側橋塔的不同工況下的橫橋向風速和兩橋的橫橋向風速比值。可以從圖上看出,不同的入口風向作用下,除個別工況外兩橋的橋塔處橫橋向風速變化規律基本相同,但相比跨中稍差。整體上依然表現出西側來風的規律性相比東側來風更好的特點,這主要是由于西側橋塔受東側山脊線的影響較小。從跨中和西側橋塔在西側來風作用的下的變化規律可以看出兩橋的變化規律是基本一致的。總體上看風速與河道夾角較小時,兩橋的橋塔處風速相關性更好。

圖11 兩橋西部橋塔橫橋向風速
如圖12所示,將兩橋的西側橋塔處風速進行線性回歸擬合,兩橋西側橋塔的橫橋向風速比較符合線性相關性相較于跨中較弱,風速點更為離散。圖中的擬合風速線截距為0,斜率為0.8736,由此可以看出同一峽谷中的緊鄰的上下游橋梁在靠近兩側山體的橋塔處的風速依然具有相關性,但弱于跨中。
3 結論
通過建立考慮臨近山體的三維風場數值分析模型,研究了復雜山區突出山體影響下兩座相臨橋梁橋址區風速相關性,得到以下結論:
(1)在同一橋址區中的橋塔和跨中的風速相關性良好,整體上風速變化規律相同,特別是當入口風向與河道夾角較小時,表現出了良好的線性相關性。
(2)對于上下游橋梁跨中的相關性,可以看出,由于山脊線的影響在公路橋跨中受明顯遮蔽時,兩橋表現出風速明顯差異,由此看出,當橋梁受到高聳山體明顯遮蔽時兩橋的風速相差較大且規律不同,當山體的遮蔽效應降低后,兩橋風速表現出較好的風速相關性。

圖12 兩橋位西部橋塔橫橋向風速相關性
(3)對于上下游橋梁的西側橋塔之間的相關性由于受兩處橋址區的峽谷寬度和山體坡度的影響,兩橋除特殊工況外的風速變化規律基本相同,但相關性弱于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