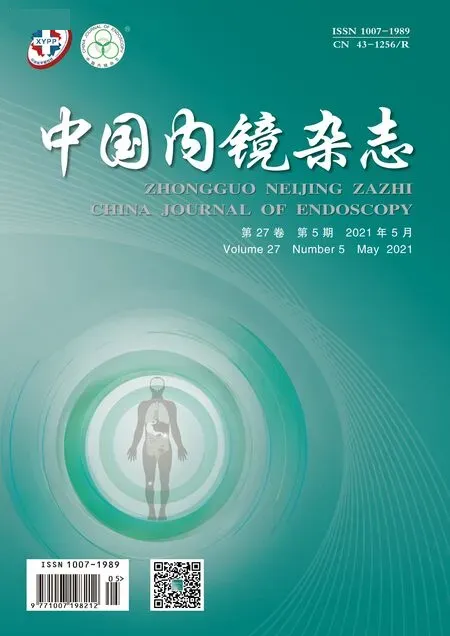婦科腹腔鏡手術患者術中低體溫發生率及影響因素分析*
陳懷穎,蘇麗靜
(寧德師范學院附屬寧德市醫院手術室,福建寧德352100)
因各種原因導致機體核心溫度低于36℃的現象稱為圍手術期低體溫[1],發生率較高[2-5]。人體通過機體完善的體溫調節機制,使核心溫度相對恒定在36.5~37.5℃。但麻醉1 h內核心與外周的熱量重新分配,會引起核心溫度快速下降,施行全身麻醉的患者代謝產熱減少約30.0%[6]。根據影響因素的不同,手術過程中致患者低體溫的因素大致可歸納為患者自身因素、麻醉相關因素和手術因素[6-8]。謝言虎等[9]研究表明,年齡、術前體溫、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和室溫是術中低體溫的危險因素;其中年齡>60歲的患者低體溫發生風險增加,麻醉時間和CO2總使用量是腹腔鏡術中發生低體溫的獨立危險因素。熊璨等[10]Meta分析顯示,我國關于術中低體溫危險因素的研究樣本量均較小,各研究間異質性大,證據不充分。且目前的研究多以開放性手術為主。近年來,腹腔鏡手術因其切口小和術后恢復快等優勢深受患者歡迎,已在臨床中廣泛應用,逐步取代了傳統的開放性手術,而腹腔鏡術中低體溫發生率及危險因素的研究仍較少。本研究旨在探討婦科腹腔鏡手術患者術中低體溫的發生率及相關影響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選取2018年10月-2019年6月就診于本院婦科擬行腹腔鏡手術的患者為研究對象,觀察患者術中體溫變化。本研究共觀察婦科腹腔鏡手術390例,排除甲亢病史2例、術中出血大于800 mL者2例和術中由腹腔鏡轉開腹手術者3例,最終納入383例,患者平均年齡為(40.9±9.8)歲。其中,子宮+輸卵管切除14例,子宮切除57例,輸卵管切除78例,子宮肌瘤剔除201例,其他33例。患者麻醉平均時間為(117.6±51.8)min,手術室平均時間(139.2±54.5)min。發生術中低體溫(<36℃)的患者119例,發生率為31.1%。本研究經過寧德市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同意參與研究的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1.1 納入標準①年齡≥18歲;②擬行腹腔鏡手術;③術后順利返回病房;④術前體溫>36.0℃;⑤患者知情同意,自愿參加本研究。
1.1.2 排除標準①術中轉為開腹手術者;②術前有甲亢等代謝性疾病者;③術中腹腔出血量>800 mL。
1.2 資料收集方法
使用紅外線耳溫槍(生產廠家:博朗,型號:IRT 6520)測量鼓膜溫度作為圍手術期核心體溫。入手術室時測量基礎體溫,麻醉后每30 min進行1次監測,出手術室前測量末次體溫。手術室期間任意時間的核心體溫低于36℃則定義為患者存在低體溫。
采用自行設計的“婦科腹腔鏡手術術中低體溫資料收集表”進行資料收集,包括以下內容:①人口學和手術前參數:年齡、性別、身高、體重、BMI、基礎體溫、術前血紅蛋白量(hemoglobin,Hb)、代謝性疾病史(甲亢)和入室狀態等;②麻醉參數:麻醉前心率(heart rate,HR)、美國麻醉醫師協會分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麻醉開始時間、麻醉結束時間、麻醉藥物和麻醉劑量等;③手術參數:患者進出手術室時間、術中失血量、術中沖洗量、術中靜脈總入量和術中液體總出量等。
1.3 統計學方法
選用SPSS 24.0統計軟件包分析數據。連續性變量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分類變量采用頻數(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檢驗比較低體溫組與無低溫組低體溫發生率的差異,將單因素分析中P<0.05的變量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以上數據分析的所有P值基于雙側檢驗,檢驗水準為α=0.05。
2 結果
2.1 婦科腹腔鏡手術術中低體溫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顯示:年齡≥45歲(P=0.006)、丙泊酚用量≥260 mg(P=0.017)、瑞芬太尼用量≥625 μg(P=0.008)、麻醉時間≥90 min(P=0.000)、CO2灌注量≥150 L(P=0.001)、術中沖洗量≥1 000 mL(P=0.003)、靜脈總入量≥1 500 mL(P=0.000)、液體總出量≥200 mL(P=0.002)和手術室時間≥120 min(P=0.000)與術中低體溫相關。見表1。

表1 婦科腹腔鏡手術術中低體溫單因素分析例(%)Table 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related factors of hypothermia during laparoscopic gynecological surgery n(%)
2.2 婦科腹腔鏡手術術中低體溫的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
手術室時間包含麻醉時間,所以僅保留手術室時間納入多因素分析。將年齡、丙泊酚用量、瑞芬太尼用量、CO2灌注量、術中沖洗量、靜脈總入量、液體總出量和手術室時間等變量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術中沖洗量(=1.746,95%CI:1.079~2.826,P=0.023)、靜脈總入量(=2.554,95%CI:1.366~4.773,P=0.003)和手術室時間(=2.058,95%CI:1.107~3.823,P=0.022)為婦科腹腔鏡術中低體溫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2。

表2 婦科腹腔鏡手術術中低體溫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Table 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ypothermia during laparoscopic gynecological surgery
3 討論
3.1 高齡患者更易發生術中低體溫
本研究顯示,術中低體溫組年齡≥45歲者為51.3%,高于無低溫組的36.4%,兩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可見年齡較高者易發生低體溫。BILLETER等[11]關于非計劃性術中低體溫的病例對照實驗顯示,年齡>65歲時術中低體溫的發生風險增加1.61倍(95%CI:1.33~1.96)。這可能與老年患者新陳代謝率下降、機體產熱量無法補償散熱量、圍手術期的核心體溫下降較快有關。此外,老年人的溫度調控能力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可導致熱量散失,體溫失衡[12]。有研究[13]認為,肥胖體型者由于有肌肉和脂肪組織的隔絕,往往不易散失熱量,但我國老年人多數體型消瘦,脂肪組織減少,熱量易散失。為減少術中低體溫和預防術后并發癥的發生,臨床上針對老年患者需加強監測,積極實施保溫措施,以促進患者術后康復。
3.2 術中低體溫與麻醉藥物的使用有關
本研究的麻醉方式均為全身麻醉,使用的麻醉藥物主要是右美托咪定、丙泊酚、舒芬太尼和瑞芬太尼,其中舒芬太尼使用量較少,主要為瑞芬太尼替代。單因素分析顯示,影響術中低體溫的麻醉藥物因素有丙泊酚和瑞芬太尼。在手術過程中麻醉藥物的使用不可或缺。有研究[14]認為,所有麻醉藥物均可損害自主神經系統的溫度調控能力,引起溫覺反應閾值的輕度升高和冷覺反應閾值的降低。多項研究[15-17]表明,丙泊酚、阿芬太尼和右美托咪定均可使出汗閾值呈輕度線性增加,血管收縮與寒戰閾值明顯呈線性降低。麻醉藥物可引起溫度調節功能受損,患者暴露于寒冷的手術室環境中,是導致患者低體溫的重要因素[14]。有報道[4,18]表明,術中低體溫可引起手術切口感染和心血管不良事件。針對術中非計劃性低體溫的現象,我國的專家共識[7]建議:全身麻醉手術患者誘導前需測量和記錄患者體溫,隨后每15~30 min測量體溫并記錄一次,直至手術結束,術中需做好被動隔離以保存患者手術期間熱量。
3.3 術中低體溫與機體液體出入量和手術室時間有關
本文單因素分析顯示,術中低體溫與CO2灌注量、術中沖洗量、靜脈總入量、液體總出量和手術室時間有關。其中,術中沖洗量、靜脈總入量和手術室時間是影響術中低體溫的獨立危險因素。熱量傳遞的方式有4種:輻射、傳導、對流和蒸發。傳導是指機體的熱量直接傳給與之接觸的溫度較低的物體,手術過程中傳導是熱量丟失的主要形式。一項關于產婦剖宮產術中低體溫危險因素的研究[19]表明,術中液體輸入量>650 mL時,低體溫的發生風險上升2.16倍。本研究中,患者均實施腹腔鏡手術,雖然能夠避免開放腹腔帶來的熱量損失,但腹腔鏡和骨盆鏡檢查中注入室溫下的CO2后,體溫會出現明顯下降[20]。BIRCH等[21]的Meta分析表明,使用加熱加濕的CO2氣體時,存在機體核心溫度高0.31℃的微小差異。加溫CO2可減少使用室溫CO2帶來的熱量損失[22]。
本研究術中沖洗量超過1 000 mL的患者,低體溫發生風險增大,與文獻[23]報道一致。本研究的手術室設定室溫為22~24℃,術中使用的沖洗液為室溫條件下保存,未加溫的沖洗液進入腹腔后通過與臟器接觸會帶走機體熱量。與術中使用加溫CO2相似,若將灌洗液進行加溫,可使機體減少因沖洗帶來的熱量丟失[24]。
應用于圍手術期低體溫的非藥物干預措施主要包括體外保溫(增加蓋被和使用保溫毯)、體腔保溫(輸液加溫等)和特殊保溫(術中使用氨基酸)等[25-26],目前使用最多的是強制空氣加溫毯。多項研究[27-30]顯示,使用強制空氣加溫毯能夠有效減慢體溫下降速率、降低術中低體溫發生率和預防低體溫所引起的并發癥。此外,根據我國麻醉專業質量控制中心意見[7]:對圍手術期高危低體溫患者,即使手術時間<30 min,仍建議在麻醉誘導前使用壓力暖風毯等加溫設備進行體溫保護;手術時間≥30 min者,建議在麻醉誘導前使用暖風毯等加溫設備進行體溫保護。
本研究中,383例納入患者有119例術中體溫低于36℃,術中低體溫發生率為31.1%。單因素分析顯示:與婦科腹腔鏡手術術中低體溫相關的因素為年齡≥45歲、丙泊酚用量、瑞芬太尼用量、麻醉時間、CO2使用量、術中沖洗量、靜脈總入量、液體總出量和手術室時間;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術中沖洗量、靜脈總入量和手術室時間是婦科腹腔鏡手術術中低體溫的獨立危險因素。
綜上所述,目前我國術中低體溫發生率仍較高,術中導致低體溫的危險因素復雜,因我國大多數醫療單位尚未在術中采用積極保溫措施,所以有必要針對腹腔鏡手術患者進行持續體溫監測,及時發現術中低體溫,識別低體溫的危險因素,并盡可能地采取保溫措施干預,在積極提高現代醫療護理質量的同時,也有利于促進患者術后快速康復、降低術后并發癥發生率和提升患者遠期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