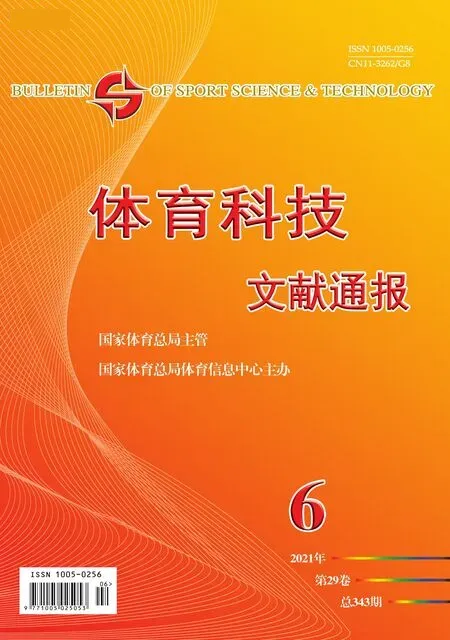競技攀巖精英運動員實力構成及提升策略
郭富強,賴培鑫,劉彥豪
前言
2016年,攀巖正式定為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比賽項目[1]。這表明全能賽特殊的競技規則[2]給競技攀巖帶來了新的發展風向標。經過幾年的發展,兩輪奧運資格賽事已選拔出28名代表當今競技攀巖頂尖水平的奧運資格運動員。對頂尖選手實力特點的分析將為競技攀巖的發展提供有益思考。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20年東京奧運會前28名資格運動員,其中男女各14名。
1.1.1 文獻資料法
通過國際攀巖聯合會和東京奧運會官方網站查詢競技攀巖最新競賽規則、奧運資格入選結果及近年世界杯及世錦賽比賽成績等資料信息。
1.1.2 視頻觀察法
觀看2019攀巖世界錦標賽和攀巖奧運資格賽,對競賽過程進行觀察、記錄。
1.1.3 數理統計法
運用EXCCEL2016對2019攀巖世界錦標賽和攀巖奧運資格賽比賽結果,整理、統計。運用SPSS23.0對各國2019年度難度、攀石、速度三項世界排名積分進行Pearson相關性分析。運用JMPPRO 13對運動員難度、攀石和速度攀巖的各項成績進行平滑處理(Lambda法取值0.05),以描繪運動員各子項實力的動態變化過程。
2 結果與分析
2.2 資格運動員實力分析
2.1.1 運動員基本情況結果
東京奧運會是攀巖歷史首次進入奧運,也是最高級別的比賽。獲取奧運參賽資格的運動員無疑是競技攀巖項目中最為頂級的運動員。鑒于第三項資格賽事為各大洲均分名額,所選運動員相對競技實力較低,故本文以前兩項資格賽事已確定奧運參賽資格的28名運動員作為分析對象,入選情況如表1。

表1 攀巖奧運資格入選結果(前28)
整體來看,歐洲選手共18名,占64.3%;亞洲選手共6名,占21.4%;北美洲選手共4名,占14.3%。反映出攀巖項目洲際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從各國入選運動員數量來看,日本4名、法國和美國各3名、斯洛文尼亞、奧地利、德國、意大利和中國各2名,其余上榜國家各有1名運動員拿到資格。配額(每個國家男女最多各2名)已滿的有日本(男、女)、法國(男)、德國(男)、美國(女)、斯洛文尼亞(女)。得益于日本的攀巖開展基礎和日本體育運動廳的重點扶持[3],日本運動員的實力近年提升十分顯著。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來看,日本隊伍均傲居群雄。
2.1.2 實力構成分析
競技攀巖包含攀石(Boulder,B)、難度(Lead,L)、速度(Speed,S)三個子項,各子項名次既決定運動員的世界排名,也反映出運動員在三個項目中的相對實力。包括田麥久在內的諸多學者認為前3名和前8名是反映競技實力的重要分界線[4][5]。前3名是能夠獲得獎牌,前8名能夠進入決賽,前20名能夠進入資格賽。第3、8、20名是攀巖運動員進入下一比賽階段和獲得榮譽的重要節點。本文以第3、8、20名為界,劃分運動員在各個項目的實力等級(如表3),以直觀表現運動員各子項相對實力。首先,選取運動員過去一年在攀巖世界杯比賽的最佳兩次比賽結果(借鑒世界排名積分計算辦法);其次,計算兩次最佳比賽名次的平均值作為運動員在各子項目的最終名次(數據來源于IFSC官方);最后,按照表2,根據名次對運動員子項實力進行劃分。如,Tomoa在2019年世界杯比賽中B、L、S三項獲得最好的兩個名次分別是第1和第1名、第2和第6名、第12和第12名;因此B、L、S三項名次均值為第1、第4和第12名;根據表2進行劃分,Tomoa的B、L、S三項分別屬于A、B、C實力等級。根據運動員各子項實力等級的強弱情況進行命名。均衡型:三項實力等級一致或由C、D等級項目混合組成(該情況下不足稱為優勢)時命名為均衡型。SL/BL/SB雙優勢型:兩項優勢項實力等級相同或由A和B組成優勢項、C或D組成弱勢項時,命名為SL/BL/SB(高等級兩項)雙優勢型。S/L/B單優勢型:優勢項唯一且不低于B級,命名為該優勢項(S/L/B)單優勢型,命名優先次序按均衡型>雙優勢型>單優勢型。此外,按照世界排名將資格運動員進行排序,規定男女前3位為第一梯次運動員,第4至第8位為第二梯次運動員,其余為第三梯次運動員。根據以上程序的劃分、命名和歸屬,最終得表4和表5。

表2 資格運動員子項實力等級劃分示意表

表3 奧運資格運動員實力類型(男)
2.1.2.1 拔尖項目優勢效應
如表4、表5,不同梯次運動員的拔尖項目(實力等級為A或B的項目)數量存在明顯差異。第一梯次的三名運動員由男女世界排名前3構成,均具有2個不低于B級的項目,其中至少包含1個A級項目。第二梯次的運動員均來自男女世界排名第4至第14名,均具有2個不低于C級的項目,其中至少包含一個不低于B級的項目。第三梯次運動員的世界排名從第15名到第46名不等,表現為或具有一個不低于B級的項目或具有兩個不低于C級的項目。可見,資格運動員所具有的拔尖項目數量成為區分其實力梯次的關鍵所在。這也成為低梯次運動員邁向更高梯次的重要參照。

表4 奧運資格運動員實力類型(女)
拔尖項目的重要性,在規則上也可見端倪。攀巖全能以B、L、S三子項名次相乘所得積分進行最終成績排名依據(以低為優)。以我國運動員宋懿齡為例,在奧運資格賽中,其預賽B、L、S三項名次分別是第20、19、2名,總積分為760,名列預賽第9;預賽第10的Fanny分獲第5、13、13名,總積分845。對比可見,盡管宋懿齡B、L兩項均弱于Fanny,但憑借S項的拔尖優勢將總積分壓低使排名靠前,從而獲得該項奧運資格賽的最后一個資格名額。而預賽第6名Iuliia三項分獲第21、21、1名,總積分441,B、L兩項雖弱于宋懿齡,但憑借S項領先宋懿齡一個名次,成功進入決賽。這說明了攀巖全能的規則認可“名次越靠前含金量越高”,也反映出在全能賽中拔尖項目能夠一定程度上彌補其他弱勢項的缺陷。拔尖項目的數量也因此成為區分運動員所處梯次的重要標志。2.1.
2.1.2.2 攀石和難度項表現協同
從優勢類型來看,男女資格運動員的實力排布均呈現相似規律:BL雙優勢型>B/L單優勢型>S單優勢型≈均衡型。男女第一梯次資格運動員均為BL優勢型;第二梯次運動員除世排第4的Kai為BL雙優勢型外,其余9人均為B/L單優勢型;第三梯次運動員則呈現出S單優勢型、均衡型以及少部分L單優勢型兼具的局面。各梯次的優勢類型表現出梯次越靠前越有規律、越靠后規律越不明顯的特征,這似乎表現出實力越強的運動員共性越明顯,而實力較差的運動員個性化越明顯。總結為運動員實力好得很有規律,差得各有千秋。

表5 2019年度各國各項世界排名積分相關性分析
從共性來看,第一梯次和第二梯次均為B和L優勢型而非B和S或L和S優勢型。該現象反映出B和L可能存在1+1>2的協同效應。通過對2019年度攀巖世界杯55個國家各單項積分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1),發現各國B和L項成績的相關系數達0.923(p<0.01),檢驗結果證實了B和L項目確實存在高度相關性。外在的成績表現來自項目內在本質的差異,而人體運動的本質是動作和能量代謝[6]。在動作方面,攀石(B)和難度(L)項均要求運動員在抓、摳、拉、推、張、蹬、跨、掛、踏等動作中靈活運用;在能量代謝方面,B和L項的比賽時限為4-6分鐘,對運動員在糖酵解供能能力和肌肉耐力上要求更高。區別于B、L項,速度項(S)擁有固定比賽路線,動作模式相對固化;比賽最快僅需5.48秒便可完成比賽[7],主要由磷酸原供系統供能。成績表現和內在機理的分析都在佐證這樣一個現象:B和L項之間存在協同效應,而與S項之間的協同效應不明顯。由于協同效應的存在,在B或L項中有一項拔尖項目的運動員更容易提高另一項的實力等級,而拔尖項目的數量正是不同梯次資格運動員的重要區分標志。揭示了為什么第一梯次和第二梯次的資格運動員均為B和L優勢型,而非B和S優勢型或L和S優勢型的原因。
從個性來看,第三梯次兼具各種優勢類型的資格運動員,可大致分為兩種類型:均衡型和單項優勢型。兩種類型的存在說明資格運動員某個子項目劣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由其他優勢項目彌補,無拔尖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無劣勢項進行彌補。通過與第一梯次和第二梯次的對比可知,能夠彌補的“一定程度”的程度就是區分資格運動員是否能夠進入第一或第二梯次的界限。
2.1.3 實力演變特征
資格運動員的實力梯次、實力等級和優勢類型展現的是結果,結果來自過去多年訓練、參賽的過程。本文選取自2016年攀巖項目正式入奧后資格運動員在攀巖世界杯或世錦賽中參賽的各單項成績名次,以時間為軸擬合出其各子項實力演變趨勢(趨勢向下說明名次前進),以一號種子選手Tomoa(男)和Janja(女)為例,同中國運動員潘愚非(男)和宋懿齡(女)進行對比分析,趨勢如圖一和圖二。盡管每個頂尖水平的運動員都不可復制,但是其實力對比特征及演變規律能夠把握競技攀巖制勝規律提供參考。

圖一 Tomoa和潘愚非實力演變趨勢

圖二 Janja和宋懿齡實力演變趨勢

表6 運動員信息及資格賽事比賽結果
2.1.3.1 男代表運動員實力演變分析
圖一可見,男一號種子運動員Tomoa在B項有較好的基礎。2017年開始同時參加S、L項的世界級比賽,一經參賽L項成績便明顯優于S項。成績變化趨勢呈現出優勢項目繼續拔尖、弱項動態進步的特點。積極向好的變化趨勢令其在資格賽事(如表6)中發揮極為出色:傳統優勢項目攀石(B)奪得單項第一,難度和速度均發揮出色。這與其深度貼合攀巖全能需要充分利用優勢拔尖、BL項協同的特點密切相關。中國運動員潘愚非,圖一可見其較早開始三個項目的比賽。S項漸退步、B項漸進步、L項波動后突進的演變趨勢使其從早期的S單優勢型,轉變為如今的L單優勢型。在優勢類型上,潘愚非的實力演變符合當今攀巖全能的競技需要。橫向比較Tomoa,兩人劣勢項S相差無幾,但在兩人相對優勢的B和L項上,潘愚非明顯落后于Tomoa。說明潘愚非在優勢類型上具有進入第一梯次的潛力,但在絕對上顯現出優勢項不夠拔尖的不足。
2.1.3.2 女代表運動員實力演變分析
圖二可見,女一號種子運動員Janja較晚參加S項世界級比賽,B和L項較早開始且始終保持較高水平;整體呈現出B項持續拔尖、L項略微退步、S項動態波動后突飛猛進的趨勢。依照該變化趨勢,Janja在資格賽事中B、L項穩定發揮出頂尖水平,速度項在預賽中奪得第7,符合其實力演變結果。中國年輕運動員宋懿齡,圖2顯示出其明顯的S單優勢型實力特征,并呈現優勢項愈發拔尖,而弱項攀石和難度項動態波動、甚至有下滑趨勢。資格賽中,其優勢項S與劣勢項B、L的極大反差是其實力演變趨勢的印證。優勢項的持續進步給宋懿齡帶來歷史性的突破,不僅在2019年4月攀巖世界杯(重慶站)打破女子速度攀巖世界紀錄,也令其憑借S項的優勢位列資格賽第9而獲得奧運資格。橫向對比Janja,盡管宋懿齡的優勢項S也已達頂尖水平,由于缺乏B、L項協同效應的增益,S項的優勢并未成為提高B、L項的動力。頂尖水平項目數量的落后和劣勢項目緩慢的前進步伐給宋懿齡進入更高梯次帶來了阻礙。
2.2 提升策略
2.2.1 實力梯次特征
通過對資格運動員實力構成的解析及代表性運動員的實力演變分析,可知不同梯次資格運動員在優勢類型和實力等級上存在明顯差異。這些差異成為低梯次運動員提升實力的參照。2019年度攀巖全能世界排名前3的運動員(第一梯次)奧運資格入選率100%,世界排名第4-14(第二梯次)的運動員入選率45.5%,世界排名第15-46(第三梯次)的運動員入選率17.2%。如圖三示,運動員進入更高梯次,需滿足不同的共性條件。

圖三 梯次特征示意圖
2.2.2 個案分析
2.2.2.1 我國男運動員潘愚非提升策略
潘愚非的實力屬于第二梯次,攀石(B)、難度(L)和速度(S)的實力等級分別為C級、B級和C級,優勢類型屬于L單優勢型。以進入資格運動員第一實力梯次為目標,根據前文優勢類型和各梯次實力等級構成規律的描述,潘愚非需保證有兩個不低于B級的項目,且有一項為A級。考慮到B、L項目可能存在的良性遷移效應以及在于種子運動員Tomoa的實力對比中所表現出其相對優勢項B、L不夠拔尖的不足,繼續發展B、L項目可能更容易累積優勢,因此其提高策略應該至少將B、L項目的實力等級提高至一個A級、一個B級。鑒于潘愚非在2019年攀巖世界杯(維拉斯站)獲得難度賽亞軍,將A級目標確定為L項、B級目標確定為B項更契合實際。盡管S項并非如今所長,但其擁有較長時間的S項經歷,加上中國是S項強國,一批優秀的運動員曾多次創造和打破世界紀錄,擁有在S項上的深厚基礎[8],所以,在精雕細琢B、L項之外,也應充分利用好我國在S項培養上的優勢加強補短。
2.2.2.2 我國女運動員宋懿齡提升策略
宋懿齡的實力屬于第三梯次,攀石(B)、難度(L)和速度(S)的實力等級分別為D級、D級和A級,優勢類型屬于S單優勢型。資格賽上中表現可以用“S項的拔尖決定其下限,B、L項的劣勢決定其上限”來概括。下限的保障是宋懿齡躋身世界前列之本。而S項優勢的缺陷不僅在于缺乏與其他項的協同效應,還在于S項容錯程度較低,一旦出現失誤,對成績影響極大。在2019年攀巖世界杯(廈門站)的速度攀巖決賽中,宋懿齡出現失誤導致最終成績超過8秒,與此同時,對手ARIES則打破了由之前宋懿齡創造的速度攀巖世界紀錄并提高至6秒99。因此,保證下限的關鍵在于不斷提高速攀訓練水平的同時也要提高其發揮穩定性,以確保優勢項拔尖的效應能夠發揮充分。對于上限的提高,與Janja的橫向對比便說明了問題,未形成B、L項優勢協同是宋懿齡在全能項相對落后的重要原因,因此B、L項也是宋懿齡邁進更高實力梯次不可繞開的坎。按照各梯次實力等級分布規律,若宋懿齡的弱項B、L提高2個單位(等級/項)的實力等級,其實力等級會提升一個梯次,進入第二梯次;若提高3個單位以上,則會進入第一梯次。因此,宋懿齡的提升策略應把握“保證下限,再提高上限”的原則。
5 結論
1.拔尖項目優勢和B、L項目之間的協同效應使不同梯次運動員在實力構成和實力等級呈現規律差別,該差別可作為低梯次運動員提升實力的參照。
2.根據世界排名順序,攀巖奧運資格運動員的實力構成呈現出BL優勢型>B/L單優勢型>S單優勢型≈均衡型的排布特征。
3.第一梯次運動員均具有2個不低于B級的項目,其中至少包含1個A級項目;第二梯次運動員均具有2個不低于C級的項目,其中至少包含一個不低于B級的項;第三梯次運動員表現為具有兩個不低于C級的項目或具有一個不低于B級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