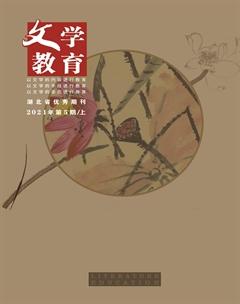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穆旦詩歌隱喻研究
陳珂
內容摘要:穆旦是中國新詩史上的一位重要詩人,在其詩歌中運用了意象和國家隱喻,以映射其所處時期的中國,建構起個體與國家之間的隱喻關系。本文基于概念整合理論,以穆旦的詩歌為語料,對穆旦詩歌中有關中國的隱喻進行了研究。通過分析描述穆旦詩歌中隱喻的表現形式來呈現穆旦心中的中國形象構成,文章探討了穆旦是如何用意象和隱喻來呈現當時的中國以及個體和國家之間的關系的。
關鍵詞:穆旦 隱喻 意象 概念整合 詩歌
一.引言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是一個追求革新和個性解放的時代。受達爾文思想影響的新文化主倡者們批判傳統思想對人個性的束縛和磨滅,并“致力于展示中國文化的病態特征,用以隱喻當時的社會文化乃至社會制度,隱喻現代人的生存困境、人生觀念和精神追求的選擇等方面的問題”(譚光輝 2007)。
作為中國新詩史上最為重要的一位詩人,穆旦的詩歌創作主題也與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緊密聯系。研究發現,穆旦的詩歌致力于塑造詩人與政治共同體的關系,穆旦的詩歌呈現了社會困境和當時國人愿景的同時,也參與了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建構。以往的文章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穆旦詩歌中的歷史修辭方面,所以關于穆旦詩歌中意象和隱喻的討論并不多,但其詩歌中意象和隱喻背后體現出的個體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還有待研究。
文章選取穆旦的兩首代表性詩歌《野獸》和《古墻》,運用概念整合理論對穆旦詩歌中的意象和隱喻進行考察,并試圖回答以下問題:在穆旦的詩歌是如何通過意象來隱喻當時的中國的?個體與民族國家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隱喻關系?這種關系如何得以建構、表達了什么思想?
二.概念整合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研究者們大多采用Lakoff和Johnson(1980) 的概念隱喻理論來闡釋隱喻。在此基礎上,90年代,Fauconnier和Turner(1998)共同提出概念整合理論。Fauconnier和Turner的概念整合理論主要涉及到兩個輸入空間,一個類屬空間和合成空間。根據概念整合理論,經過輸入空間到合成空間的信息投射后,最終會形成兩個輸入空間都不具備的層創結構。概念整合理論對自然語言意義的生成和理解具有很強的闡釋力,目前它被用于多種語言現象的解釋,比如詞匯、句法、語用預設、語言變異、創造性思維以及文學作品等方面的分析。作為人類普遍的認知過程,概念整合理論也為理解詩歌中的隱喻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三.穆旦詩歌隱喻意義建構的認知分析
1.“中國是野獸”
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
是誰,誰噬咬它受了創傷?
在堅實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溝渠,血的溝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銅樣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跡,從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躍起,
風在鞭撻它痛楚的喘息。
然而,那是一團猛烈的火焰,
是對死亡蘊積的野性的兇殘,
在狂暴的原野和荊棘的山谷里,
像一陣怒濤絞著無邊的海浪,
它擰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隨著一聲凄厲的號叫,
它是以如星的銳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復仇的光芒。(《野獸》,1937)
“現代中國是野獸”這一隱喻出現在中國遭到列強侵略時期,這個概念隱喻恰逢其實地表達了當時國人對國家的感情,當時的許多文學創作者都以這個隱喻為基礎,以描繪當時的中國。面對當時中國對外國侵略的懦弱以及國人缺乏力量和斗志的身體,魯迅呼吁以動物身上最為原始的獸性來改造國民柔弱的精神素質。他曾多次借用“狼”意象,呼喚野性的回歸。狼身上具有的好戰、野性和自由意志,是魯迅心中的精神界戰士所具有的良好品格。這樣的戰士,總是“所遇常抗,所向必動,貴力而尚強,尊己而好戰”,即使“力戰而斃,亦必自救其精神,所以他們總免不了群起而攻之的命運。
在《野獸》這首詩歌中,“受難的野獸”暗指“受難的中國”。在日常生活以及在人們的認知中,很難把國家和野獸的概念聯系在一起。概念隱喻模式強調源域到目標域單方面的映射,但是中國這個國家的概念域與野獸的某些概念要素不對應,因此,這一部分運用概念整合理論,以呈現出“野獸”這一隱喻性形象的生成過程和內部結構。
根據概念整合理論,詩歌的輸入空間1是野獸,輸入空間2是祖國。輸入空間1中有“受傷”“頑強抵抗”“野性”“復仇”等概念要素,輸入空間2包括“被侵略”“頑強”“歷史悠久”“復興”等概念要素。兩個輸入空間的信息有選擇性地構成映射,從而完成輸入空間1和空間2 的首次整合。整合后形成的合成空間產生“祖國是野獸”的層創結構。同時,讀者透過字里行間首先感受到野獸各個方面的特征。“血的溝渠”“痛楚的喘息”讓人仿佛看到一個遍體鱗傷的野獸在血泊中痛苦地喘息;另一方面,“抖身”“站立”“躍起”“號叫”等動詞讓人感受到一個充滿野力的形象。接著,讀者在對輸入空間合成的基礎上,通過激活自己的百科知識,提取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野獸”以及“現代中國”的背景概念結構,開始以歷史的眼光來審視這首詩。回眸穆旦創作這首詩時的歷史背景:詩歌創作于1937年,當時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家危機深重,穆旦作為一位具有濃厚家國情懷的知識分子,在祖國面臨危機之時的內心不可能是平靜的。面對此情此景,詩人運用野獸的意象,從各個方面對野獸進行細致描寫,塑造了一個頑強的野獸形象。在詩人看來,野獸雖遍體鱗傷,但仍然不屈不撓,勇于抵抗,這是作者所贊揚的精神。受難之時野獸對苦難的反抗,暗喻中華民族在抗戰時的堅忍與頑強,同時也是在戰爭磨礪中個體自我生命力覺醒的寫照。詩人將對祖國和國民的情感凝聚在“野獸”身上,勇于抵抗的野獸成為中華民族和個體生命力的象征。
在經歷了輸入空間的投射后,讀者結合類屬空間的結構,充分發揮其認知主動性和創造性,并對信息進行有選擇性的推理,最終形成層創結構的動態意義,達到關于此詩的解讀和感悟。在詩歌結尾詩人發出了對戰爭的復仇之聲,“復仇的光芒”暗示野獸不會就此屈服,它將進行強烈反擊并獲得勝利。野獸所透射的精神,讓人敬佩,與當時國家不屈不撓的抵抗聯想起來,讀者可以領悟到詩人對原始而強悍的野力的向往,以及對中國必將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信心。
2.“中國是古墻”
古墻寂靜地弓著殘老的腰,
駝著悠久的歲月望著前面。
一只手臂蜿蜒到百里遠,
敗落地守著暮年的寂寥。
凸凹的磚骨鐫著一臉嚴肅,
默默地俯視著廣闊的平原;
古代的樓閣吞滿了荒涼,
古墻忍住了低沉的憤怒。
古墻蜿蜒出剛強的手臂,
曾教多年的風雨吹打;
層層的灰土便漸漸落下,
古墻回憶著,全沒有惋惜。
怒號的暴風猛擊著它巨大的身軀,
沙石交戰出哭泣的聲響;
野草由青綠褪到枯黃,
在肅殺的原野里它們戰栗。
古墻施出了頑固的抵抗,
暴風沖過它的殘闕!
蒼老的腰身痛楚地傾斜,
它的頸項用力伸直,瞭望著夕陽。
晚霞在紫色里無聲地死亡,
黑暗擊殺了最后的光輝,
當一切伏身于殘暴和淫威,
矗立在原野的是堅忍的古墻。(《古墻》,1937)
《古墻》和《野獸》兩首詩都創作于1937年,當時抗日戰爭爆發,戰爭給國家、個人帶來了許多災難,國家經濟陷入荒廢,民族文化受到沖擊。這些事件成為詩人寫作的重要背景。在這首詩中,穆旦將當時的中國想象成一堵承受著歷史重負的古墻。它有著堅忍的面龐,殘老的腰身,剛強的手臂和蒼老的胸膛。原野中的萬物都在經受著暴風的猛擊,古墻也是如此,但它并沒有因此被擊垮,它無時無刻不在進行“頑強的抵抗”,“蒼老的腰身痛楚地傾斜,它的頸項用力伸直”,這些無一不呈現出古墻的堅韌和頑強,而在詩歌結尾,我們可以發現,這面古墻不再僅僅是殘缺破舊,它已成為了于苦難中頑強抵抗的中華民族的象征物。
該詩的輸入空間1是古墻,輸入空間2是祖國。兩個輸入空間的部分信息經過相應的匹配和投射后形成合成空間,再經過類屬空間有選擇性的整合和對信息的凝練,最終形成一個新創結構。在這一過程中,讀者通過文本形象理解、百科知識的激活和心理空間映射,完成對詩歌的在線意義解讀。首先,讀者從“殘老”“憔悴”“殘暴”“淫威”感知到一堵殘破的、承受著苦難和歷史重負的古墻形象。詩歌中關于古墻形象的描寫也充分讓讀者感受到了古墻堅韌的精神和頑強不屈的形象。接著,讀者走進詩人當時的創作角色,體驗詩人創作時的精神歷程:詩人寫這首詩時,中國正處于抗戰時期,日本的侵略使中國積貧積弱,民族危機深重。
在這之后,讀者發揮主觀能動性,經過完善擴展形成最終的層創結構,即讀者自身所感悟到的全詩的思想靈魂。詩中沒有直白地出現“國家”或者“中國”這樣的詞語,但讀者主體充分發揮其認知能動性后可以感悟到,古墻這一意象象征的就是當時滿目瘡咦的華夏民族。由此感悟到詩歌的在線寓意:現代的中國就像古墻一樣,雖身體衰老,苦難重重,但精神不老。
四.結論
本文以穆旦詩歌為研究對象,對穆旦詩歌中的意象和隱喻關系進行了考察。研究表明,穆旦詩歌中的形象呈現著他對戰時中國想象的同時,也建構起了個體與民族國家之間的聯系:詩歌中的形象蘊含著詩人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著如同詩人一樣的小個體,詩人把對社會、民族、時代的深憂巨痛展現為個體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這不僅體現了詩人對所處時代的深刻理解,也讓人體會到詩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參考文獻
[1]Gilles Fauconnier,Mark Turner.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8:22(2).
[2]Lakoff.G.& 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穆旦.《穆旦詩文集》[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4]譚光輝.癥狀的癥狀:疾病隱喻與中國現代小說[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