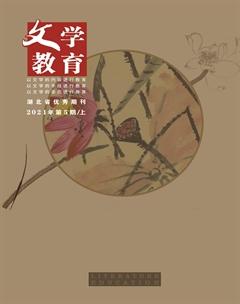《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中的藝術表達
廖夢帆
內容摘要:《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是由美國作者塔拉·韋斯特弗所寫的一部自傳體小說,書中講述了一個17歲之前從沒上過學的少女是如何逃離大山,飛往屬于自己嶄新的世界的故事。本文以“傷痕”和“救贖”為切入點,對小說中的藝術表達進行解讀,挖掘其區別于傳統文學的創新性的藝術手法,展現其蘊藏在文字之下的藝術世界。
關鍵詞:《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 傷痕 救贖
2020年,一部新人處女作,上市第一周就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榜第一名,全美銷量破百萬冊,作者因此還被《時代周刊》評為“年度影響力人物”,成為各大暢銷榜第一名以及年度最佳圖書的小說正是塔拉·韋斯特弗所寫的《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小說講述了一個出生在美國愛達荷州山區的姑娘塔拉,通過自己不斷的學習,掙脫了原生家庭的傷痕與束縛,在對自己的過往進行反思時得到救贖與解放的故事。
一.原生家庭的桎梏:傷痕與束縛
1.無法掙脫的生存悖謬
人之所以產生掙脫意識(掙脫命運、掙脫囚籠、掙脫災難),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自我意識的反抗和對現狀的不滿,是逃離也是救贖。這正是“掙脫”的藝術表達意義所在。塔拉將這種現狀藝術表達為悖謬,在經歷過痛苦、崩潰、自我懷疑之后,最后通過融合過往接受曾經厭惡的現實達到自我和解,這同時也正面直擊主人翁內心深處的虛弱與迷惘,這一絲帶有宿命意味的矛盾是人類生存中無法避開的問題,雖說是一個無解的悖謬,但我們卻總能被這種藝術情節所打動。
“悖論是一種表面似乎矛盾而內含真理因素的表達方式,如實用的和科學的研討相悖的方法。”[1]塔拉在書中描述過這樣的一個情景:“我看到了一個堅不可摧、像石頭一樣難以對付的自己。起初我只是不斷地讓自己相信這一點,直到有一天它變成了現實。然后我才敢坦誠地告訴自己,這對我都沒有影響,再也沒有什么可以影響我。但我誤解了最重要的事實:它沒有影響我,這本身就是它的影響。”由此不難發現,悖謬本身就是在自相矛盾中形成的,這樣的表現手法,使塔拉的作品中的人與社會的對立和沖突更加明顯,從而更加引人深思。
你無法想象在全球最為發達國家,塔拉沒有合法的身份登記、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沒有同齡的朋友。她的父親不斷的灌輸著一種思想:學校是魔鬼路西法腐化和墮落圣潔思想和靈魂的集中營,去上學就代表著將自己的孩子交給魔鬼。大山外的世界充滿著危險,不久后還會爆發大規模戰爭,世界末日也即將來臨。在父親反科學、反現代化的思想灌輸下,塔拉對大山外的世界既好奇又恐懼。她無法判斷父親話語的真實性。但正如加繆所說的:“在這個世界連鼴鼠都想有所希望。”[2]她的希望也出現了,哥哥泰勒通過自學考試上了大學,塔拉第一次正式接收到教育的概念,在泰勒的影響下,她開始學習、思考,開始有了逃離這種困境想法。
“我決定嘗試過正常人的生活。十九年來,我一直按照父親的意愿生活,現在我要試試別的活法。”能看出來,塔拉的自我意識正在漸漸覺醒,她開始意識到偏執的父親正在使一家人的生活變得扭曲不堪;意識到父親宗教觀的荒謬以及嚴重的思想疾病;意識到哥哥肖恩對她的傷害是真實存在的。她開始意識到只有當人用實際行動去反抗,才有機會沖出黑暗、走向光明,雖然這并不容易,但只有摒棄懦弱與絕望,才有飛越大山找到出路的機會與可能。
2.直視深淵的藝術手法
人類一方面創造并發展了文明,將文明推向無比的輝煌,這過程中同時也包含了人類的自我抹除,人類逐漸成為文明的奴隸。塔拉用自己的童年經歷作為故事主線,將作品中的人物扔進了一個畸形又荒誕的環境中。那些血濃于水的暴虐、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如同一道道的傷痕在塔拉的生活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那被隨意對待、任意呵斥的過往讓塔拉開始明白,“我們是如何被別人給予我們的傳統所塑造,而這個傳統卻被我們忽視了。”“我們在為一種話語發聲,這種話語的唯一目的是喪失人性和殘酷地對待他人。”
而這種痛苦與其畸變的原生家庭有著莫大的關系,通過書中的描述能看到塔拉經常受到哥哥肖恩的欺負和虐待,不是被肖恩抓住頭發在地上拖來拖去,就是將塔拉的腦袋按進馬桶,甚至言語威脅要殺掉塔拉,而父母卻完全的漠視肖恩的行為。就像塔拉所說的“我是如何在本該保持沉默時開口,卻在本該說話時閉上了嘴巴。”塔拉知曉自己痛苦產生的來源,知曉家人的暴行對自己造成的傷害。
在書中,塔拉開始直視自己身上的傷痕,而這整個過程痛苦到無法言語,正如尼采所說“凝視深淵過久,深淵亦回以凝視。”很多人因無法跨越這一道坎而墜入深淵,當塔拉面對那些曾經給予塔拉信心的人、那些鼓勵她和家人對峙的人、那些同樣遭遇過不幸的人、那些本該和她站在同一戰線的人,在利益沖突面前統統繳械投降,站在了塔拉的對立面去批評她、指責她。如果說,塔拉是因為她的經歷而變得堅強,那么到后來,她不斷地去回望、去理解、去接納曾經的過往,從而掙脫原生家庭的桎梏。
二.披荊斬棘的道路:救贖與解放
古往今來,無數文學作品中的救贖意識是從宗教層面進行詮釋的,往往充斥著濃郁的宗教情結與宗教信仰。在宗教層面上:認為所有的人都有罪,至于如何抹去這些罪過,則有兩種途徑:一種是他人的救贖、另一種是自我的救贖。
1.他人的救贖之路
塔拉在經歷了一系列質疑、辱罵和否定之后,患上了嚴重地神經性疾病,嚴重到無法出門見人、無法繼續完成學業的程度。但她的導師一直沒有放棄她,不斷地向她灌輸正向的思維方式;她的男友也沒有放棄他,一直陪伴在她的身邊支持鼓勵著她;她的同學朋友們更是一直在默默地關心著她。塔拉身邊的人都在用行動一點點地將她拉出了深淵,漸漸的塔拉發現自己的生活雖充滿了破碎的裂痕,但那些裂痕也恰恰是陽光所照進來的地方。
隨著那些隱藏在深處的溫情漸漸浮現:母親曾對她說“不要留下!走吧,不要讓任何事阻止你走。”父親會在塔拉要去哈佛讀書時對她說“無論你在哪個角落,我們都可以去找你。就算世界末日來臨,我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將你帶回家。”太多的痛苦和傷害讓塔拉忘記了這些為數不多的溫情回憶。當這些記憶重新浮出水面,給予了塔拉新的希望“我相信我能修復這個裂痕——現在我回來了。”塔拉漸漸明白了“個人對過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將永遠局限于別人所告訴他們的。”
文學創作的內容取決于生活中的人和事在作者心靈中的投影,面對生活中出現的巨大變化,其理想和信仰發生了較大的改變,這在塔拉的作品中所折射出的結果就是她開始理解父母的行為,她開始有勇氣去找尋一條歸家的路,一條歸往她心靈家園的路。
2.自我的救贖之路
人感覺到痛苦的主要原因是無盡的欲望,若心無旁騖,沒有太多的欲望,自然能夠掙脫牢籠,完成自我的救贖[3]。在該作品中表現為不斷地學習、重新認識世界,從而達到自我救贖的目的。“我多年來的學習,是為了讓自己能夠見證和體驗超越父親所給予我的更多的真理,并用這些真理構建我自己的思想。”塔拉開始認真地思考,思考她是否真的能夠割舍這一份血融于水的親情、是否真的能夠放下這壓抑的過往、是否還要放任自己沉浸在對過去的怨恨之中。
這條路是如此的艱難又漫長,塔拉一直嘗試著去理解、去改變:去理解父母兄長過往的行為;去改變曾經那個對世界一無所知的女孩。“我現在明白了,父親想從我身上驅逐的不是惡魔,而是我自己。”塔拉最后并沒有原諒過去,但她尋找到了一種與過去的自己和解的方法。面對這一切,塔拉認為是教育開啟了她新世界的大門,讓她的生命有了更多可能。
在接受福布斯的采訪時,她曾說“教育意味著獲得不同的視角,理解不同的人、經歷和歷史。如果人們受過教育,他們會變得不那么確定,而不是更確定。他們應該多聽,少說,對差異滿懷激情,熱愛那些不同于他們的想法。”人的一生,是一個不斷發現、修復、救贖的過程。塔拉帶著原生家庭的束縛、帶著無處安放的自我、帶著不被善待的過往,重塑了自我,完成了自我救贖。
三.結語
“文學創作向來都是對真理的一次探索。”[4]當小說作者塔拉·韋斯特弗將自己的過往向讀者們娓娓道來時,文字中包含的那一份淳樸和自然,讓人相信這個故事的是真實存在的,是真實的發生在我們身邊的。
在現代社會,人們常常感覺到被壓榨、被放逐、被剝奪,塔拉將這些情感運用獨特的藝術手法融合進自己的文學作中。在與家人發生激烈沖突的情節里,塑造了眼界缺失的“父親”形象,凸顯了教育缺失對人影響。在與自我和解的情景里,在對形而上學的悖謬追尋中,仿佛人人都無法逃避過往的傷痕。塔拉選擇的藝術表現方式是變幻的,通過適當的情節設置,準確又形象地展現了貧窮的本質。而這一具有現代性的表現手法,向世人傳遞著:只有行動起來才能掙脫困境,只有直面困難才能擺脫束縛,只有反抗才會有希望。
參考文獻
[1]吳金濤:《卡夫卡的荒誕美學論析》,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第9頁。
[2](法)加繆:《弗蘭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誕》,葉廷芳編《論卡夫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頁。
[3]王宗濤:《人生困境與自我救贖》,黃山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第126-129頁。
[4](奧地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傳》,張霽明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8-469頁。
(作者單位:南昌航空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