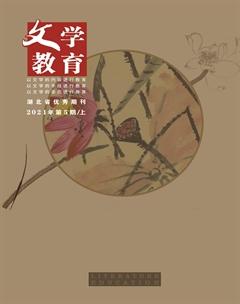波德萊爾與格麗克詩歌中死亡主題的差異性
張樂
內容摘要:古今中外,對死亡問題進行探索和研究的文學作品數不勝數,其中以詩歌最盛。法國十九世紀著名的現代詩人波德萊爾與美國當代著名女詩人格麗克,在詩歌創作中都有對死亡的闡釋。雖然兩位詩人的詩歌中都存在死亡,但是二者存在差異性,其差異性表現在多個方面。本文將通過文本細讀和對比研究,從死亡主題成因的不同,死亡意象的不同兩方面來分析死亡主題在兩位詩人的詩歌中差異性的體現,以此挖掘其詩歌死亡主題所蘊含的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波德萊爾 格麗克 死亡 差異性
一.引言
死亡在波德萊爾的詩歌中尤為突出,他的代表作《惡之花》更是將“死亡”作為一個章節,來追尋死亡這一主題。死亡也是格麗克詩中的一大主題,從她的第一本詩集開始,死亡反復出現,第五本詩集《阿勒山》幾乎是一本死亡之書,第六本詩集《野鳶尾》也有抽象的死亡體現[1]。雖然兩位詩人的詩歌中都存在死亡,但是二者存在差異性,其差異性表現在多個方面。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波德萊爾死亡主題的關注主要有兩個研究方向,一是對作品本身死亡主題的研究,二是對其作品中死亡主題的比較研究。國內外學者對格麗克詩歌中的多種主題進行探索,死亡是其中一個主題。雖然學者們對于兩位詩人的死亡主題都有探究,但是尚未有將兩者進行差異性對比的研究。本文旨在對波德萊爾和格麗克死亡主題的差異性進行研究,通過文本細讀和對比研究發現死亡主題在兩位詩人詩歌中差異性的體現,以此挖掘其詩歌死亡主題所蘊含的價值與意義。
二.死亡主題成因的不同
法國詩人波德萊爾在他的的詩作中對死亡的書寫較多,最鮮明的代表作就是詩集《惡之花》,由《憂郁和理想》、《巴黎風貌》、《酒》、《惡之花》、《反抗》和《死亡》六個章節構成[2]。《死亡》這一章共有六首詩,從不同層面詮釋了詩人對死亡的認知和思考。下文將對波德萊爾如此偏愛死亡主題的原因進行分析。
首先,波德萊爾受當時時代背景的影響。《惡之花》創作于19世紀中期,深受當時時代背景的影響。19世紀初期,法國爆發了工業革命,社會生產力提高迅猛,人們對于物質的追求日益猛烈。那個時期,人們物質上富足,精神上匱乏,所以當時歐洲涌現了許多充滿憂郁、迷茫、孤獨等的文學作品。正如勃蘭克斯所說,“19世紀早期的憂郁是一種病,這種病不是哪一個人或哪一個國家所獨有的,它是一場由一個民族傳到另一個民族的瘟疫,就像中世紀常常傳遍整個歐洲的那次宗教狂熱一樣”[3]。波德萊爾的詩中反映更多的是在當時繁華富裕的巴黎下,貧苦大眾的內心世界。《死亡》這一章描寫和反映的就是當時巴黎這所城市光鮮亮麗的外表下,底層人民的慘狀。此章節的第二首詩《窮人之死》就反映了繁榮社會背后存在的貧窮與衰敗。
“死亡給人慰藉,哎!又使人生活;
這是人生的目的,唯一的希望,
像瓊漿一樣,使我們沉醉,振作,
給我們勇氣直走到天色昏黃;
……
這是神祗的榮耀,神秘的谷倉,
這是窮人的錢袋,古老的家鄉,
這是通往那陌生天國的大門!”[4]
波德萊爾之所以描寫窮人的死亡,原因是現實中光鮮亮麗外表下的巴黎也存在著貧窮與衰敗。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窮苦人民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更別提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因此,人們將死亡作為寄托,祈禱死后能步入天堂,在天國中感受在人間從未體驗過的溫暖,平等和自由。因此詩人說,“死亡給人慰藉,哎!又使人生活”[4]。在現世的生活中人們無法實現理想的生活,只能寄希冀于死亡,憧憬死后進入天堂的樂園后的生活。所以,人們對于死亡的態度不再是畏懼,而是充滿期待,將之視為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經之路。
其次,波德萊爾詩歌中的死亡主題成因與其特殊的個人經歷密不可分,因為藝術品就像是一面鏡子,反應創作者的思想、經歷和品性。波德萊爾的生父是“孔多塞和卡巴尼斯的老朋友,才智出眾,受過良好的教育,保持著18世紀的整飭、優雅的風度,共和時代傲慢不遜的習氣沒能將之完全抹殺”[5]。生父的特征在波德萊爾身上也有很好的繼承,“波德萊爾總是保留著恭敬、禮讓的作風”[5]。作為父親的“老來子”,波德萊爾從小就得到的很好的寵愛。但好景不長,父親在他六歲時變不幸去世,而后,母親不顧比德萊爾的反對,改嫁給了奧皮克將軍。作家在創作時會不自覺地將自己的經驗帶入進去,這段童年經歷在《旅行》中就有所體現。“這腔調好熟,我們認出了幽魂;我們的皮拉德斯把我們迎接”[4]。皮拉德斯是希臘神話的王子,俄瑞斯忒斯的密友,俄瑞斯忒斯殺死了弒夫令嫁的母親后,與皮拉德斯一同逃亡。詩人提到這個故事是因為在波德萊爾眼中,母親的再嫁是一種背叛。他后來寫道:“如果別的母親有一個我這樣的兒子,是不會再嫁的”[5]。波德萊爾的繼父對波德萊爾想要從事文學事業的愿望也一直表示反對,母親的改嫁與不被肯定的內憂外患,是使得詩人一生憂郁和痛苦的始作俑者。家庭的不美滿使他孑然一身無所牽掛,因此他向死亡尋求救贖。
格麗克如此偏愛死亡主題的一個原因是受其家庭環境的影響。格麗克出生于1943年,在她出生的前七天,她的大姐不幸夭亡,整個家庭隨之陷入悲痛之中。新生命的降臨,并沒有給這個家庭帶來太多的喜悅,更多的是睹人思人。這種與生俱來的哀傷感深深烙在了格麗克的內心深處。因此,在她之后的詩歌創作生涯中,她用大量的文筆描寫死亡和新生,其詩中充滿著悲痛,孤獨……格麗克似乎從一出生就面臨死亡(姐姐的死亡),她對死亡的態度不是懼怕,因為在她心中生存比死亡更使人恐懼。她的名詩《野鳶尾》開頭就說:“在我苦難的盡頭,有一扇門。聽我說:你稱之死亡。我記得”[1]。家庭因素對于格麗克詩歌中的死亡主題影響重大,憂郁的家庭環境使她無法脫離死亡這一主題。當讀者讀到她的詩歌時,就可以感受到詩中體現的哀傷、悲觀、叛逆、孤獨……
格麗克偏愛死亡主題的另一個原因是她受到了其他文學家的影響。格麗克對詩歌尤為喜愛,從小就開始閱讀莎士比亞、布萊克、濟慈、艾略特等文學家的作品,其中最受她喜愛的文學家就是艾略特。艾略特的《荒原》中有這樣一句:“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從死去的土地里培育出丁香,把回憶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攪動遲鈍的根蒂”[6]。格麗克深深地被這種自然的表達方式所吸引。艾略特對格麗克的影響,在《新生》中有所體現,格麗克的《新生》與艾略特的《荒原》有不謀而合之處。例如,“春天”對于格麗克來說,就像是艾略特描繪的“四月”一般,是殘忍的,充滿死亡的氣息。
“確實,春天已經回到我的身邊,這一次
不是作為愛人,而是作為死亡的信使,但
它仍是春天,仍然要溫柔的說起”。[1]
從這一詩節可以看出,詩人開始時滿懷希望,而后是失望過后的哀嘆。格麗克通過自然的描繪方式使死亡消無聲息地與生命中的美好融入到一起,從而說明死亡是無法避免的。這點與存在主義奠基者之一雅斯貝爾斯所言一致,“哲學信仰要求采取高傲的人生態度,這種態度雖然并不‘盼望死亡,但把死亡當做一種一直滲透到當前現在里來的勢力而坦然地接受下來”[7]。不管是艾略特筆下的“四月”,還是格麗克筆下的“春天”,都處處可見死亡的痕跡。因此,生死相伴相依,死亡是慢慢滲透到人們生命當中來的。
三.意象不同
作為法國早期印象派詩人,波德萊爾將死亡作為一種象征手法,在他的詩歌中,他使用大量與死亡密切相關的象征性意象來描繪死亡,如“墳墓”,“靈柩”,“墓園”,“墳場”等意象。這些意象如繁星點點,充溢在詩里行間,無時無刻不提醒讀者注意死亡這一主題。在《情侶之死》這首詩中,詩人以“墳墓”這一意象來表現死亡的場景,以“最后”,“永別”來暗示死亡。整首詩到處體現著死亡,題目“情侶之死”也是對死亡這一主題的呼應和重復。
“我們會有充滿清香的眠床,
深深的如同墳墓一樣的沙發,
奇特的花卉為我們在架子上
開放著,天空也更是美麗有加。
兩顆心競相燃盡最后的熱量,
最后將變成兩支巨大的火把,
在兩個精神,在孿生的鏡子上,
相互映出了彼此雙重的光華。
玫瑰和神秘的藍色做成的夜晚,
我們將互相射出唯一的閃電,
仿佛長長的嗚咽,充滿了別緒;
隨后,有一位天使忠誠又快樂,
他把門微微的打開,進來擦拭
無光的鏡子和點燃熄滅的火”。[4]
第一個詩節中,死亡在“墳墓”這一詞中得到體現。“墳墓”與死亡有著最直接的關聯,是一種空間上的限定。通常情況下,“墳墓”象征恐懼和衰亡,但在波德萊爾眼中,“墳墓”卻是一個棲身之所。第二個詩節描寫了臨死前的場景,第三詩節則是死亡到來的時刻。最后一個詩節,是死亡之后的復活,逝去的靈魂和熄滅的愛將會被重新喚醒和點燃。這樣的復活,意味著靈魂和愛將永遠存在,而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到達永恒的一個階段。在波德萊爾的詩中,死亡不是痛苦的。他用消極的(“最后的”和“熄滅的”)和積極的(“美麗”,“光”和“唯一的”)詞匯反應死亡的雙重性,即死亡雖然是悲痛的,但卻是得到永恒的愛的唯一途徑。雖然死亡是人生命的起點,但也是另外一個世界中永恒的生命的起點。情侶在臨死之際完成了身體和靈魂的交融,實現了靈魂伴侶的理想狀態。因此,死亡來臨的那個晚上,也具有一種理想的美感。波德萊爾對死后靈魂復活的信仰,正反映了他對理想之可抵達的信仰。就這樣,死亡把人們帶到了一個理想的世界,這不是我們所在的人世,而是“另一個世界”。
在波德萊爾的詩歌中,他所使用的死亡意象給人更直觀的印象,他對死亡的態度具有雙重性,而死亡這一意象在格麗克的詩歌中有不同的體現。在格麗克的詩歌中,死亡處于核心位置。從她的第一本詩集開始,死亡這一主題就反復出現。提起格麗克,人們常想起《新生》這首詩,雖以“新生”命名,但卻充滿了死亡的意味。在《新生》中,格麗克采用第一人稱,像講述唯美的故事一般,促成詩歌整體的美感。詩人將生與死相襯托,通過嗅覺、聽覺和視覺等多種感官,動靜結合,將新生的美好和死亡的遺憾刻畫得淋漓盡致。在這首詩歌中出現的與死亡意識相關聯的意象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時間意象。“確實,春天已經回到我的身邊,這一次不是作為愛人,而是作為死亡的信使,但它認識春天,仍要溫柔的說起”[1]。詩歌中描繪的是春天,提到春天,人們會聯想到生命,萬物都將在春天復蘇。但是,在這首詩中,詩人打破了傳統的印象,隨春天而來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的信使”,即哈德斯的信使。哈德斯是希臘神話中的冥王,他派信使來的目的,就是告訴人們,死亡離人們又進了一步。“我”在春天里重生,也將在春天里死去,既贊嘆“新生”,又歌頌“死亡”。以春天暗示死亡,打破讀者的客觀印象,從而達到戲劇性的悲觀效果。
二是實物意象。在《新生》中,存在著許多實物意象。“年輕人正在買輪渡的船票。笑聲,因為空氣里飄滿了蘋果花”[1]。“年輕人”這一意象,與“春天”一樣,讓人聯想到朝氣,不僅意味著一個新的旅程即將啟程,還意味著許多可能性。“蘋果花”開了,意味著生機與豐收。“年輕人把他的帽子扔進水里;多半是他的心上人接受了他的愛情吧”[1]。這一句表明新的新戀情的展開,同樣意味著人生新旅程的開始。這些美好的畫面使人耳目一新,期待新生活的來臨,給人無限美好的遐想。詩歌中的“我”重獲新生后,耳邊縈繞著笑聲,空氣中彌漫著蘋果花香,映入眼簾的是活力四射的年輕人。“年輕人”、“船票”、“蘋果花”等意象,是多么美好的名詞和場景,但與之相反,他們是“死亡的信使”,象征的不是希望,而是死亡。格麗克在談到死亡時,不是提醒人們珍惜當下,而是描述一種客觀事實,她的詩寒氣逼人,逼著讀者去看真實的世界。因為死亡是客觀存在的,無法避免,在死亡面前,愛情是不可靠的。格麗克想要點醒大眾,引導讀者深入思考死亡的存在。
四.結論
通過對死亡主題和死亡意象的比較,可以發現死亡意識貫穿波德萊爾與格麗克詩歌創作的始終。對波德萊爾來說,對“死亡”的偏愛,是詩人在當時社會下的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是對于現實生活的一種反思。對于格麗克來說,死亡主題的體現是她將個體經驗轉化為詩歌藝術的過程。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兩位詩人對死亡觀的不同感受,在波德萊爾的詩中,死亡具有雙重性。與之不同,格麗克在談到死亡時,不是提醒人們珍惜當下,而是描述一種客觀事實,因為死亡是客觀存在的,無法避免。格麗克想要點醒大眾,引導讀者深入思考死亡的存在。這也體現了詩人們對于死亡的思考,也呼喚人們對自身存在意義的思考,對人生價值和理想進行追求。
參考文獻
[1]露易絲·格麗克:《月光的合金》[M],柳向陽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寧文莉:《波德萊爾的詩歌美學觀——基于愛倫·坡對波德萊爾的影響》[J],《現代交際》,2019(20):121-122。
[3]勃蘭克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M],張道真譯,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4]波德萊爾:《惡之花》[M],郭宏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5]泰奧菲爾·戈蒂耶.回憶波德萊爾[M],陳圣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6]T.S.艾略特:《荒原》[M],裘小龍,湯永寬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7]雅斯貝爾斯:《生存哲學》[M],王玖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