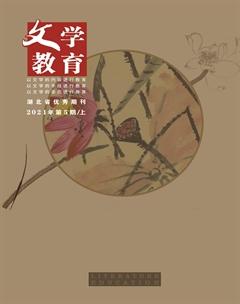五四時期的童話翻譯概述
張曼
內容摘要:“五四”前,由于受到“父為子綱”兒童觀的影響,中國兒童并未受到重視。“五四”時期,由于西方思潮的影響,兒童意識開始覺醒,兒童文學的創作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童話是一種重要的兒童文學類型,由于本身具有的特點能夠起到引導兒童的作用。而在一時之間無法創作足夠的童話滿足中國廣大兒童的需要,因此在五四時期,很多外國優秀童話被翻譯過來,也出現了大批翻譯家將外國的兒童文學作品介紹到中國,對我國的兒童和兒童作家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童話 童話翻譯 五四時期
一.引言
現代社會兒童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重視,人們認為兒童是祖國的花朵,代表著祖國的未來。但兒童不是一直都這么重要的地位,在“五四”前,只是作為成人的一種附屬物而存在。作為一種重要的兒童文學題材的童話,在中國很久以前就已經有了,但現代意義上的童話可以說是“五四”之后才出現的,因為“自五四開始出現真正由文人創作的童話始,‘童話才越來越清晰地成為兒童文學文體之一,而與民間故事等其他文學類型及文體分開,并擁有了自己的特定內涵”[1]142。本文從“五四”時期的背景,童話的定義、特點和作用,“五四”時期的童話翻譯三個方面,對童話和“五四”時期的童話翻譯進行簡單介紹。
二.時代背景
五四運動前的,在中國“孔教的精神枷鎖禁錮著人們的頭腦,神鬼之學猖獗,文學上的‘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從思想、文學語言上禁錮著人們的解放”,[2]93-94幾千年來,統治中國的核心兒童觀是“父為子綱”為核心的,兒童被看做是成人的附屬物,沒有受到根本上的重視,因此也沒有專門為兒童創作的作品。
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和民主,倡導文學革命(即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猛烈攻擊了傳統的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西方新思潮開始涌入中國。然而因為“自1928年起,新成立的太陽社和后期創造社正式發起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這標志著文學革命開始向革命文學轉變”,[3]1-2因此,雖然一般認為五四時期指1916-1924的新文化運動,本文所采用的五四時期則是從1916年到1927年的十年。
在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期間,出現了一個翻譯高潮,大批外國作品被翻譯到中國,其中包括一些兒童文學作品,如林紓翻譯了《魯兵遜漂流記》,包天笑翻譯了《馨兒求學記》(Curoe),周桂笙翻譯的一些伊索寓言、格林童話等。在“五四”時期十年間,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來華講學,他的的“兒童本位論”的創作思想“以不可阻擋的凌厲之勢,沖擊著統治了中國幾千年的以‘父為子綱為核心的傳統兒童觀”,[4]這就引起了當時一些有識之士的注意,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開始把目光投向幾千年來受到忽視的兒童身上。
三.童話的定義、特點和作用
兒童文學的體裁有很多種,如兒歌、兒童詩、童話、寓言等,童話是其中一種重要的形式,它符合孩子的思維特點,因此深受孩子們的喜愛。
1.童話的定義
童話,在英語中稱作“fairy tales”。這個詞語不是原本就存在于漢語中的,而是“清代末年從日本語詞匯中引進來的,起初含義較廣,包括給孩子們寫的一切故事性作品。后來才慢慢把它和神話、傳說、寓言、民間故事、兒童小說等體裁嚴格區分開來,單指那些富有豐富的想象、強烈的夸張、帶有神奇的幻想色彩的故事”。[5]115童話、神話和傳說都帶有幻想性,但是神話是完全虛構的神的故事,傳說是有相當歷史事實依據的關于超人的英雄故事,而童話是比較樸實、幽默、更富有人情味的民間故事,[6]57因此相比較而言,童話更適合兒童閱讀。
2.童話的特點
童話既然是給孩子讀的,那它就有著孩子的思維特點。兒童由于缺乏對社會常識的了解,因而思想就比較靈活,比較喜歡幻想,因此,“童話最基本的特征是幻想,幻想是童話的靈魂”,[7]78這符合了孩子的天性,適合兒童閱讀。
另外,童話在語言上也有著兒童語言的特點。在詞語方面,鑒于兒童認識或者明白的詞語尚少,童話用詞較為簡單,而且多用兒童化的詞語,如兒化音、疊字、擬聲詞等。在句子結構上,也不宜過長過復雜,因此句子較短,句子之間關系簡單,以方便兒童理解。在內容上,多用夸張、象征和擬人,因為“童話的幻想是通過某些藝術手法表現出來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夸張、象征和擬人”;[7]79孩子們的思維比較的直接,所以夸張手法的運用能將善惡之間的界限夸大,讓他們認識到兩者的不同,從而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惡。而在內容上,童話常用象征,也就是用一些動物、植物等代替人的形象,“通過帶象征性的童話形象,確切地概括了人的特征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將幻想與現實相結合。[5]134正因為有著這些特點,童話因此也受到兒童的喜歡。
3.童話的作用
童話不僅僅是兒童讀的,成人也能閱讀從中享受到文學帶來的快樂。對于兒童來說,由于他們的社會經歷尚淺,對對錯和真善無法辨認,而童話中,善惡分別明顯,通過閱讀,可以讓給他們以暗示,明白什么事對的和善的。同時,童話中充滿了幻想的成分,這就“可以進一步引起他們的好奇心,豐富他們的幻想能力,并將他們的幻想引到正確的方向去,幫助他們的思維活動得到正確的發展”。[5]140
正是因為童話有以上的特點和作用,使它成為一種重要的兒童文學形式,在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缺乏的時候,一些有識之士便挑選了一批外國的童話進行翻譯。
四.五四時期的童話翻譯
早在五四前,一些外國的童話就已經被翻譯過來。如晚清時期,包天笑就翻譯了意大利作家德·亞米契斯的《馨兒就學記》;在1909年魯迅、周作人已經出版了《域外小說集》,其中包括愛爾蘭作家奧斯卡·王爾德的童話《安樂王子》(Happy Prince)。但是當時兒童意識尚未覺醒,而且這些作品都是用文言文翻譯的,因此沒有受到很大的重視。而“五四”時期,則出現了一個兒童文學翻譯的高潮,一批優秀的外國童話通過翻譯被介紹給中國的讀者。
1.原因
新文化運動倡導文學革命,反對當時的八股文和中國現有的長篇章回體小說,提倡新文學,改革這些舊文學。杜威的“兒童本位論”思想也促使中國的各界人士開始關注兒童,注意到兒童的存在,兒童意識開始覺醒,兒童的地位得到重視。與此同時,兒童文學的創作也成了當務之急。當時兒童意識剛剛覺醒,而中國兒童的數量有很大,本國兒童文學作品極度匱乏,一時之間不能創作出在質量和數量上都能很好的作品,因此,翻譯外國現有的兒童文學作品就成了一條捷徑。
當時國外有很多優秀的童話作品,也有一些已經被譯介到中國,翻譯這些已有的童話,是最為便捷也最有效的方法。“五四”時期,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進行了兒童文學的翻譯,比如魯迅、周作人、茅盾、趙元任、趙景深、夏丏尊等。一些著名的童話被翻譯過來,如安徒生、格林兄弟、王爾德等人的童話,這些“兒童文學名著等大批地譯介進來,也是因為由‘人的發現而意識到了‘兒童的獨特性”。[8]
2.主要的譯作
在這一時期內,主要的童話翻譯作品包括趙景深、周作人、茅盾、鄭振鐸等翻譯的《安徒生童話全集》;魯迅翻譯的童話劇《桃色的云》、《愛羅先柯童話集》、《小約翰》;周作人重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裝》;夏丏尊翻譯了《愛的教育》;趙景深翻譯了《格林童話集》十二卷;鄭振鐸翻譯了歐洲童話《列那狐的故事》;1921年趙元任翻譯了英國劉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夢游奇境記》等。
在有些情況下,翻譯的作用很大,比如說能引進一種新的文學形式,比如十四行詩就是通過翻譯被引入中國的。童話雖然不是一種全新的文學體裁,通過翻譯這些外國童話,我國一些關心兒童、熱衷為兒童創作的作家也能從中得到學習,在題材、風格等方面都有所借鑒。在問及外國翻譯過來的童話與自己的創作是否有關系時,葉圣陶就回答:“既然看過,不能就說絕對沒有影響。正象廚子調味兒,即使調的是單純的某一種味兒,也多少回有些旁的吧。”[6]39同時,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時我國兒童文學匱乏的現象,“填補了五四時期清理舊‘兒童讀物后留下的空白,”[4]對我國的兒童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五.小結
綜上所述,五四時期時代背景特殊,一方面五四前翻譯活動出現了一個高潮,外國文學被介紹到中國;另一方面,兒童意識得以覺醒,兒童的文學也受到重視。童話本身具有幻想的特征,符合兒童的天性,適合兒童閱讀,是一種重要的兒童文學類型,因此,五四時期的翻譯家就選取了外國兒童文學中一些著名的童話進行翻譯,以彌補當時中國兒童文學作品嚴重匱乏的狀況,這對中國兒童以及兒童作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1]王泉根.兒童文學教程[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2]王秉欽.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3]任淑坤.五四時期外國文學翻譯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王泉根.“五四”與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轉型[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1):169-180.
[5]蔣風.兒童文學概論[M].長沙: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82.
[6]陳伯吹.兒童文學簡論[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59.
[7]黃云生.兒童文學教程[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6.
[8]秦弓.論翻譯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以五四時期為例[J].文學評論2007(2):119-126.
(作者單位:四川外國語大學成都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