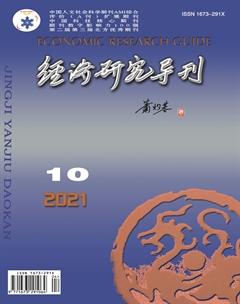企業融資結構對創新效率的影響
董良穎 雷良海

摘 要:創新是推動企業進步和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以我國2013—2018年滬深A股信息技術服務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選擇創新效率進行衡量,檢驗融資方式及比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企業的內源性融資和股權融資對企業的創新有明顯的正向促進效應,而債務融資則具有明顯的負向效應。因此,企業應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對融資結構進行適當的優化調整,盡可能提高內源融資和股權融資的比例。同時,在政策方面,國家應加快推動多層次資本市場構建,促進企業增加股權融資,減少債務融資,最終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關鍵詞:內源性融資;外源性融資;企業;創新效率
中圖分類號:F832.5?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1)10-0044-04
引言
基于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及企業發展情況,可知創新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創新是推動經濟跨越式發展的必然要求,是推進企業進步的必然選擇。一個企業或國家想要持續發展,必須依賴創新。企業的創新則需要有足夠的資金保障,而籌集資金的方式則顯得尤為重要。企業主要通過盈余公積等來源進行內源性融資,此外,通過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獲得資金。不同的資金來源渠道對企業的創新發展的影響也存在較大差異。綜合分析我國各大中小型企業可知,目前企業的融資方式還是以向銀行貸款等的債務性融資為主。通過這種方式企業雖然可以獲得大量及時性資金,但需要支付相對高昂的利益費用,增加企業的償債壓力,對企業日常經營產生負面影響,并增加企業的財務風險,這會導致企業的創新發展受到阻礙。
直到2019年年末,我國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架構已經基本搭建完成,雖然能滿足一些企業的直接融資需求,但由于其建設并未進一步完善,架構不成熟,體系尚未健全,所以還并不能達到滿足市場上所有企業的融資需求。
本文的研究要點分別為:首先,現有文獻主要關注創新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或者是通過企業的創新能力來分析企業績效,并把營業收入、營業利潤等相關財務指標作為衡量企業經營績效的指標,而較少有研究企業創新能力的文獻,本文把創新能力作為中心進行研究,這一點上具有一定新意。其次,本文從創新效率這個角度出發,以效率這一相對性指標作為衡量指標,可以使研究更加科學合理,得出的結論也更具有說服力。最后,由于各行業之間的差異性,對于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其負債水平及股權占比等對企業的研發創新的影響并不相同,所以分行業進行實證研究得到的結果對該行業而言更具有準確性和參考意義。本文選取在滬深A股上市的所有信息技術類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以使結果對該類企業的融資決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企業創新能力是衡量企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但由于該指標的不可衡量性,需要將其表達成可直接衡量的定量指標。而目前的文獻主要是將企業創新投入或產出等定量指標作為測度指標,選取企業專利數或研發總額進行衡量,但這些指標均具有絕對性,且其只代表某一方面的大小,并不具備所有因素,使得代表性有限。而且由于各個行業的特殊性,創新所需的成本、時間及資源等因素完全不同,使其在創新投入這方面也有較大差異,可知依靠這些定量指標的絕對性數值所得出的結論并不完全準確,且不具有絕對的說服力。因此,不能以企業的投入金額和專利申請數量等指標作為衡量指標來進行研究。
綜上,本文選取了企業創新效率來衡量企業的創新活力。該指標是一個相對指標,是指企業在一定時間內的創新產出與創新投入之間的比值。該指標從企業創新速度的快慢進行考慮,而不是金額大小的角度,使該研究更加嚴謹科學。在現有的對企業創新績效研究文獻中,劉洪偉和馮淳(2015)采用企業并購成功后每年成功申請的專利數作為技術創新績效的代理變量。姚立杰和周穎(2018)依據專利數是企業當年和歷史相關研發支出的函數的觀念來選擇指標。樂菲菲和張金濤(2019)認為,使用專利數量與業績指標比值的形式能夠較好地體現企業創新效率。王曉燕和張冊(2020)認為研發投入與產出等定量指標具有絕對性,代表性不強。
我國現行的經濟大環境下,國家積極倡導去杠桿,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推動企業優化融資結構,促進企業融資便利化,并減少債務融資比例。胡宗義和馮婷(2018)認為,融資結構指企業獲得各項生產經營資金的來源、組合及其相互關系。Myers 和 Majluf(1984)提出了優序融資理論,內源性融資的成本相對較低,容易成為企業的融資首選。何國華等(2011)提出融資結構會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的觀點。鐘田麗等(2014)認為,企業融資結構選擇是指企業負債融資與股權融資的選擇和配比。所以,根據企業融資方式的不同,分別研究分析其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很有必要,并能為企業協調籌資方式和比重、提高企業創新效率提供參考。
內部融資是指企業利用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等進行融資,不需要支付相關費用,企業可隨時自由取用。Brown和Petersen(2009)指出,企業通常會在融資時優先考慮內源性融資,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以及破產風險,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張麗(2019)研究得出,內源性融資對企業創新投入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且在充滿激烈競爭的外部環境下,企業創新屬于商業機密,是企業獲得更多市場份額的依靠,為降低外泄的風險,減少損失,并適當縮減創新過程中的費用,企業更傾向于通過內源性融資來籌集資金。由此,提出理論假設H1。
H1:內源性融資能正向促進企業的創新效率。
根據所查數據得知,目前我國的大部分企業都是通過債務融資來籌集所需資金,高比例的債務融資意味著利益費用較高,這使得企業可自由使用的資金減少,對創新發展的投入減少,抑制了企業的創新活力。而融資成本過高,企業的研發創新項目就得不到持續發展。黃少安和張崗(2001)指出,債務融資所需支付的高額融資成本會嚴重制約企業的創新發展。彭景頌和黃志康(2015)認為,債務融資通常是依賴于銀行,但這種由負債引起的契約往往會難以監督,導致很難形成有效的債權債務約束機制。擁有較多負債的企業所能夠承擔的研發費用相對較低,使得研發動機減弱。根據以上分析,提出理論假設H2。
H2:債務融資會對企業的創新效率產生負面影響。
股權融資是指企業以發行股票等方式籌集資金,該方式籌集到的資金對企業的創新產出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因為一般的股權投資者青睞高風險、高收益的項目,這剛好滿足企業的創新投資需求。并且相對于債務融資而言,股權融資的成本也較低,也沒有還本付息的硬性約束,對企業的創新投入具有促進作用。李匯東等(2013)研究結果表明股權融資無須償還股本,支付費用,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企業創新投資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且從股權集中度和公司治理角度分析,股權融資有利于解決股權集中帶來的問題,并積極推動企業的創新研發活動(任海云,2010)。良性循環有利于提高企業的創新動力,并帶動創新績效得到提升。由此,提出假設H3。
H3:股權融資能積極促進企業的創新效率。
二、樣本與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2013—2018年在滬深A股上市的信息傳輸、軟件及信息技術服務業的相關數據作為研究對象,為保證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對收集整理的數據做剔除ST和*ST公司、數據不完整,消除極端值的處理,最終得到有效樣本516個。本文用到的所有數據均來自CSMAR和Wind數據庫。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企業創新效率(IE)。由于行業之間存在差異,企業專利的申請和授權數量會有所差異,且企業的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也有很大不同,還會受到企業自身盈利能力等因素的影響,采用這些指標并不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選取企業本年研發費用與本年營業收入的比值(IE)作為指標來衡量企業的創新效率。
2.解釋變量。解釋變量為企業的融資結構,本文分別以內源性融資、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作為具體的解釋變量,以企業留存收益與累計折舊之和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內源性融資,以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來衡量債務融資,以股本與資本公積之和與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股權融資。
3.控制變量。本文選取對企業的創新研發投入影響最大的幾個因素作為控制變量。主要包括企業規模、企業上市年限、大股東持股比例、企業盈利、政府補助和董事會規模。
其中,被解釋變量的計算方式如下:
企業創新效率(IE)=本年研發費用/本年營業收入
(三)模型構建
為檢驗提出的H1、H2和H3三個假設的正確性,本文對三種融資方式分別構建如下的多元回歸模型: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以Stata15.1軟件作為研究工具,對全樣本包含的所有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得到描述性統計分析的結果。從顯示的結果可以看出,我國信息技術類行業IE的均值為11.94,說明目前我國該類行業的整體創新效率比較偏低,創新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加強。IE的最小值為0.12%,幾乎接近于0,而最大值為41.53%,兩者之間差距較大,表明在我國現階段的發展水平下,信息技術有關行業的發展層次不齊,企業發展狀況的好壞與企業創新研發水平密切相關。內源性融資的均值為19.39%,最小值甚至為負,這表明有部分企業目前根本沒有能力進行內部融資。債務融資的均值為32.35%,股權融資的均值為46.38%,反映出我國的信息技術類行業目前逐漸開始減少對債務融資的依賴,轉向股權融資。債務融資的均值下降到30%左右,但最高值還是達到77.53%之高,其企業資金基本全部依賴負債來實現,這也說明即使目前我國處于測結構性改革過程中,但仍有部分企業的杠桿率較高。
(二)相關性分析
本文對所有的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以了解各指標之間的關聯程度,并得出相關系數矩陣。IE與內源性融資和股權融資的系數分別為0.146和0.195,均為正數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IE與內源性融資和股權融資成正相關關系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企業內源性融資和股權融資能正向促進企業的創新效率,這一結果也初步驗證了假設H1和假設H3。同時,IE 與債務融資的相關系數是-0.34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表明IE與債務融資成負相關關系并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企業債務融資與企業的創新效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負相關關系,這一結果初步驗證了假設H2。通過相關性分析結果還可以看出,本文選取的所有變量與企業創新效率之間都有顯著的相關性,說明本文的實證模型是科學合理的。
(三)回歸結果分析
以企業創新效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對全樣本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并得到回歸結果。根據回歸結果可以看出,IE的內源性融資的回歸系數是0.106,顯著大于0,說明企業的內部融資對企業的創新效率起到積極的促進效用。內部融資每增加1個單位,IE會隨之增加0.106個單位,即企業的內源性融資占比越大,企業的創新效率越高,由此得出假設H1成立。而IE 的債務融資的回歸系數是-0.183,說明企業的債務融資會對創新效率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負債每增加1個單位,IE就會降低0.183個單位,說明隨著企業籌集資金中負債資金的增加,企業的創新績效降低,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所以假設H2成立。IE的股權融資的回歸系數為0.195顯著大于0,說明通過股權融資籌集的資金對企業創新投入發展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股權融資每增加1個單位,IE就會增加0.195個單位。即當企業股權融資的比例上升,企業的創新效率也會隨之增加,則假設H3成立。通過比較內源性融資和股權融資與企業創新效率的回歸系數的數值大小,可知股權融資對促進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作用更大。因此,我國應加快推動市場完善發展,增加資金籌集渠道,促進企業融資便利化,并鼓勵企業積極通過發行股票等方式籌集資金。由于版面限制,實證結果所得表格省略。
四、穩健性檢驗
第一,多重共線性檢驗。為使本文建立的模型具有良好的穩健性,首先需要對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以方差膨脹因子法進行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可知,個變量的VIF值均小于10,模型的整體平均值僅為1.76,遠小于10。得出本模型中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的結論。
第二,進一步檢驗。為檢驗回歸結果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增加實證結果的說服力,本文通過改變被解釋變量重新進行實證分析來進行進一步的檢驗。將企業創新效率采用企業市值與年末總資產的比重(IE2)作為衡量指標進行回歸檢驗,并得到新的回歸結果。根據新的結果進行分析,得到企業融資結構對企業創新效率影響仍然顯著的結論。且內部籌資及股權籌資對IE2的影響是積極的推動作用,通過銀行借款等債務融資對IE2仍是起到抑制作用,綜上可得本論文采用實證模型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即企業內源性融資能正向促進企業創新效率,而債務融資則與企業創新效率之間是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同時股權融資與企業創新效率之間是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結語
在經濟快速發展,市場競爭激烈的大環境下,企業的創新效率對企業自身的發展及是否能在市場上占有一定地位起著關鍵的作用。為了能夠有效反映出企業創新的真實水平,選取創興效率這一指標來對企業的創新能力進行衡量。企業如想能夠平穩高效發展,首先需要重視自身的創新投入發展活力,提高創新發展效率。而考慮到資金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性,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優化企業的融資方式及比重。企業為促進自身的創新能力,在自身能力范圍內適當調整融資結構。合理分配三種融資方式的比重,并適當減少對債務融資的依賴程度,增加其他兩種融資比重。本文以2013—2018年在我國滬深A股上市的信息傳輸、軟件及信息技術服務業公司為樣本,研究了企業的籌資方式及比重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并得出內部融資和股權融資會對企業創新效率起到積極推動作用,而債務融資則會對企業創新效率產生顯著負面作用的結論。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為更積極地促進企業發展,提高企業創新效率,企業應該理調整融資方式,貫徹落實國家的供給測結構性改革政策,積極落實去杠桿政策。且企業自身能力對于創新能力也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對于企業自身而言,企業應不斷提升盈利能力,增加留存收益等,使企業有能力進行內源性融資。
第二,政府應更注重于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加快對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構建,促進企業股權融資便利化。出臺相關政策,并采取相應手段,以達到優化企業債務和股本融資結構,提高股權融資在企業融資中的比例。股權融資的便利性使得企業可以逐步減少企業向銀行貸款籌集資金等方式的依賴,并轉向股權融資,增加企業股權融資比例,這使得企業可以自由使用且能夠投入于企業創新研發等活動的資金增多,從而更有利于企業的整體發展。企業發展良好,盈利能力較強,能夠進一步促進企業的科技創新。
第三,為降低我國信息傳輸、軟件及信息技術服務業各公司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政府應對不同企業的發展水平提供具有針對性的政策指導意見,對發展相對落后的中小微企業加大扶持力度,給予更多的關注,并在能力范圍內對各企業的創新研發活動提供層次化資金補助計劃等,以確保企業能夠有足夠的資金進行創新研發活動,提升企業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1]? 劉洪偉,馮淳.基于知識基礎觀的技術并購模式與創新績效關系實證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5,(16):69-75.
[2]? 姚立杰,周穎.管理層能力、創新水平與創新效率[J].會計研究,2018,(6):70-77.
[3]? 樂菲菲,張金濤.政治關聯斷損、研發投入與企業創新效率[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9,(1):90-96.
[4]? 王曉燕,張冊.去杠桿背景下企業融資結構對創新效率的影響研究——來自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金融理論與實踐,2020,(3):17-25.
[5]? 胡宗義,馮婷.外部融資結構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基于我國信息技術行業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18,(1):3-10.
[6]? Myers Stewart C.,Majluf Nicholas S.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4,(2):187-221.
[7]? 何國華,劉林濤,常鑫鑫.中國金融結構與企業自主創新的關系研究[J].經濟管理,2011,(3):1-4.
[8]? 鐘田麗,馬娜,胡彥斌.企業創新投入要素與融資結構選擇:基于創業板上市公司的實證檢驗[J].會計研究,2014,(4):66-73.
[9]? Brown J.R.,Petersen B.C.Financing Innovation and Growth:Cash Flow,External Equity,and the 1990s R&D Boom[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9,(1):152-185.
[10]? 張麗.融資結構與創新投入的關系解析[J].現代企業,2019,(2):85-86.
[11]? 黃少安,張崗.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分析[J].經濟研究,2001,(11):12-20+27.
[12]? 彭景頌,黃志康.戰略性新興產業公司績效與資本結構優化研究[J].財會通訊,2015,(33):59-62.
[13]? 李匯東,唐躍軍,左晶晶.用自己的錢還是用別人的錢創新?——基于中國上市公司融資結構與公司創新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3,(2):170-183.
[責任編輯 辰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