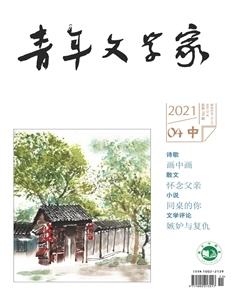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形象喻示探討
周博
形象喻示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中的一種方式,其主要特點是批評者在批評對象時通常將其轉化成一種比喻方式,將抽象的特征轉化成直觀具體的形象,并不需要嚴謹的邏輯推理能力,而是給人一種不言而喻的感覺。張伯偉的《鐘嶸<詩品>的批評方法論》就是論述的這方面內容,所以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式時,既要注重其發展過程,也要注重藝術之間的內在聯系。而在使用形象喻示批評方式時,要綜合考量形象喻示的形成和發展、內涵和提示、思維特性和審美內涵等方面,并投入個人審美經驗,促使批評對象更加生動直觀形象化。
一、中國古代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往往伴隨主觀意識,影響讀者的思想意識,但這種方式也是建立在社會發展基礎之上。審美風氣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產生重要影響,所以讀者在閱讀古代文學作品時,主要做到保持自我,不忘初心,避免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獨特的看法,這就要求讀者要夯實自己的文化底蘊,增加知識面,培養自身文化素養,提高審美能力,對古代文學作品有自己的獨到見解。與此同時,讀者還需掌握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批評標準,了解事物發展過程以及原因和結果,才能正確認識到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優勢與不足。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往往能夠反映出批評家的品性,換句話說就是批評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所生出的想法會受到自身思想水平與文化素養等方面影響,從而影響古代文學批評。如果某部文學作品在表達方式上或者蘊含道理上難以讓人理解,或多或少存在偏見時,那么讀者就會產生一定的閱讀障礙,不能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以,也要求文學創作者要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文化底蘊,在符合人們思想認知基礎上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另外讀者根據自身人品進行文學評價,在某種方面上具有保守與片面性,會導致優秀作品不被大眾所熟知,影響對文學作品的正確判斷。因此,需要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進行正確的評價與批評,應注重文學作品本身,避免出現道德評價。
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形象喻示
(一)形象喻示中意蘊外化的幾種類型
形象喻示指的是作家或者作品將風格內蘊外化,批評者首先應從整體把握批評對象,然后將批評對象外化成一種不言而喻的直覺。而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形象喻示包括人化、物化以及禪化三種形式。首先,人化也就是說批評者習慣將其自身作為衡量事物的標準,將事物賦予人的名稱,人的精神與靈魂;人化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一種常見方式,如宋代吳沆《環溪詩話》中“詩有肌膚,有血脈,有骨骼,有精神”,古人通常情況下,都將文章人化,從而賦予文學藝術生命特征,促使文章行文脈絡更加生動形象。如張謙宜《齋詩談》中,“身既老矣,始知詩如人身,自頂至踵,百骸千竅,氣血俱要通暢,才有不相入處,便成病痛”,這是典型的人化,以人的氣象、血脈等來喻詩。也就是古代文學批評中的生命之喻。其次,物化與人化截然不同,物化是將人比喻成物的過程,也就是說萬物皆有靈性,如《詩經》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將自然事物積淀成一種精神審美原型,對于創作者來說是熟悉且富有聯想的,能夠抒發創作者的思想感情。禪化則是一種較高級別的境界,批評者往往會借助禪宗或佛經等傳達文學作品的內蘊,禪化更注重人的本性,認為文學即人學,如吳可《藏海詩話》中,“凡作詩如參禪,須有悟門”,也是說在品讀文學作品時,就相當于參禪,有著相似的心理過程,作品風格以及內蘊相對抽象,需要對其進行深入思考,參悟其中道理。
(二)形象喻示批評的體式
中國古代文學是詩人通過某種表達形式,將其賦予深刻的道理,表達出古人所體驗或所感悟到的內容。批評家對中國文學進行批評時也是處于相對感性與自由的狀態,但人們往往受固定思維模式影響,在采取形象喻示批評方式時,在行文脈絡與結構上都會受到影響,通常情況下可分為總分結構、并列肯定、對比差異、排比設喻等方式。接下來將展開做簡要說明。
1.總分結合
這種表述方式主要是從整體到部分等進行具體表述,給人一種非常完整的感覺,如曹植的《前錄序》中,“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從“儼”“勃”等多個方面分別探討“君子之作”的內蘊,既能把握整體內容,也能顧及到局部具體內容,促使評價更具有說服力,注重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合乎情理的表達出文學作品的內涵。
2.并列肯定
這種述說方式多數情況下應用于兩位藝術家的風格特征評說中。如“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通過“爛若披錦”和“排沙簡金”,一致肯定了潘岳和陸機的藝術風格,采用并列肯定這種方式,通常是兩位創作家的藝術風格難分高低,并且在表達方式上都工整勻稱,前后呼應,整齊美觀,給人一種美的享受。
3.對比差異
相對于并列肯定來說,對比差異的區別之處就在于比較兩位創作者的差異性,在表述結構上相對整齊,但前后內容有所不同。如“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通過這樣的評價,充分表達出陶淵明與謝靈運作詩的差異。
4.排比設喻
排比設喻是在并列肯定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形象喻示在先秦時期運用較少,并且在運用過程中都采用簡潔明快的表達方式,隨著歷史不斷演變發展,這種排比設喻方式越來越夸張,如“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輿玉輦,雕龍彩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凡”,在皇甫湜《諭業》一文中,句句用喻,并且大肆渲染,給人一種目不暇接之感,這種方式在當代得到有效發展,在文學創作上都講究鋪排渲染效果。
(三)形象喻示思維
1.直觀感悟
由上文可知,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形象喻示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尋找本體和喻體二者之間的契合點進行設喻,另一種是通過意象全面描述批評對象。首先說第一種方式,批評者需找出契合之處進行比擬,簡潔明了,并且能夠突出重點,如羅大經的《鶴林玉露》中“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通過對比韓柳的差異,突出二人的寫作風格。其次是運用意象對批評對象進行對角度的評價,從而掌握創作者的藝術特征,如在葉燮《原詩》中“漢魏之詩,如畫家之落墨于太虛中,初見形象。一幅絹素,度其長短、闊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次脫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濃淡;而遠近層次,尚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明也”,抓住重點進行比擬說明,從而引發讀者的想象,為讀者帶來一種新鮮之感,并為文學批評注入新鮮血液。
2.突出主要特征,對比事物差異
形象喻示思維主要通過具體的比擬,將事物的內在意蘊描述出來,促使讀者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有直觀性的了解,對于思維抽象、含義隱晦等事物運用形象喻示這種批評方式最為適宜,能夠將抽象的概念具體形象化。如明代李東陽《麓堂詩話》中“蓋正言直述,則易于窮盡,而難于感發,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文章本身晦澀難懂,將隱含事物形象化,有利于激發讀者閱讀興趣,反復閱讀,理解其中深意。
3.籠統形象,非客觀理性
形象喻示思維比較籠統,但又非常形象地將事物進行比喻和說明,缺乏邏輯性,所以批評家在評論過程中會賦予文學想象美,但是卻存在一些問題,如評論語言相對較模糊。如朱權的《太和正音譜》中曰“徐甜齋之詞,如桂林秋月;胡紫山之詞,如秋潭孤月;楊顯之之詞,如瑤臺夜月;吳仁卿之詞,如山間明月”。在中國古代文學中,“月”有多方面的象征意義,如象征著皎潔、清雅、柔和等,這樣的評語會使讀者難以理解這幾個人文學風格的差別在哪,并且很多詞匯隨著歷史的不斷演變和發展,暗含之意也會發生改變,很多時候具有不確定性。再加上批評家由于個人喜好在評論過程中會存在片面性,影響讀者的判斷,如愛詩詞歌賦者與不愛者會有不同的看法,“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筆”,“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這兩種不同的評語就是因為個人審美存在差別。
三、結語
綜上所述,形象喻示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具有要作用,通過塑造意象和構造意境而表達出批評家的想法,這種批評方式既有優勢又有缺陷,優勢之處在于通過形象喻示將事物生動形象化,使讀者更好地理解文學內涵;而缺陷之處在于這種批評方式受批評家的主觀思維影響較深,并且缺乏嚴謹的邏輯性,缺乏客觀性,從而影響讀者的判斷。所以我們在運用形象喻示這種批評手法時,應正確認識其存在的不足,充分發揮優勢,采用辯證思維去分析相應的古代文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理解其中蘊含的深刻道理,從而形成多元化的評價體系,促進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